|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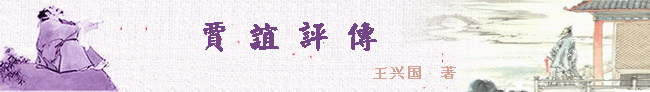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一 著作真伪,聚讼纷坛
(一)关于贾赋真伪的考辨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类有"《五曹官制》五篇",班固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赋类有"《贾谊赋》七篇"。又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抬补》于《春秋》类有贾谊《春秋左氏传训诂》。以上四种著作,《五曹官制》和《眷秋左氏传训诂》,早已失传,所以前人讨论不多。赋七篇今尚存五篇,《吊屈原赋》、《鵩鸟赋》原载《史记》和《汉书》本传,是世所公认的贾谊著作,没有争论。《旱云赋》和《鵩赋》原载《古文苑》。《惜誓》载《楚辞集注》。对《惜誓》和《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后人有不同看法。例如,朱熹在《楚辞集注·惜誓》的题注中说:"《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鵩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问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这表明朱熹是信为贾谊所作。清人王耕心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其文(指《惜誓》--引者)虽搞辞高朗不让昔贤,而篇首即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贾子遗文已不待辩。或以为代屈原为辞,尤非事实。屈原之衰健,向无明文可考,今乃妄称衰老,于义何居?且贾子之忠诚可质屋漏,《度湘赋》(即《吊屈原赋》--引者),颇寓迁谪之慨,亦怨而不怒,无愧风人。此文篇首己云衰老,篇中复云'寿冉冉而日衰',又云'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又云'远浊世而自藏',以孝文之世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若直以此为贾子所作,何异诬罔先贤,妄凿浑沌!朱子注《楚辞》,虽亦姑事因循,要为千虑之一失,非后学所宜附和。"(《贾子次诂·记纪下》)所以王氏在编《贾子次诂》时,便将此篇弃而不录。
其实,王耕心否定《惜誓》为贾谊的论据,王夫之在《楚辞通释·惜誓》的题解中早已回答了。王夫之肯定此赋为贾谊的著作的根据是:
一、"贾谊渡湘水,为文以吊屈原,其同旨略与此(指《惜誓》--引者)同。"王夫之的这个观点,与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是一致的。就以王耕心举的例子来说,《惜誓》中讲"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在《吊屈原赋》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又如《惜誓》中有"远浊世而自藏",《吊屈原赋》中则有"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沏深潜以自珍。"为什么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可以那样写,而在《惜誓》中写了,就不行呢?可见,王耕心说"以孝文之世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为谊作审矣。"王夫之把《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出入互见"的责任推在贾谊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汉书·贾谊传》中的《陈政事疏》是班固撷取《新书》加以重新编辑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详述。不过,就《新书》本身来说,也确有一些段落有重复之处。造成这种重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在《新书》流传过程中抄写差错所致;其二,贾谊自己在不同场合、时期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不可避免地使用类似的思想。我认为,《惜誓》和《吊屈原赋》中的重复,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因此,尽管其思想有类似之处,但其表达方式,即语句并不雷同。
三、王夫之还指出:"惜誓者,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谊意以为原之忠贞既竭,君不能用,即当高举远引,洁处山林,从松乔之游。而依恋昏主,迭遭谗毁,致为顷襄所窜徙,乃愤不可惩,自沉泪罗,非君子远害全身之道,故为致惜焉。谊所言者,君子进退之常经,而原以同姓宗臣,且始受怀王非常之宠任,则国势垂亡,而欲引身以避患,诚有所不能忍;其悱恻自喻之至性,有非贾生所知者。则惜誓之言,岂足以曲达幽忠,匪舌是出,九死不迁之郁曲哉?顾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异于东方朔、严夫子、王褒、刘向、王逸之茸阘无情。且所以惜原者,珍重贤者而扳留之,亦有合于君子爱惜人才之道。故今所存去,尽删七谏九怀以下诸篇,而独存《惜誓》。"王夫之这段话表明,他认为《惜誓》虽未能"曲达"屈原之"幽忠",但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较东方朔等人的"无情"之作为高。加之《惜誓》"有合于君子爱惜人才之道",所以王夫之对之十分重视。他在作《楚辞通释》时,将传统的《楚辞》中许多篇章均删去了,但却保存贾谊的《惜誓》,这说明他对此赋之重视。相比之下,王耕心将此赋从他自己重新编定的《贾子次诂》中删去,就显得过于轻率了。
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认为《旱云赋》非贾谊所作,其理由是:"其末段有云:'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汉武帝以后才有的事,当非贾谊所作。"(《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62 页)我觉得这一论断与史实不符。其实天人感应的思想在陆贾那里就已开其端。《新语·道基》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又说:"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新语·术事》说:"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又说:"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这些说明,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不是汉武帝以后才有的事,而是汉初就已如此。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在贾谊书中同样可以找到。例如《新书·耳痹》一文开头便说:"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言在则害,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败,倍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接着,他举楚平王"怀阴贱,杀无罪",结果得到的是子孙失国。自己死后还被掘墓鞭尸的报应;吴王阖闾"行大虐",结果导致"上帝降祸,绝吴命乎直(胥)江"的惨报。最后,贾谊的结论是:"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闲,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这些说法,与《旱云赋》中所讲的"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用这样一句话来否定《旱云赋》是贾谊所作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二)对《新书》"事务"文真伪的主要分歧
关于贾谊著作的真伪问题的争论,除了上述个别赋以外,主要是集中在《贾谊新书》上。现存《新书》五十八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这五十八篇文章中,有三十二篇题下标存'事势"的字样,有十八篇题下标有"连语"的字样,有八篇题下标有"杂事"的字样。当我们回顾关于《新书》真伪问题的争辩时,可以看到主要是围绕上述三十二篇题下标有"事势"的著作与《汉书》有关篇章所录贾谊奏疏的关系而展开的。争论的不同观点,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是南宋人陈振孙(约1183-?)在其《直斋书录解题》的"非谊本书"说。他录《贾子》十一卷。"今书首载《过秦论》,未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可见,陈振孙是以《汉书》中所载贾谊奏疏衡量《新书》有关文章,认为除《汉书》中所载者外,其他内容均浅陋和驳杂,不是贾谊原来的著作,不值一顾。清人姚鼐在《辨贾谊新书》(载《惜抱轩文集》卷五)中,大体上也是沿袭陈氏的观点。他说:"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之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晰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可见,姚氏基本上也是沿袭陈振孙的观点。
其二,是朱熹的"杂记稿"说。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五记载:"问谊《新书》。曰'此谊平日记录稿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又说:"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宋人工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谈到贾谊书时,也是沿袭此说。黄震的《慈溪黄氏日抄》卷五十六《贾谊新书》条下说:"所论汉事,皆于《治安策》及《论积贮》、《谏禁铸钱》者,殆平日杂著所见,而他日总之以告君软?"清人卢文绍的后人纂集说,实际上也是承袭了朱熹的"杂记稿"说。他在《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是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卢文弨说《容经》等篇"辞义典雅"这是对陈振孙"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的有力驳斥,而他所举的这些篇名均系"连语"一类,这也说明他是肯定了这些篇章的独立存在的意义。
其三,是《四库全书总目》的"不全真,亦不全伪"的说法。《总目》说:"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朱子语录》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陈振孙亦谓:'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赞又称'三表五饵以系单于',颜师古《注》所引《贾谊书》与今本同。又《文帝本纪》注引《贾谊书》'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间其名',亦与今本同。则今本即唐人所见,亦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朱子以为杂记之稿,固未核其实。陈氏以为决非谊书,尤非笃论也。"如果我们将以上三种观点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然对贾谊《新书》的真实性见解不一,但有一点却又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均"浅驳不足观","难得粹者","瞀乱无条理"。而他们的方法,也都是以《汉书》所载贾谊著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书》,非《汉书》所有者辄鄙弃之。当然,对于这种做法,历史上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宋人王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中就曾指出"班固作传(指《贾谊传》--引者)分散其书(指《贾谊新书》--引者),参差不一,总其大略。"这就是说,王应麟认为《汉书·贾谊传》的《陈政事疏》,是班固取《新书》有关篇章,"总其大略"而成的。为此,王应麟还作了具体分析,如他指出"自'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已上,则取其书所谓《宗首》、《数宁》、《藩伤》、《藩强》、《五美》("一动而五业附",《新书》云"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凡七篇而为之。"如此等等。而清人刘台拱则认为:"谊陈治安之策,与其《保傅传》本各为一书,班氏合之,而颇有所删削"(《汉学拾遗》)。清代学者汪中(1745-1794)则指出:"自《数宁》至《辅佐》三十三篇,皆陈政事。按《晁错传》,'错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则知当日封事,事各一篇,合为一书固有其体,班氏约其文而分载之本传、《食货志》尔,其指事类情优游详,或不及本书。"(《述学内篇·贾谊新书序》)。这表明汪中不仅认为《汉书·贾谊传》所载《陈政事疏》是班固约贾谊《新书》而分载之,而且认为班固的"约文"有的地方不如贾谊原书"优游详"。清人俞樾(1821-1907)
也认为,班固是据《新书》作《贾谊传》的,因此他对卢文招在校定《贾谊新书》时,动辄以《汉书·贾谊传》来删改《新书》的作法十分不满,认为他"是读《汉书》,非治《贾子》也。"(《诸子评议·贾子》)
(三)余嘉锡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遗憾的是,上述学者虽然看到了《汉书·贾谊传》中《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的正确关系,但均未深入展开论述。直到近人余嘉锡(1883-1955),才比较系统地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余氏把《新书》与《汉书·贾谊传》详加比较,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不是《新书》抄《汉书》,而是《汉书》抄《新书》。余氏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批评了《四库提要》关于《新书》是"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的说法,指出: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如取《势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为典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使非《新书》具在,班固又于赞中自言之,则读者莫知其所谓"行臣之计"者为何等计,将不觉其为操术之疏,而疑为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而其文终焉,则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一篇之于也。而于移风易俗(即"商君弃礼义"节)及礼貌大臣(即"人主之尊譬如堂"一节)两太息之间,忽取《新书·保傅》及见于《大戴》之《礼察》二篇阑入其中,既无长太息之语,又与前后文义不侔。《礼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礼禁将然,法禁已然,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犹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礼义以道习天子,而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之意。班固删去"为人主师傅"数语,使此一节若泛言礼与法之短长者,以起下文"礼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联贯为一矣。然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为长太息之一那?以此一节赘于其间,无乃如贾生所谓"方病大肿,一胚之大几如要"也乎!凡此皆其删并痕迹之显然者,而曾无人肯为细心推寻,亦可怪也。《新书》自南宋已苦无善本,卢文■以校勘名家,然其校此书于非《汉书》所有者,率不能订其谬误,通其训诂,凡遍其所不解,辄诋为不成文理,任意删削。俞樾《诸子平议》(卷二十七)讥其是读《汉书》,非治《贾子》,深中其病。若陈振孙者,其识未必过于卢氏,彼亦徒知读文从字顺之《汉书》耳,则不以为《汉书》录《新书》,而反以为《新书》录《汉书》(见《书录解题》卷九),固其宜也。乃《提要》从而附和之,谓此书乃取本传所载,割裂颠倒,其亦未免泪于俗说也夫。我所以不惜篇幅摘引余嘉锡这一长段议论,目的是为了说明,余氏在《新书》真伪问题的研究上的确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这种新就在于他不像前人那样,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地一味歌颂"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因而指责《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相反,余氏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将《新书》有关篇章与班书所载贾谊之文的某些段落进行比较,因而从逻辑和语法上揭露了班氏书中所载贾谊之文,"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余氏所举的第一个"斧凿之痕",从语法上来说叫"苟简"。吕叔湘和朱德熙说:"文章不应该烦冗,不必要的话不必说,这是不错的。可是如果走到另一极端,不把话说周全,使意思不能完全表达出来,那也是不对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年版,第215 页)班固取《势卑》篇文"陛下何不以臣为典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就使人不知"行臣之计"何所指。所以余氏说:"使非《新书》具在,班固又于赞中自言之,则读者莫知其所谓'行臣之计'者为何等计"。余氏的这种分析,既说明了班氏"行文之疏",又证明了《新书》之可靠。因为班氏在《赞》中虽提到"五饵三表",但未介绍内容,颜师古在注中介绍了内容,但也只是一个提纲,而《新书·匈奴》篇则有详细分析,且现存《新书·匈奴》与颜师古所引内容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它的可靠性。余氏所举第二个例证,即班书所录《治安策》一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可是在往后的介绍中,提到的"长太息"却只有三次。这实际上也属于"苟简"的"行文之疏"。余氏所举第三个例证是,班固将《新书·保傅》篇阑入移风易俗与礼貌大臣两太息之间,不仅"与前后文义不侔",而且将《保傅》篇中"为人主师傅"数语删去,"使此一节若泛言礼与法之短长者,以起下文'礼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联贯为一矣。然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为长太息之一耶?"这种错误作法从逻辑上来说,叫做"论据不相干",从语法上来说,就是"文不对题"。余氏的分析证明,所谓"颠倒"、"割裂"者并非《新书》,而是班固。这种驳斥是有力的,它一扫数百年来存在于一些学者中的对《新书》的偏见,为人们研究《新书》与《汉书》中所录的一些贾谊著作的关系,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余嘉锡的最后结论是:"陈振孙谓决非贾本书,固为无识,即《提要》调停之说,以为不全真亦不全伪者,亦尚考之未详也。"
(四)魏建功等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新书》真伪问题仍有不同看法。王季星同意卢文弨看法,也接受了余嘉锡的基本结论:"《新书》和本传文字互有出入,并不能断定一定是《新书》照抄《汉书》,反过来倒应该说《汉书》本传是真正建立在《新书》的基础上面的。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早已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是可供研究的。"(《贾谊和他的作品》,载《东北人大学报·人文科学报》1956 年第4 期)黄云眉则明确表示他不同意余嘉锡的观点,而赞成姚鼐"妄人伪为者"之说。黄氏在其初版于1931 年、重订再版于1959 年的《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中,对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逐条驳斥《提要》所谓"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又进行了反驳,从而得出结论:"卢氏与《提要》之语,皆近调停,而余氏又曲予回护,皆不可谓有识。"但是,必须指出,黄云眉在反驳余嘉锡时,回避了我们前面曾引证过的那一大段话,而那段话恰恰是余氏断定《新书》为真的最基本论据,而他驳《提要》所谓"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的一些论据,都是从属于其基本论据的。黄氏绕过余氏的基本论据而驳斥其次要论据,因而其结论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也就是说,余氏论证《新书》为真的方法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为后人研究指明了一个正确方向。
1961 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 期发表了魏建功、阴法鲁、吴竞存、孙钦善所撰《关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探索》一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沿着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思路继续进行深入探索的。如果说,余氏还只是从宏观上指出班固的《汉书》在摘录《新书》时留下的"斧凿之痕",即主要是指出班书在对《新书》的一些重要内容的取舍和安排有失当之处,那么魏建功等人的文章则进一步从微观上分析了班书有关摘录中存在的问题。该文不仅逐篇调查了《新书》见引于《汉书》的内容与原文的异同,而且以《藩伤》、《权重》、《淮难》三篇为例,与《汉书》所引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班固在引书时存在的问题。
作者指出,班固在摘引《新书·藩伤》一文时,只保留其部分结论,即"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而将"非所以活大臣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去掉了。而且班固还将贾谊得出这个结论的论据,即"既已令之为藩臣也,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莫邪而予邪子"至"所谓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一大段删去,这样做,作为史料运用,进行剪裁加工,只取结论,是可以的;"但这一部分在《藩伤》中正是何以'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非所以全爱子'的论述,是整篇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去之则不完整。"作者指出,班固在摘引贾谊《新书·权重》篇时存在的问题是:(1)将"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陛下且见之矣"一句中的"诸侯偕冠"删去。就使"下文'陛下且见之矣'中的'之'便无着落,本来'之'是指代'诸侯偕冠'这件事的。"(2)在上述"陛下且见之矣"后,《权重》原文还有段话:"岂不苦哉!力当能力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引文据《贾谊集》),也被班固删去。作者指出:"'岂不苦哉'四字不存,则'陛下且见之矣'意思未足。'见之矣,又会怎样呢?非有,岂不苦哉'作补充不可。"又,将这一段话删去,"则'甚可谓不知且不仁'句不存,这样,下文'难以言知''不可谓仁'便都无根著。"(3)班固将《益壤》篇结尾一段话,即"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移至《权重》篇"不可谓仁"之后,"说明班固认为它们讲的是同一内容。其实这两篇完全是两回事。《益壤》所说的是为了避免远属地区输均、徭使的不便,同时为牵制强大诸侯,主张增大个别诸侯王的治域;而《权重》所说的则是削弱诸侯王的权势;二者的意思恰恰相反。贾谊是把这两件事作为特殊问题和一般问题分别处理的,其内容毫无共同之点,把二者连在一起,就造成观点的矛盾。"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汉书》的删削,改变了贾文原义,甚至改得语句不连贯,文义晦涩,观点矛盾。"作者在分析《汉书》对《新书·淮难》一篇删削时指出,除了《汉书》将《淮难》中述淮南王罪状的一大段话,被概括为"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这样一句抽象的话之外,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将《淮难》原文中子肯报楚仇、诸刺吴王及荆轲刺秦王的叙述删掉,"这样,下文'白公子肯之报于广都中'' 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令人摸不着头脑,而且为什么'与之(指淮南王子)众,积之财'会导致象白公子胥报仇, 诸荆轲行刺的后果,读者也难以明白(凡此情况,足见《汉书》删削的破绽)。"正是通过这种典型例证的分析,所以《关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探索》一文的作者得出结论:关于《汉书》与贾谊原书的关系,这里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汉书》载文的本源是贾谊原书,而且陈政事的数次上疏组成了原书的重要内容;第二,传中所录仅是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班固是有选择的;第三,载文只是叙其"大略",班固是作了剪裁加工的,不全是原文。总之,正如王应麟所说:"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艺文志考证》卷五)这是贾谊原书与《汉书》的关系,试看前面现存《新书》与《汉书》的比较,它们的关系也恰恰与此三点吻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这种吻合正证明了今本的这一部分接近原本,具体说,就是今本这一部分的绝大多数篇章不仅思想内容可靠,而且语文形式也比《汉书》引文更接近原貌,它基本上保存了原本的样子。
余嘉锡、魏建功等人的考证,可以说基本上了结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关于《新书》真伪争论的公案,它可以使我们比较放心地引用《新书》中的文字进行学术研究,而不致作茧自缚地局限于班固《汉书》中所引用的个别篇章。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