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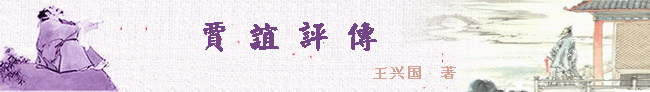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一 伦理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性论,是贾谊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贾谊论性,上承孔子的人性论。我们知道,孔子是以习言性的。他曾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贾谊同意孔子这一观点,他尝说:毁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保傅》)
所谓"人性非甚相远也",正是"性相近"的反面表述。贾谊还曾引孔子的一句话:"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同上)这句话不见于《论语》,也未见于先秦其他古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是贾谊的杜撰。因为时代久远,我国许多古代典籍早已散佚,而其中有些典籍在贾谊当时可能还是存在的,因此这句话很可能是孔子的佚文。加之,这句话与孔子的"性相近"一语的精神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所谓"性相近",正是指的"少成若天性"。一个人的性情如何,在未出生以前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当他出生以后,人们才能从其一哭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中,看出其性情来。心理学把人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粘液质,但这是就人的气质而言,而非言人性之善恶。气质虽然从婴儿时期就可见其差别,而人性却难以见其差别。所以孔子说"性相近",是符合实际的。至于所谓"少成若天性",则是说人性虽然在生下来之时是相近的,但当他出生之后,便马上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薰染,从而很快地形成了人们之间的性情和性格的差别。这就如贾谊所说的:"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保傅》)这种由"习"而得之性,虽然是后天得来的,但由于它是从小就大体定了型的,所以似乎是先天所成。我们要注意"少成若天性"之"若"字,正是作"好象"、"似乎"解。
贾谊虽然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观点,但他对孔子的人性论又有所发挥和发展。这种发挥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人牲作了理论化的注释
我们知道,孔子少言性,所以没有对性是什么进行解释。孟子把人性视为人禽区别的关键:"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于存之。"(《孟子·离娄下》)但这是讲的人性之重要性,而非给人性下定义。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苟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苟子·正名》)"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同上)这里虽然对性作了一些规定,但讲得比较笼统。贾谊则不然,他对性的规定就颇有理论色彩: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性生气,通之以晓"。(《道德说》)
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曾经分析过,贾谊的"道"是一种原始的物质,尽管它"无形",但却是"德之本"。"德者,离无而之有",它相当于构成各种事物的物质元素。所以贾谊说:"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道德说》)这句话正是对"道德造物"一语的说明。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各种具体形态的事物便开始出现了,"故润则腒然浊而始形矣"(同上)。具体事物之中有气有神,而性则是气与神相结合的产物,所以贾谊说:"性,神气之所会也。"这里的"神"和"气",不过是道与德的别名。因为贾谊说:"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冰而为德,神载于德。??道虽神,必载于德,而颂乃有所因,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这就说明,所谓"神",不过是道的代名词而已。尽管贾谊说"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但他认为从更直接的关系来讲,是"德生物又养物",而"道虽神,必载于德",所以他讲的"气"更多的是指"德"。因此,贾谊说性是"神气之所会",实际上也是道德之所会,是道与德相结合的结果。在贾谊看来,单纯的道或神无法形成性,道、神必载于德才能发挥作用;单纯的德或气,也只是象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德润,故曰"如膏,谓之德"》)只有当道、神寓于其中,才能形成有性情的事物。贾谊说:"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贾谊把事物的"性"说成是"与外物之感相应"的东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物之"性"固然是内在的东西,但是这种"性"要反映出来并且彼人们认识,就非得通过该物与他物相互作用不可。例如,我们要知道某物是否有胶性,就要试一试它是否能胶着某种东西。贾谊说的"润厚而胶谓之性",正是为了形象他说明性是某物与外物之感应所反映的特点和功能。
(二)人性有善有恶
虽然孔子未尝以善恶论性,但孔子之后的孟子主性善,而苟子主性恶。
贾谊生于孟荀之后,且是苟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必然要对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有所表示。
从现存的贾谊著作看,尽管贾谊是苟子的再传弟子,但是他却明确表示过不赞成性恶论。他在谈到秦国的社会风俗和教育内容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其(指秦--引者)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营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保傅》)
在贾谊看来,胡亥之所以那么凶残,坏事干尽,并不是因为他性恶,而是为秦国的习俗和教育制度恶劣所致。
贾谊对孟子的性善论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从其所提出的"材性"论却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主张性有善有恶的。我们且看贾谊下面的这段话: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粱、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任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者,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连语》)
所谓"材性乃上主",实际上是认为上主的"材性"是善的,所以"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所谓"材性乃下主",实际上是认为下主的"材性"是恶的,所以"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至于中主,其"材性"则是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所以它"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细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显然,贾谊把"材性"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的作法,与他自己说的性"相去不甚远"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否认胡亥的"性恶",另一方面又将桀、纣归人性恶的下主之类。
贾谊提出的"材性"有上、中、下三等之说,在思想史上开董仲舒"性三品"之先河。在《春秋繁露·实性》中,董仲舒主张有所谓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可教而善的"中民之性",和教而不善的"斗宵之性"。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同上)"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之所以强调以"中"名性,是因为他认为"圣人"和"斗筲"都是少数,而"中民"是社会的大多数,既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性是可善可不善的,所以教育才有可能。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设名不正,故弃重任而违大命,非法言也。"(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 品说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贾谊的性三品说虽然没有董仲舒的论证那么细密,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却是很清晰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均将性分成上、中、下三品,而且他们对这三种品性的特点的分析也是完全一致的。
(三)教育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如果说在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的命题中,已经蕴含了道德习行和教育训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却没有展开论述的话,那么贾谊则把这种关系作了比较充分的展开和论证。
例如,贾谊说: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徇俯而加志,我憻僈而弗省耳。(《劝学》)
这是从人性虽同,但各人的表现或功绩各异,说明" 俯而加志",认真学习和练习的重要性。
贾谊又说: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旱教谕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保傅》)
这里说的"心未滥"说的是少年时期的人性的纯朴状态。所谓"先谕教,则化易成",更多地是指对一个人,从小就要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使之潜移默化,习与性成。而所谓"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是指要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知道如何合宜得体地处理事情。这就非教育莫属,所以说是"教之功"。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