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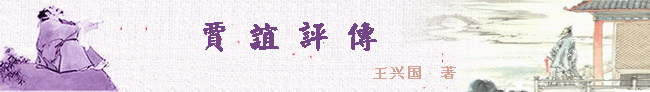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二 后人对贾谊的评论
后人对贾谊的评论颇多,而且分歧很大,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贾谊的遭际,即汉文帝待他是厚还是薄?二是关于贾谊思想的派别属性,即是属儒家,还是属法家或其他什么家。
(一)对贾谊遭遇的不同看法
关于贾谊生平遭际到底是好还是坏的争论,在汉代即已开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贾谊与屈原合传,尽管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是因为他们两人均善于"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但实际上是惺惺惜惺惺,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更加同情屈原和贾谊的不幸遭遇,此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看他在《贾谊传》中,一则曰由于绛灌等短贾生。"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二则曰贾谊困"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三则曰贾谊谏封淮南王子,"文帝不听";四则曰他自己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无处不充满着对贾谊不遇的同情之心。刘向实际上是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所以他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班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同上)所以他在《汉书·叙传》中又说:"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睿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屏藩,以强守围;吴楚合从,赖谊之虑。"可见,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肯定贾谊的人才,而分歧之点则在于:司马迁和刘向认为,按贾谊的才能完全可以任公卿,况且文帝有此打算,可是由于当朝大臣的阻挠,文帝这个愿望不仅未能实现,而且逐渐疏远贾谊,使他终于藩国太傅之任;而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其谋议已略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
自两汉以后,历代关于贾谊的生平遭遇的不同看法,大体上都没有越出司马迁、刘向与班固的观点。例如唐人李善在注《昭明文选》中贾谊的《鹏鸟赋》时,就说过:"贾生英特,弱龄秀发,纵横海之巨鳞,矫冲天之逸翰,而不参谋棘署,赞道槐庭,虚离谤缺,爱傅卑土,发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谓之未为不达,斯言过矣!"《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周代外朝种植槐棘,以为朝臣列班的位次。后人因以槐棘代公卿之位。可见李善是明确地认为贾谊当时只有登公卿之位,才可以称得上是"达"和"遇"。宋人欧阳修亦持此论,他说:"班史《赞》之以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予切惑之。"接着,欧阳修分析了贾谊一系列主张被文帝采纳了的情况后说:"故天下以谓可任公卿,而刘向亦称远过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浅,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斩级矢石之勇,或鼓刀贩缯贾竖之人,朴而少文,昧于大体,相与非斥,至于谪去,则谊之不遇可胜叹哉!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裨坠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泪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则固之善志逮(殆)与春秋褒贬万一矣。"(《贾谊不至公卿论》,载《长沙贾太傅祠志》卷一)在欧阳修看来,贾谊之不遇,是由于大臣之"非斥",文帝之"远贤"。王安石承班固之说,认为"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可见,在王安石看来,一个人的遇不遇,不在于其官职大小,而在其言能否为君王采用,其言能被采用,则可谓受知遇之恩,如果其言尽废,那么即使位至公卿也难以言知遇。苏轼在《贾谊论》中谈到贾谊之所以见疏于文帝时,则归咎于他"不能自用其才",即不善于深交绛灌等大臣,"默默以待其变",相反,而是"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清人袁枚说:"吾尤怪太史公谓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阳年少,内位大夫,外为师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诚,自惊不及,宁肯虚誉?其所议论,颇见施行,其未为丞相者,将老其才而用之。宾门纳麓,尧试舜且然,而遽谓文帝之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为《鵩赋》、《吊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颜渊不改其乐,亦三十而卒。乌得以其早亡,为有所怼乎?"(《读贾子》,载《长沙贾太傅祠志》卷二)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尽管关于贾谊遇不遇的争论非常热闹,表面看来双方意见颇为对立,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两种不同意见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要我们深究一下便可发现,争论双方对"遇"与"不遇"所持的标准并不一致。就司马迁、刘向。李善、欧阳修一方来说,他们所谓"遏"的标准,是贾谊应按文帝起初的打算那样,"任公卿之位"。既然贾谊没有登上公卿之位,还被文帝疏远,最后郁郁而死,那当然就是"不遇"。就班固。王安石一方来说,他们所谓"遇"的标准,是贾谊的一些政见到底还是被文帝采纳了,因此尽管他未至公卿,但还是"未为不遇"。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前者更为重视的是个体的目前的现实的价值,而后者更为重视的是群体的长远的历史的价值。须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往往重群体价值而轻个体价值。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首重其对社会的价值,至于其个人的富贵利达是不必过多地计较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具体反映。古人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其立论的出发点也就是首重社会价值,即强调个人应该对社会尽义务,至于个人的权利是什么,社会应该如何给个人所尽的义务相应的权利和报酬,则往往被忽略了。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所以象班固这样的正统史学家便不满意于司马迁突出地强调贾谊的个人遭遇。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证据之一,就是说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司马迁何止在"述货殖"时是如此,他在品评人物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对贾谊滴居长沙的忧愤心情的无限同情,不正是"崇势利而羞贫贱"的一种表现吗?司马迁对个体价值的这种尊重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表明,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关系,正如同权利与义务。功利与道德的关系一样,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固然离不开群体而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个体,群体也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甚至会变成一种无人身的抽象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会是驾临于个体之上的东西,而且会成为与个体相对立、压迫个体、扼杀个性的东西。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礼教"、所谓"理学",不正是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吗?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从屈原、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另一传统,即比较尊重个体价值,表现个性。抒发性灵。而后代一些文学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尽管班固论断贾谊"未为不遇",但是他们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继司马迁之后,反复咏叹贾谊的"不遇"。
总之,如果按照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相统一的观点来衡量贾谊,我觉得贾谊一生既有"不遇"的一个方面,也有"遇"的一个方面,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抹煞另一个方面。所谓"不遇"是指贾谊本来可以任公卿,结果反而被谪居长沙任太傅,这个客观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就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幸的。所谓"遇"则是指他的有些重要政治主张毕竟被汉文帝接受并实行了,有些主张虽然汉文帝未见实行、但其后继者却实行了,从而对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贾谊的确实现了"三不朽"。正是由于贾谊对汉王朝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汉王朝对他个人的给予,所以后人才更加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这种同情,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消极抗议。
(二)对贾谊思想属性的不同看法
对于贾谊思想的派别属性,历来分歧也颇多。这些分歧大体有以下几种:有论其为法家者。司马迁在论述西汉前期的思想发展形势时曾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明确地将贾谊作为汉初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夫之基本上也是持司马迁的观点,他虽然说过"谊之为学, 而不纯",但从他评论的主要倾向看,还是认为贾谊是法家。例如,他一则说贾谊"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二则说:"贾生之言曰:'使为治,劳治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欲立经陈纪,为万世法。'斯其为言,去李斯之言也无几";三则曰谊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赢政、李斯?"因此是"不闻道而只为术也"(《读通鉴论》卷二)。清人丁泰在其《论陈政事疏)中将贾谊与柳宗元、王安石相比,他说:"向使谊不遇文帝之贤,而遇任。文之党以煽之,则彼之挟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锐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废耆旧、更法度与王安石同。安石作'怀王坠马'。'贾傅死悲'之诗,盖怜其术相契也。向使谊果斥绛。灌而得行焉,则纷纷多事,能不如荆公乎?其欲削诸侯。震兵威,在当时则适与晁错同。错之说天子者,盖即其髋髀斧斤之遗意也。向使谊不死,则此术虽见抑于文帝而必求试于景帝,七国之变其为错耶?呜呼!如柳与王则名不全;如晁则身不全,故为谊幸也。"(《长沙贾太傅词志)卷一)显然,了泰也是把贾谊视为法家的。在当代,也有说贾谊是西汉前期的"新法家"者(参见萧萐父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有谓其为儒家者。最早提出此论者是刘歆。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逻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困袭??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班固祖刘氏之说,在编《汉书·艺文志》时,便将贾谊《新书)列入儒家类。班固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艺文志》)这大概就是班固将贾谊列入儒家的原因。自班志之后,历代史书之《艺文志》及目录学著作绝大多数均是将《新书》归于儒家类。
有谓其为道家者。此说见之于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六《贾谊新书》,其言日:"要其本说以道为虚,以术为用,则无得于孔子之学,盖不过以智略之资,战国之习,欲措置汉天下尔。"近人顾实云:"《尹子》。《吕览》杂议之书,平视百学,规模远矣。秦火而后,汉至文。景之世,儒业犹未起,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晁错(《汉书·食货志》载其《贵粟书》)不讳诵述神农。黄帝,颛顼,帝喾遗语,尹、吕之风,犹未沫也。"(《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又说:"杂家《吕览》、《尹子》开卷而道儒之说杂然并陈(荀卿亦称《道经》),其略标百学平等之风平?贾谊。晁错生于汉初,立言犹尔,流声未坠。"(《汉书艺文志讲疏·序》)现在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吕氏春秋》应属道家,顾氏此论也承认贾谊书中多道家言。《宋史·艺文志》将贾谊《新书》列入杂家,其原因大概亦在此。
有谓其为纵横家者。朱熹即持此说:"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未子语类》卷一三七)又说:"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同上,卷一三五)可见,朱熹说贾谊的"纵横之习"即系指"权谋功利";而所谓"这边道理"则是指"一两句仁义"。明人何孟春在《贾太傅书序》中赞成朱说,他说:"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
以上四种观点、在贾谊的著作中均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据;但如果要问到底那一种说法根据更多一些,我以为论其为法家和儒家音根据更多一些,但是贾谊既非纯粹的法家,也非纯粹的儒家,他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起来,其理由如次:首先,按班固的说法,所谓"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汉书·艺文志》)从班固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所谓纵横家大体上有二个特点一是他们都善于辞令。纵横家主要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就都是"智有过人者"的说客。过去人们在探索问答体赋的源流时,有人就曾认为"本于纵横"(参见马积高《赋史》第5 页)。贾谊的赋在赋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受纵横家辞令之影响是可能的。但朱熹说他是纵横家并非指此,二是纵横家善于"权事制宜"。权者,称量之谓。《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权事制宜"就是要衡量事物的实际情况,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这种思想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例如苏秦的弟弟苏代在《遗燕昭王书》中就有"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史记·苏秦列传》)之类的说法。而贾谊书中类似的说法颇多。但贾谊书中这种辩证法因素与其说是来自纵横家,还不如说是来自道家更符合事实。况且朱熹说贾谊是纵横家的理由并非指此。三兄班固说纵横家中之"邪人""上诈谖而弃其信"。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纵横家的基本特征,而决不是仅限于其中的"邪人"。司马迁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同上)他在评论张仪时又说:"三晋多权变之土"(《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说的"权变",班固说的"诈谖",朱熹说的"权谋",其含义是相通的。它们在政治上指搞阴谋权术,从哲学方法论来看,则是指诡辩。我们曾经指出,贾谊书中有些关于"术"的论述,但它们更多地是受了先秦法家的影响。刘勰说:"战国争雄,辩士云踊,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文心雕龙·论说》)这正是说的纵横家善于搞诡辩。汪奠基说,诡辩的特点就是"有意识地以假代真,混淆是非;或虚构事实,捏造论证:或颠倒黑白,有意欺骗。"(《中国逻辑思想史》第93 页)以这些特点来衡量贾谊的著作,找不出一个例证。由此可见,贾谊书中确然有受纵横家影响的方面,但朱熹并没有抓到;而朱熹所说的属纵横家影响的方面,在贾谊书中又找不到。因此要把贾谊归人纵横家便失去了根据。
其次,贾谊虽受道家影响颇多,但并不是道家。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比较司马谈和班固所论的道家特点,我认为贾谊受道家影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主张"以虚无为本",这是他的哲学本体论;二是主张"以因循为用",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认识论;三是"因时为业"、"因物与合"的辩证法思想;四是"清虚以自守"的"君人南面之术"。这些我在论贾谊哲学思想时均已谈过,此处不再赘述。除了这些相同之处外,我认为贾谊思想与道家还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无为,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主张有为。这一点我在分析其哲学思想时已经说过。二是他主张礼治,大讲仁义道德,而道家则与此相反。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同上,第十九章)。班固在介绍了道家的特点之后说:"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汉书·艺文志》)重仁义与弃仁义之间,区别是十分鲜明的。尽管到了秦汉之际的黄老帛书,吸收了儒家的某些德政的思想,如"主惠臣忠"(《经法·六分》),"兹(慈)惠以爱人"(《十六经·顺道》),"节赋敛,毋夺民时"(《经法·君正》)等等,但却从不谈礼。这说明贾谊的仁义礼治思想与老子是对立的,而且与黄老帛书的德政思想也还存在着原则的区别。正是以上这些区别的存在,使贾谊的思想不完全同于道家。
贾谊的思想继承了许多法家的传统,但他又不是纯粹的法家。贾谊对法家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和法家一样讲法、术、势。班固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可是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与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周末风俗》)这是说法家是不讲礼制的。例如商鞅就说过:"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是否意味着班固所说的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是不符合事实的呢?我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班固所说的"礼制"也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史记·太史公自序》)。而这种思想在《韩非子·忠孝》一篇中是表述得很清楚的。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工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这一说法与儒家的"三纲"之说是完全一致的。在第二章,我们曾用许多材料证明贾谊继承了法家法、术、势的思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对法家"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的思想是领会颇深的。他说:"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又说:"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阶级》);"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服疑》)这一切,都说明必须明主臣之尊卑,等君之势。二是贾谊继承了法家重耕战的思想。例如李悝说:"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綦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见《说苑·反质》)这一观点在贾谊的《瑰玮》一文中就被明显地继承了,不仅思想一致,而且语言也相似或相同。如贾谊说:"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又说:"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势安得不寒。"这说明,贾谊对法家的一些基本观点都是继承了的。为什么又说他不是纯粹的法家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汉书·艺文志》)贾谊在他的著作中除了《过秦》这一专文之外,还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批评秦王朝"仁义不施","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正是这种批评,使他与先秦法家区别开来。如果法家是主张"以吏为师"的话,贾谊则实质上是主张"以师为吏",看他将"师"列为"王者官人"的第一等(《官人》),他在《傅职》中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诏工、太史之职责,均是首重师傅之责。如果说先秦的法家是"去仁爱,专任刑罚"的话,那么贾谊则是仁爱与刑罚兼重,且强调以礼为先。他说的"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制不定》),就正是仁义与法制并重。他说:"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治安策》)这表明贾谊是把教化置于法令的优先地位的。如果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因而使"亲亲尊尊之恩绝"(《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话,那么贾谊的"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阶级》)则显然是为了"别亲疏"、"殊贵贱",从而显示"亲亲尊尊之恩"。这一切都说明贾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家。
最后,贾谊也继承了儒家的一些基本观点,但又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班固说:"懦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班固所论儒家的这些特点,在贾谊书中均可找到,在本书有关章节中我们也曾论及。我之所以说他又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就是因为如前所述,他吸收了各派的长处,特别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的一些长处。正是这些新的因素,又使他区别于本来意义上的儒家。
由此看来,贾谊思想的确是相当复杂的,因而历来人们对其思想的派别属性争论不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为什么在争论中任何一种主张都无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赞成呢?原因就在于人们在研究贾谊时,往往忽视了其思想的过渡型色彩。须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政治原因,如统治集团的一时爱好等加以解释的问题,而是有着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支配其间。这种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同人们的个体认识一样,也总是由片面到全面、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实质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吏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战国时诸子百家的目的都是"为治",即为了经世致用。但为什么他们所陈述的方法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认识有深浅之别,有全面与片面之不同。既然是认识问题,那么这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便可以通过讨论和实践而逐步趋近一致。自从战国末期以来,从百家争鸣到百家逐步融合、汇通,再到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便是这种逐步趋近一致的表现。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荀况到贾谊之间各主要学派或人物的情况,便可以发现这种融合的确是存在的。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学说虽以儒家为主体,但汇集了各家之所长,成为对百家争鸣的理论总结。在天人关系上,他继承了道家学派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克服了儒家和墨家人格天的唯心倾向,在礼法关系上,他把法家的法治思想引人礼制之中,使礼法结合,王霸并用;对其他各派的一些合理因素也无不加以吸收。吕不韦主持修撰的《吕氏春秋》则主要是站在道家立场"兼儒墨,合名法"。高诱说,《吕氏春秋》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吕氏春秋·序》)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它汇合百家的倾向。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虽然他是以法家的代表人物的面貌而出现的,但他的哲学思想很明显地继承了道家。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尽管韩非突出地强调法、术、势,但他又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施行法、术、势的目的是为了"利民萌便庶众"。《韩非子·问田》记载堂谿公向韩非提的一个问题:"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韩非答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庶众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由此可见,韩非反对礼治,提倡法治,就其主观愿望来说,还是认为是一种"利民萌便庶众"的"仁智之行"。这就说明,韩非思想也是综合百家的历史产物。西汉前期统治者推崇的黄老道家,其本体论虽是坚持道家的"道",但其政治哲学却吸收和继承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不仅如此,黄老道家是刑德并称,并主张先德后刑。《十六经·姓争》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缨缨(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十六经·观》说:"先德后刑以养生","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黄老道家把德放在刑之前,并将"德"解释为"兹(慈)惠以爱人"(《十六经·顺道》),"节赋敛,毋夺民时"(《经法·君正》),这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德政思想的影响。西汉初期著名思想家陆贾在总结了秦王朝实行严刑峻法的失败经验之后,进一步把《黄老帛书》中"先德后刑"的思想发展成以仁义为本。他说:"事逾烦天下愈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是陆贾并不是完全反对刑法,他只是认为"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新语·无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先秦至西汉前期思想史的这样一种圆圈式发展的趋势:苟子是这个圆圈的起点,他站在儒家的基本立场综合百家,十分重视礼治。其学生韩非和李斯则否定了儒家,成了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而秦王朝的实践则证明单纯的严刑峻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便接受了刑德结合。先德后刑的黄老思想。陆贾提出"仁义为本",贾谊突出地强调礼治。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已进入一个新的否定,即对法家对儒家之否定进行再否定的过程。当然,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到董仲舒才最后完成,但从陆贾和贾谊的思想中已经明晰地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转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历代正史的艺文志和目录学的著作将贾谊归人儒家类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陆贾和贾谊思想的这种向儒家的复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即综合道。法各家思想成就上的复归,按照侯外庐的说法叫"内法外儒"(《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63 页),按照张纯和王晓波的说法叫"阳儒阴法"(《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第249 页)。"此处所言的'阳儒阴法'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为以懦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也有'法家化,的儒家。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故儒家'言',而法家'行'。三为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同上)尽管这段话是针对整个汉代社会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贾谊。例如贾谊对礼的论述便是"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因为他说的"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正是法家的"尊主卑臣"之论。又如他说"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则实际上是在主张"儒家'言'","法家'行'"。至于贾谊的"儒家的理想"则主要表现在他高谈尧舜禹汤,而"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则突出的表现在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主张曾被王夫之斥为"阳予阴夺"之术。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