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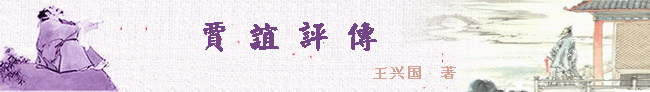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三 尚贤的人才思想
陆贾和晁错都认为,最高统治者要使自己的统治稳固,就必须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陆贾说:"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辅政》)晁错说:"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举贤良对策》)。他们的人才思想,大体包括任贤的重要性、选贤之标准及方法等方面。
(一) 论任贤的重要性
陆贾对任贤重要性的认识,是从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说: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然处高之安。乘克让之敬,德佩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缺覆(他本"缺覆"作"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辅政》)
陆贾在这里再一次向刘邦回答了"秦之所以亡"的原因,就是所任非人。他关于"杖圣"、"杖贤"、"杖仁"、"杖义"、"杖谗"、"杖贼"的说法,突出地表明了人材的质量对政治建设的密切关系和极端重要性。对此,晁错也有类似的认识。他说: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举贤良对策》)
陆贾和晁错的这些话,都是为了劝诫人君,在选择人才时,要力求选择那些圣者、贤者、仁者、义者,而力避那些谗贼之徒。
可是那些谗贼之徒又不是可以一眼便能识破的,他们往往大好似忠,美言似信,欺骗人主。而人主要能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就必须自身具有很强的分辨能力,首先自己应该是一个贤者、智者。所以陆贾说: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知之君,孰能别其形?故尧放驩兜,仲尼诛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为之倾;惟尧知其实,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郑儋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辅政》)
此处所说的郑儋,《左传》作郑詹,又作叔詹,并说他是郑国执政大臣,是一个好人,而《谷梁传》、《公羊传》则说他是一个"微者"、"卑者"、"佞人"。但据《春秋》所载,齐人执郑詹和郑詹归鲁是庄公十七年,而鲁国之"乾时之耻"是在庄公九年,因此陆贾所说的"郑檐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不知何所据。尽管陆贾所说可能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①他是据《谷梁传》的说法,将郑儋说成"佞人";②他引用(或编造)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从而进一步说明任贤的重要性。正如唐晏所说:"此盖讥鲁之因循不振耳,非必因詹致败也。"(《新语校注》)
(二)选择人才的标准及方法
前面所引陆贾的"杖圣"、"杖贤"、"杖仁"、"杖义"和"杖谗"、"杖贼",同时也说明他是以道德为标准,将人才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圣、贤、仁、义者,这是为他所肯定的人才;一类是谗、贼之徒,这是为他所否定的人才。除此以外,陆贾还将人才按其气质、性格、智愚等分为若干类。他说:怀刚者久而缺,持(亦作"恃")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促急(亦作"疾")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辩者不可以说众??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辅政》)可见,陆贾比较欣赏的人才,是那些"持柔者"、"迟重者"、"温厚者"、"柔懦者",而特别反对那些"小辩"、"小慧"之人。他的这种人才标准,从方法论来说显然是继承了老子"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的观点,但从政治观来说,则是继承了儒家的"仁义"思想。
晁错的人才标准则更加接近儒家的观点。他说: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纵)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家者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无邪辟之行,外无骞(亏损)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举贤良对策》)
这里,晁错既从"自行"又从"事君"两个方面对人臣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人才标准。他所说的"方正之上"的"方正"一词最早出自法家。《管子·明法》云:"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韩非子·奸劫弑臣》云:"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可见,"方正"一同原意指持法端平正直。在汉代,文帝把贤良方正作为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方正"一词与"贤良"一词连用,便具有更多的道德意义。我们看,晁错所说的"方正之士",固然包含有持法刚平正直之意,如"奉法令不容私",但其他一些条目则更多地是属于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他的人才标准更多地接近儒家。
关于如何选拔人才,晁错现存著作中不见论述,但陆贾的《新语》中却有所论述。他认为选拔人才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要为阿谀谄佞之徒所惑,也不要对那些行不苟合、言不苟容的正直之士看不顺眼。陆贾分析了那些阿谀谄佞之徒之所以能得势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上有好者。他说:"夫举事者或为善而不称善,或不善而称善者,何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故行或合于世或顺于耳,斯乃阿上之意(亦作"义"),从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因其刚柔之势,作为纵横之术,故无忤逆之言,无不合之意(亦作"义")者。"(《辨惑》)这就是说,统治者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去选择人才,那么势必只能纠集一些阿谀顺旨的谄佞之徒在自己的身边。陆贾认为那些正直之士往往是"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的,他以孔子弟子有若为例,说有一次鲁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由于有若这种损上而益下的主张不符合哀公的心意,所以没有被采用。对此,陆贾发挥了一番议论,他说: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为益国之义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敢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行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夫邪曲之相衔,在桡之相借(亦作"错"),正直故不得容其间。(《辨惑》)
由于正直之士不苟合于世,其逆耳忠言也往往使统治者听不进去,所以统治者要招纳贤才就不仅要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而且要扶正压邪,亲贤臣,远小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一些谄佞之徒就会乘机打击正直之士,而自己互相吹捧,互相抬轿子,从而做到"无高而不可上,无深而不可往"(同上)。其次,要防止"党辈"的干扰。陆贾说的"党辈"指由于政治上特殊利益而结成的一些顽固的帮派小集团,他们为了自身卑鄙小集团利益控制舆论,利用"众口之毁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力黑",从而达到打击一些人,抬高一些人的目的。为了说明"众口之毁誉"的厉害,陆贾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赵高以鹿驾车随秦二世出行,二世问他:你为什么驾鹿?赵高说:是马不是鹿。二世说:你错了,怎么以鹿为马。赵高说:我没错,您如果不信,可以问各位大臣。结果大臣中有一半人说是鹿,一半人说是马。二世听了大臣们的这种回答,对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了。陆贾由此得出结论:"夫马鹿之异形众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也,况于暗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辨惑》)
陆贾认为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用来对待人事,其危害性就更加严重。
他说古时候,有一个与曾参(孔子弟子)同名同姓同时的人杀了人,结果有人给曾子母亲报信,说她儿子杀了人。第一次来报告时,曾母根本不相信,照常在织布。过了不久,又有人来报告曾母,说她儿子杀了人,曾母还是将信将疑。待第三个报信人来过之后,曾母不得不赶紧将织布的梭子丢下,翻越自家房外的围墙逃走。陆贾说:"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言之者众,夫流言之并至,虽真圣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陆贾又指出,鲁定公之所以不能用孔子,就是因为"拘于三家,陷于众口","内无独见之明,外惑邪臣之党",结果"弱其国而亡其身"。因此,陆贾得出的结论是:"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也。"要使日月重光,就得有"神灵之化,罢云霁翳"。同理,只有当上有"明王圣主"、下有"贞(原文为"真",据唐校本改)
正诸侯,诛锄奸臣贼子之党,解释凝滞纰缪之结,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慎微》)三、选贤不能局限于公卿贵戚之子弟,更要注意那些隐居穷泽的"不羁之才"。陆贾说:夫穷泽之民,据犁嗝报(唐晏说"嗝疑是之假借,《说文》:裘,里也"。又云"报当作服")之士,或怀不羁之才,身有尧舜禹皋之美,纲纪存乎身,万世之术藏于心,然身不用于世者,□□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贵戚之党友,虽无过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辅助者强,饰之者巧,靡不过也。(《资质》)
由于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条件不同,有才能之士或不用于世,而平庸之辈倒有可能飞黄腾达。陆贾认为,造成人才发挥作用的机会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那些考察选拔人才的"视听之臣"缺乏能力。他说: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日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资质》)陆贾这段话,说明了求贤和近贤对于国家安危的极端重要性,而人君要真正做到求贤、近贤,就必须充分发挥观听之臣的作用,要求他们认真了解下情,推举圣贤之才加以重用。
(三)陆、晁任贤思想的历史渊源
尚贤和任贤,在我国有着古老的传统,但在先秦时期,不同的学派却对它采取不同的态度。《尚书·咸有一德》中记载了传说是商工大臣伊尹的这样一句话:"任官为贤才,左右惟其人。"原注:"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才不可任;选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可见,在商代任贤思想即已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便是极力推崇贤人政治。据《论语》记载,仲弓做了季氏宰之后,向孔子请教如何施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又问:怎样去识别贤才并把他们提拔出来呢?孔子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同上《为政》)孔子的这些说法,显然是对《尚书》所说的"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古代,明确提出"尚贤"这一概念的是墨家。墨子认为"尚贤为政之本",他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使)能。"(《墨子·尚贤中》)可见,孔墨两家在尚贤这个问题上有着相通之处,所以墨子的弟子有见于此而曰:"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远)年之言也。"(同上)这段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尚贤思想的久远。
道家和法家对尚贤思想则持批判态度。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第三章)老子之所以反对尚贤,是认为贤者必有为,而真正的"圣人"是"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同上,第七十七章)的,即有了功劳而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聪明才干;真正的智者是不敢为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同上,第三章)。法家商鞅也不主张尚贤。他用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远古的时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就必然造成亲疏之别,爱私则必然存心好险。有了亲疏之别和好险之心就必然发生争讼。如何解决争讼呢?于是出现了贤人,贤人创立中正之道,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就喜好仁慈了。这时人们便抛弃了亲亲的观点,而树立了尚贤的观点。贤人虽以爱人利人为职责,但由于没有必要的制度,所以久而久之同样出现了混乱。这时圣人便出现了。圣人定分、立禁、立官、立君,使社会进入有法制有秩序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抛弃尚贤而尊重贵人。所以商鞅的结论是:"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可见商鞅这套理论也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它为法家崇尚法治,以吏为师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韩非继承了他的思想。韩非说:"废常上(尚〕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然而,韩非并非是根本不用"贤"字,不过他赋予它以与儒家完全不同的解释。他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的一个故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姜太公吕望封齐时杀了两个隐士,原因就是这两个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周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去责问吕望:"夫二子,贤者也,今日享国而杀贤者,何也?"吕望在回答周公的责问时,用法家的刑罚耕战理论把上述二隐士的话批了一通之后,讲了这样一段话:"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己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由此可见,周公与吕望对贤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周公的"贤"是指其人之品德高尚,而吕望的"贤"则是指甘为人君的驯服工具。周公的观点代表儒家,吕望的观点则代表法家。
通过以上分析再联系陆贾的"以圣贤为杖",贾谊的"上贤而贵德",晁错的"求贤以为辅翼",他们继承的更多的是儒家的"举贤才"和墨家的"尚贤"思想,他们对"贤"的理解更多地接近懦家而不同于法家。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