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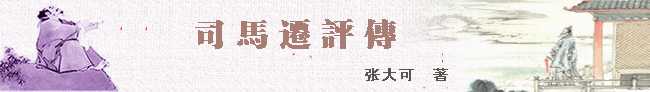
|
三、论六家要指
《论六家要指》是一篇杰出的历史哲学论文,它反映了汉初黄老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司马谈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法宝。
1.《论六家要指》写作的时间和背景。
秦汉政治大一统,要求文化思想与它相适应。所以,综合百家学说,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秦始皇相吕不韦集门客撰述《吕氏春秋》就做的是这种统一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倡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原因亦在此。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的动机,以及作于何时,弄清这一背景,是领略其精微大义的关节。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于元朔五年。理由是:"案《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对于司马谈的写作动机,郑鹤声说:"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悻者,言好儒而轻道也,故于道儒两者,辨之尤切。"郑氏从学术旨趣立论,揭示司马谈写作动机,深得《要旨》精髓,而系于元朔五年指弹公孙弘,却是立论未周。因为古代并无公开论坛报纸、刊物,开展学术论争;而独尊儒术体系确立以后,也不允许有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对峙,列国纷争,各国引进人才,因而才有百家争鸣局面,各派学说,自立门户,传艺授徒。自秦汉统一,政治一体,再无争鸣背景。文景时博士并存百家,尚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即使这时,较大的思想斗争,总是展开在庙堂之上,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例如景帝时辕固生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武帝建元元年王臧、赵绾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等,表面是思想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又如,文帝时贾谊写《过秦论》、《治安策》,贾山作《至言》;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等,都是上奏朝廷,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强烈政论。如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针对公孙弘请立五经博士弟子,必上奏朝廷,形成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司马谈还能做太史令吗?显然不能。而且《太史公自序》亦未作这样的记载。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③,认为司马谈在"得知窦大后第一次战胜尊儒派之后,立即写了《论六家要指》,核心是完全肯定道家","是与窦太后思想合拍的",否则司马谈"在建元时是不可能让其入仕的"。照此说来,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岂不是赶潮流以为入仕的敲门砖?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只能得意于一时,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岂能容他?吉春《年谱》的说法,仍可商榷。《太史公自序》揭示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我们认为《论六家要指》应作于元狩元年(前122),实质的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而非上奏朝廷的政论。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述史计划是上起陶唐,下迄获麟。获麟即元狩元年。这一断限说明司马谈着手述史在无狩初。他的《论六家要指》,就是述史的宗旨和宣言,当作于述史之始。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思想体制已经确立。儒生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封平津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竟致于"靡然向风矣"。尊儒崇儒从上到下成了一边倒。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文景时代的无为政治为汉武帝的多欲政③ 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
治所代替。全国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而且翻江倒海式的沸腾起来。司马谈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以写了《论六家要指》。不过矫弊也罢,警告也罢,都只是学术上的自我磨励,而不是上奏朝廷,卷起政治斗争。
按照这一认识,正是崇儒之风的大气候形成,这才促使基于道家立场的司马淡写了《论六家要指》。元狩元年,比郑鹤声认定的元朔五年推后只两年,但形势不同。由于元朔六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尊儒之风从量变发生了质变,"靡然向风矣"。更主要的是司马谈着手述史,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2.《论六家要指》的内容。
《要指》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它五家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褥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过分吝啬,尊卑无别,"俭而难遵";但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言尊主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这些评论,把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在正统思想家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受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的强烈批评。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论六家要指》所论的"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样的"道",尚贤、尚法、尚刑名,不非毁礼义,不排斥儒学,既非先秦老庄,亦非汉初黄老。《要指》开宗明义,"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实,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
3.《论六家要指》的价值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司马谈之前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是诸于中已开论学术分派分家之例。《荀子》所论,凡六说十二家,《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为六。在司马谈之后,有刘欲《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分先秦学术为九派,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这九家,不过是司马谈所论六家,加上纵横、杂、农三家而已。这三家不足与前六家相颉抗。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吾于刘、班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挚当时学派之大纲,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精,以此为最。"显然,《史记》首创孟荀、老庄申韩及孔子学术史传,阐述学术源流,《论六家要指》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论六家要指》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特别表现在对阴阳家的评论上。阴阳家的众多忌讳只不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阴阳家所讲的四时之大顺,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司马谈又认为神形离则死,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但司马谈并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认为神形是两个东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这是二元论的观点。司马迁深受其影响,故他的历史观基本是二元论①。在方法论上,《要指》把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言而喻,得益于《要指》的两点论思想。又,在儒道互绌的激烈斗争时代,司马谈兼收并蓄,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完成了包容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是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的。至于《要指》将儒道两家对比评论,实质是将汉初政治与武帝时期政治对比评论,认为无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这对于司马迁最后定稿《史记》是有很大影响的。
司马谈的其他著作,《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太史公《万岁历》一卷。"其书已佚。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有司马谈《祠后土议》、《立太峙坛议》、《论六家要指》三文。至于司马谈作史,详本章第五节。① 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1989 年4 月三秦出版社出版。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