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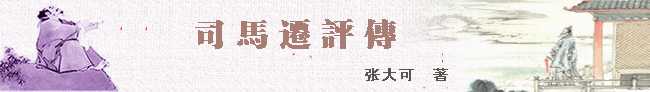
|
一、《史记》完稿与修订
1.太始四年,《史记》基本完稿。
《史记》完稿,《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司马迁计点篇目字数寓有深意。他在《报任安书》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部,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计点篇目字数,表明自己十分美满地在有生之年完成了雪耻的心愿,发愤之作大功告成,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此其一。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著《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效《春秋》,是非裁夺一出于司马迁之手,"俟后世圣人君子"评说,增一字与减一字都是不可以的,表现了司马迁的自信与超越,追步圣人毫不逊色!此其二。此外,司马迁留下的这一篇目及字数统计,可为今天研究《史记》断限与"十篇缺"的重要标尺,这或许是司马迁先知先党的预设,也或许是他非始料所及之事。司马迁死后,两汉儒者竟相续补,或遭当路者删削,这篇目字数的统计成了《史记》一书无形的护法神。《太史公自序》作于何年,无法考知。但司马迁却在《报任安书》中透出《史记》基本完稿的消息,考知《报书》的写作时间,就大体可知司马迁的写作进程。《报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括号内"上计轩辕"等七句据五臣注《文选》本补入。计,借为记。这几句总括《史记》五体篇数与《自序》相符,所以它透露了《史记》已基本完成,但还没有最后定槁。试与《自序》的总括文字作一对照,就可看出问题。
《自序》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对照两段文字有三点不同:第一,《史记》五体的编次顺序不同。《报书》序列为:表、本纪、书、世家、列传;《自序》排列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与今本《史记》吻合。第二,《报书》未定书名;《自序》定名为《太史公书》。第三,《报书》无字数统计,《自序》总计全书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三点不同,说明《报书》作于《史记》即将完稿之时,而早于《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作《报任安书》之后,仍在继续修订。
《报任安书》的内容,本书第五章已作了剖析,它是司马迁痛定思痛的回溯,正因为《史记》已大体完成,他才写了这封回信,向知心朋友一倾忍辱著书的郁闷,并表达他的抗争精神。所以,考证《报书》的写作时间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它对于了解司马迁的写作进程及推知卒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说。
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认为写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征和二年巫蛊事发,太子刘据起兵讨权臣江充。当时任安任北军使者护军,太子授节给他,命令出兵助战。任安受节却闭门不出,首鼠两端。事平,任安被钱官小吏揭发,处以腰斩。赵翼根据"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等语,认为任安在巫蛊案中下狱,于狱中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推贤进士",援救自己。清包世臣认为"推贤进士"四字是任安征和二年蒙罪后求援的隐语①。今世时贤又多解"会东从上来",为征和二年司马迁扈从武帝由甘泉回长安。据此,任安致函司马迁和司马迁回信任安,均在征和二年。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则根据《报书》中"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这几句话推定《报书》作于太始四年。因为《武帝纪》载,武帝出巡,在一年中既东巡,而后又西上雍,只有太始四年。又据《任安传》载汉武帝语"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云云,任安于太始四年另犯有"不测之罪",而非巫蛊案。依照王说,我们可以推知,任安在太始四年所犯"不测之罪",终因司马迁营救而获免。正由于司马迁营救了任安,所以才在《报书》中诉说衷肠,让任安做两手准备,或自裁,或侥幸,但对喜怒无常的汉武帝不要抱幻想。按王国维说,两人通信在太始四年,早于征和二年两年。
按核事实,王说比赵说为优。首先"会东从上来",方位词"东"的用法,叙事者若系离去才能解为"往东"①;若系归来,只能解释为"自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可为此作注脚。司马迁接任安信,"会东从上来",即正赶上从巡武帝自东边回长安来。太始三年武帝东巡海上;太始四年,武帝东封泰山,五月还京师。任安致函司马迁必在这两年,在太始四年可能性最大。因封禅泰山是国家大事,巡幸海上是求仙。"推贤进士"属国家大事。元封元年封禅泰山,此后五年一修封成为定制。太始四年修封泰山是例行典礼,任安选此时机劝勉司马迁"推贤进士"顺理成章。包世臣认为"推贤进士"是任安求援的隐语,此说甚辨,但与情理事实不符。试想任安犯了死罪向知心朋友司马迁求援,却转弯抹角用隐语;而司马迁却迟迟不回信,直到临刑前才回信,不但不谈救援之事,倒诉说起自己的衷肠,还在"推贤进士"隐语上大做文章,这种滑稽喜戏,绝非任安、司马迁两人之所为,又,武帝诛杀任安,应在征和三年春夏之交。巫蛊案武帝视太子为叛逆而大封功臣,直到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武帝思子改变了对任安的态度,才得以被小人乘间。任安、刘屈等人均被诛杀,这是征和三年的事。当然,由于史事久远,具体时间缺载,合理推论也难免有差错。也有这样的可能,任安致函司马迁在太始四年,司马迁回信在征和二年,因"阙然不报",两信间隔可以是几个月,也可以是一两年。那就存疑待考吧。本书依从王说。
2.司马迁对《史记》的修订。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天汉三年他受祸之时"草创未就",即《史记》一书尚未完成。《报书》又说:"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则是对已成之篇的修订润饰。这两项工作当是交叉进行,太始四年以后则主要是最后的编定工作。由于史料无征,我们难以查考《史记》篇目的写作编年,但从篇中所透露的生平印记,特别是李陵案的余响,可以大体推测出司马迁作史阶段及修订内容,并从中领略他的发愤精神和诗人气质。先说修订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1)调整篇目与编定次序。《史记》规划,元狩元年起司马谈已发端述①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序》。
① 《艺舟双揖·复石赣州书》。
作,元封三年司马迁相继撰述,至太初元年开始定稿,大约《史记》规模已粗具。天汉三年,司马迁受祸,思想立场从温和刺讥转到激烈抗争,对全书篇目以及已完成的篇目内容必有相当大的调整,用以寄发感慨,留下李陵案的余响。象酷吏、游侠等篇,感情愤激,必是写于受祸之后。试作简要分析。《酷吏列传》,集中写武帝一朝的酷吏,他们一个比一个苛暴,而"上以为能",讥刺刻骨。司马迁恨透酷吏,写他们的下场一个个不得好死,杀头,弃市,族灭!而直接迫害司马迁的杜周,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既苛酷又贪婪。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鞍辔不全的马,等到他做御史大夫时,子孙尊官,家资累巨万。杜周善终,死于太始三年,司马迁独不书卒,留给读者去悬想,言外他不配有善终的下场。《游侠列传》为干犯朝廷纲纪的侠义之士立传,开篇议论立传理由:"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寄寓了对理想友谊的向往。司马迁一则曰:"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再则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司马迁之横遭极刑,"交游莫救",在此发出对真挚友谊的呼唤与渴求,不是跃然纸上吗!《伯夷列传》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质疑,其中更多有愤世之言,如"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者,不可胜数也",是极为显明的李陵案余响。这些篇目不仅写成于受祸之后,更有可能是受祸后调整篇目新增加的内容。《管晏列传》亦以议论为主,不载传主事功而载轶事。这样选材,便于抒发议论。本篇论友道,论不羞小节,论荐士,慷慨激昂,可以说是司马迁写的一篇知己论,亦当是李陵案之余响。又《魏其武安侯列传》,为平庸外戚作传,深刻地揭露了西汉盛世下的宫廷斗争,描写了上层统治集团的互相倾轧,表现了对专制主义黑暗政治的批判和谴责。笔锋犀利,语言简洁,人物富有个性,对话宛然,声口毕肖。此篇立意与笔力,非受祸之后不能写出。
至于全书编次,参阅本书前述第六章关于"五体篇数及序列义例"一节,既然《史记》五体结构是一个人工创作的系统工程,在全书完成后再做精意编排,那是不言而喻的。
(2)抒愤寄托,鸣写不平。司马迁受祸,"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故于书中极力抒写,借他人事迹寄寓感慨。这是修订的主要内容。抒愤寄托,首推《屈原贾生列传》。首先,司马迁的人格、遭遇及写作心情,与屈原两人相似而相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结果"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结果横遭口祸,被刑蒙耻。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述往事,思来者",故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的"怨",借以肯定《史记》的激扬抒愤精神。其次,司马迁强调《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战斗精神,正表明了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敢于触犯时忌,讽喻当世的黑暗。司马迁二十壮游就寻访屈原的足迹,感怀凭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所以屈原传记,当是早年所作。而今本《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又必为受祸后重新精意撰写,饱含深厚感情塑造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怨"而"愤"的人物形象,托以自悼。清人李晚芳就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①其次,当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不听昏庸楚王之乱令,违犯君臣之"义",逃往吴国,借兵报仇,司马迁不加非难,反而高度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是真正的男子汉,"烈丈夫",表现了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赞扬忍辱负重,困危发愤精神的有《虞卿列传》,说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范睢蔡泽列传》,说范蔡二人不困厄不能激发智慧以取卿相;《季布列传》,说季布斩将夺旗,是一个壮士,然而被通缉却为人奴不死,受辱不羞,终为汉名将,称得上是"贤者诚重其死"。这些议论,正是司马迁忍辱负重精神的寄托。①司马迁写人际关系,痛恶"以势利交",慨叹世态炎凉,在许多篇章中明显地渗透着他自己的人生体验①,并把他的爱恨强烈地在赞论中表现出来。《卫康叔世家赞》云:"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在阶级社会中,权力与利欲扭曲了人性,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挡不住利害的冲突,何况于朋友之间的势利交!司马迁对臣弑君、子弑父、朋友反仇等等恶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司马迁并没有丧失对真善美追求的信念。他把吴太伯立为世家之首,塑造了吴太伯与延陵季子在竞相夺权逐利的世风背景下拱手让国的典型形象。如果一个连天下都可相让的人,他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以抛舍呢?司马迁在《张耳陈余列传赞》中,强烈谴责张耳陈余以势利交的同时,倾心赞美吴太伯、延陵季子相让的仁心,这是有意安排的强烈对比。《主父僵列传》谴责趋炎附势的"宾客以千数",同时赞颂了不怕忌禁杀头而收葬主父 偃的长者孔车,这也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强烈对比,用以抒发"交游莫救"的愤世情怀。
在《史记》中,司马迁抒愤自况的例子无处不在,它表现了司马迁坦诚的胸怀,爱恨分明的感情,喜怒哀乐发自真情。他恨酷吏,就大声斥呵:"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他敬慕李广的为人,就热情赞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忻慕晏子荐贤,情不自禁说,愿"为之执鞭"。他所写《屈原列传》、《伯夷列传》,语言如同诗一样回肠荡气,富于激情。清恽敬说:"今读伯夷、屈原等列传,重迭拉杂,及删其一字一句,则其意不全,可见古人所得矣。"②如关于《离骚》的写作动机和主旨,就重迭复沓以致意。一则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再则曰:"信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三则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司马迁的评说,也是"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唱三叹,把作者对屈原的敬仰,同情与对邪曲的愤慨,倾注于笔端,字字句句都迸发出感人的力量,所以增一字减一字都是不可以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炽烈真挚的诗人气质与情怀。他对于自己所写的人和事,是倾注了全力,用尽了自己全部的① 甘泉宫在长安北面偏西,由甘泉回长安建章宫,与其说往东,宁勿说往南,充其量只能说往东南行,按地理位置也不能说"往东"。
① 《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
① 参阅本书前述第五章"发愤著书"。一节中有关内容。
② 参阅本书前述第八章"道德观"一节中关于痛恶"以势利交"的有关内容。
赤诚。这就是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发愤精神。可以推想,渗透于《史记》许多篇章的抒愤情怀,如果不是晚年反复修订,不可能具有如此的深沉和纯熟。至于只在篇中插入或只在论赞中发出的抒愤自况语言,显然留下修订痕迹。如《张耳陈余列传》的赞语就是一篇典型的例证。
(3)附记太初以后大事。内容涉及十六个篇目,凡二十二人,集中在李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上,可以看出是司马迁的精心布局,各体照映符合若节。十六个篇目为:书一篇,《封禅书》;年表四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问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三篇,《外戚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列传八篇,《韩信卢绾列传》、《樊郦膝灌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所记二十二人,其中记天汉间事六人:尹齐之死,大宛立昧蔡为王,李陵降匈奴,汉武帝封禅,梁平王刘襄卒,杜周为御史大夫。记太始间事一人:汾阳侯靳石,太始四年纵奸失侯。记征和间事十人:征和二年坐巫蛊案被族者七人:卢贺,公孙贺,韩说,曹宗,田仁,公孙敖,赵破奴;征和三年三人:卞仁坐祝诅国除,李广利降匈奴,刘屈因巫蛊斩。记武帝未后元间事五人:郦终根,秋蒙,李则,唯徐光,四人均坐祝诅上,国除,乃巫蛊案之余波;韩曾复封为侯,因韩说在巫蛊案中无辜被杀,司马迁特记其后嗣侯。这些人和事集中在巫蛊案和李陵案两件大事上,寓有微旨。司马迁受李陵之祸,故详记李陵与贰师两将军投降匈奴始未,让历史证明武帝偏袒李广利是完全错误的。故《匈奴列传》记事止于征和三年贰师李广利降匈奴,又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征和三年栏补上一笔"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特别醒目。《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太初以后见侯三十一人,司马迁只记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二侯终始,因均与巫蛊案相关连。汉武帝求神拜仙,迷信猜忌,导致了晚年的巫蛊案,葬送了太子,自是一特大事件。司马迁以李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终结武帝一生行事,本是太初以前记事的延续、互见,其势不得不附载。也就是说,李陵案与巫蛊案是司马迁修订《史记》,附记太初以后事的一条明显的脉胳。
(4)补载或修订太初以前史事。《史记》中有十二篇记载太初以前史事而有"武帝"字样,不似后人窜乱文字。《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表列汉武帝史事,起首皆为"孝武建元元年"。又,在诸侯王表中,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巳下书武帝三子立王,均书"武帝子"。《孝景本纪》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外戚世家》载卫皇后一节,称"武帝"。联系前后文字,这一节是补插文字,显然是后加的,写于陈皇后之前。而在陈皇后一节文字中,又已经写了卫皇后事迹。《卫将军骠骑列传》,附载的公孙贺等十六人,一律书作"武帝",显然是补写。此外,《屈原贾生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李将军列传》、《主父偃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均有"武帝"字样。可以说这是司马迁在昭帝之初仍在修订《史记》留下的痕迹。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