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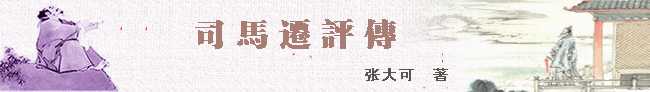
|
一、《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
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为私修之史,"藏之名山"是恐其被禁失传,故将正本藏于深山,只将副本留在京师,所以说"副在京师"。此说本之于《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颜氏云:"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颜师古注只是一个错误的猜测。
凡持藏于名山的论者,皆忽略了司马迁以大史令官守著书这一事实,而把《史记》等同于今天的个人私撰,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容的。如果说《史记》为官修书,它又有别于唐以后设馆修史之书,不是成于众手,而自始至终出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之手,自成一家之言。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国家设立书局,而是非裁夺之权一出于主编司马光之手,它是官修,还是私修,难以作截然判断。两司马之书,既是官修,又是私撰,折衷而言之,曰官助私修,即从创作角度说,两司马之书都可说是私修,而形式则是官书,尤其是《史记》正是这样的一部书。
官修之书则要上奏朝廷。《史记》书成,也是要上奏朝廷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臣迁"云云,就是《史记》正本上奏朝廷的铁证。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有汉武帝削除景纪、武纪之说,亦可说明司马迁所著书要上奏朝廷。否则,汉武帝何得而削之哉!
《史记》书成,既然要上奏朝廷,所以《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于名山",实为藏于官家书府之雅称,《史记索隐》云"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并引《穆天子传》郭璞注为证,郭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司马贞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正本藏于名山,京师指朝廷,其副贰本留京师,堂堂之尊的皇帝岂肯甘心。所以颜师古注是不能成立的。
官府藏书,不易流布,故司马迁抄留副本于京师家中。司马迁传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挥在宣帝时向外传布。《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史记》行文内容也留有官书痕迹。如《项羽本纪》,既尊羽为本纪,而记述用汉之纪年。《太史公自序》行文也有"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楚人迫我京索","维我汉继五帝未流,接三代绝业"等话头,以"我"与"楚人"对举,又称"我汉",这俨然是官修史书的史臣口吻。前引《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臣迁谨记"云云,则完全是史臣上奏皇帝的格式。有人认为,"西汉没有真正的史官",东汉班固私修国史,被人告发,东汉明帝审读已成之篇,而后才召班固为郎官,"典校秘书",后又为兰台令史,"著作东观","这才是编修后世所谓国史的开始"。论者于是断言,西汉太史令,职掌星历为主,"文史为次,实际上连次要都说不上",因此,"司马迁不是史官,也不是世袭史官的后嗣",所以《史记》是私人著作,而非官书①。上引论点是割断历史的断章取义,只见其表,未究其里。中国史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①。夏商周三代,政教合一,史官掌握文化与宗教,是人与神交通的中介人,他们侍从在王的左右,不仅随时记录王和臣下的言行,而且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上引论点,叁阅徐朔方《史汉论稿》第74-7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要预见上天吉凶,随时把神的意志传达给王。因此三代史官要精通天文、历法,世代相袭以精业务,天官与史官合二为一。东周以后,国家制度渐密,内史、御史等史官转为政事官,地位不断上升。而职掌文史星历的太史以星历业务为主,地位不断下降。到了秦汉,太史令是九卿之一奉常所属六令之一。但太史令掌天官、司图籍,合二而一的古史官遗意并没有改变,所以卫宏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①"序事如古春秋",就是整理计书,编次档案,系以年月。只要太史令职守为史官,司马迁不管是否为世袭,只要任其职,即为史官。司马迁父子相续纂其职,目的就是为了修史,《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不具引述。如果西汉太史令不是史官,那么司马谈、司马迁梦寐以求的史职岂非悬空?否认太史令为史官,即否认《史记》为官书。而否认《史记》为官书,势将割断《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也说不清司马氏父子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修史动机。因此,《史记》修撰性质的官私之辨,不仅仅是解决"藏之名山"的问题,更要涉及《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所以是司马迁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能不辨。
但是,古代史官,主要职守是司天官,掌图籍,至于记言记动,为的是补阙失,存故事。也就是说,史官典司图籍,职守是整理文献,记载实录,而不是著述历史。司马谈、司马迁效孔子修《春秋》,利用史职的条件著述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乃是发展了史官的职守②。秦汉之际为社会制度大演变的时期,史官制度亦在演变。东汉班固之后,典司修撰的史职日渐严密,至唐而成史馆制度,至此,太史令才专司天文而不掌史职。用后世健全的史官制度去范围西汉太史令,这是割断历史。《史记》书成,原题《太史公书》,就是标志其为史职所守。可以这样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官,动用国家力量,首开个人述史以成一家之言的先例,从而带动了史家的自觉责任,使效法者蔚成私人述史之风。东汉以后国家设馆修史,是中央强化集权政治控制舆论的标志,这是事势发展的必然。
①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