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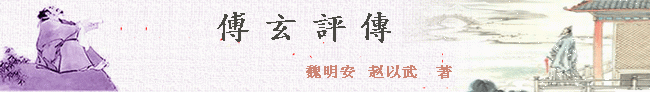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三、因物制宜以治天下
在傅玄看来,人君内修其德,正心息欲,去私立公,行公道立公制,对于"正天下"的作用,不能低估;外崇礼让,使百姓有利可图,兔于饥馁,诚信事上,孝敬事亲,对于"兴天下"的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天下"、"兴天下",最终是为了治天下,治天下还要有法的约束,法的作用不能忽视,法的手段必须相辅而行。推行仁政,离不开法治。强调法的重要性,这是傅玄关于"南面术"的核心思想。《傅子》里有一段无篇名的文字是这样说的:① 羊祜是位"謇謇正直"(《晋书》本传语)的儒者,他不理解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行李。博玄称颂荀、何,为晋武帝辩护,这是在入晋前后的事,立论不再以"匡正"为意,与《傅子》所言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
治人之谓治,正己之谓正。人不能自治,故设法以一之。身不正,虽有明法,即民或不从,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则明法者,所以齐众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设而民从之者,得所欲也。法独设而无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则势分:一则顺,分则争,此自然之理也。先"正"后"治",人君"率人",设法"齐众",是为了求其"一"而不分。这也就是荀子所谓的"以一行万"的"王者之法"。傅玄虽不像荀子那样认为人性皆恶,但他承认"人有尚德好善之性,而又贪荣而好利"(《戒言》),"善恶相蒙,故齐之以刑"(《北堂书钞》卷四三),恶的一面也还是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必须要"设法以一之",以正不法。
下面,我们分项讨论傅玄的法治观点。
(一)"天地之道"与"圣人之治"
按照汉代人遵奉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天时与人道是一种对应关系,只能顺之,不可逆之。《傅子·假言》篇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
天地生万物,"以异致同";圣人治百姓,"因物制宜"。天地有春秋之序,圣人有仁威之用;仁威迭用,如同春秋代序。故傅玄曰:天为有形之主,君为有国之主。天以春生,犹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杀,犹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发,天下乐之;威令之发,天下畏之。乐之,故乐从其令;畏之,故不敢违其今。若宽令发而人不乐,无以称仁矣;威令发而下不畏,无以言威矣。无仁可乐,无威可畏,能保国致治者,未之有也。
(《太平御览》卷一二)
上德之人,其济万物也,犹天地之有春秋,时至自生,非德之力。(《太平御览》卷八)"因物制宜"是治体,所以既"非德之力",也非威之功,必须"两尽其用"。傅玄还以水火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永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假言》)"仁令"与"威令",如同水火,"两尽其用"就得"陈釜鼎乎其间"。"陈釜鼎"就是"制宜"之举,人君掌握运用之妙,在于因时因物。这就是傅玄所谓的"圣人之治"。他在《释法》篇里,说得更明白:释法任情,奸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索以御奔马;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归之;洋洋圣化,九服仰之。春风畅物,秋霜肃杀。同则相济,异若胡越。"升平"之政有待"通儒达道",儒法沟通,恰当地援法入儒。"释法任情"与"专任刑名"都是不可取的。这篇文字很可能是入晋以后写的。因为入晋以后司马氏政权"释法任情",包容士族,政局一直是混乱的。所以傅玄提出要以法"通儒",达到"洋洋圣化"的治政目标,这仍然是一种"因物制宜"的主张。大体而言,入晋前傅玄是不赞成"专任刑名"的,今存《傅子》文及入晋初写给晋武帝的疏文,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入晋以后傅玄则对"释法任情"持批评态度,《释法》篇主要是就此立论的。援法入儒,这是荀子对礼制思想的突出贡献,被他推崇为"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傅玄向往的"圣人之治",是取法于荀儒的。他对任刑和释法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所以有"通儒达道"的议论。
(二)"先礼后刑"与"先刑后礼"
在治世理论上,儒、法两家的影响最大。儒家讲仁政,重礼治,不排除"齐之以刑"的作用,主张"先礼后刑";法家讲权术,重法治,不否认"德"亦为"二柄"之一,主张"先刑后礼"。汉未曹操执政重法治,天下贵刑名之术,儒家的礼治当然不可能受到重视,但是礼治还得要,不能全然不顾。于是,汉末以至曹魏时期的政论家就对礼与刑的轻重、先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仲长统主张以刑助德,因时制宜,所谓"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昌言》)。荀悦强调"慎刑",以"达道于天下"(《申鉴》)。他二人都承认刑的作用,但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助德"与"慎刑"之间就有轻重之别。建安末年,丁仪著文《刑礼论》(《全后汉文》卷九四),明确主张"先礼后刑";刘廖就不赞成,"与丁仪共论刑礼",其文曾"传于世"(《三国志》本传语),今可见《答丁仪刑礼书》、《难丁仪》二题下只言片语的佚文(《全三国文》卷三四),难知其详,只能从史传记载和文章题目窥测,二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刘廖大概是要讲"先刑后礼"的。到了曹魏建基至正始前后,蒋济《万机论》批评"任刑"、"好刑"之失,桓范《世要论》认为刑德"不能偏用",杜恕《体论》主张为法"参以人情",袁准《正论》提出仁、法要"两通而无偏重"。这些议论虽不完全拍合,但共同的地方在于强调礼治的重要性。而这一时期,据杜恕所言,"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求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体论·法》),法家、道家的主张更有市场。
那么,傅玄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宽简者昌,苛峻者亡。在《傅子》里,傅玄多次举到秦朝暴政速亡的例子,说明法家"严刑"。"亲法"的历史教训是应该为后世引为鉴戒的。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是宣扬法家路线的,李斯还有辅佐秦政的经历。傅玄批评李斯"深刑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下道报之"(《问刑》);提醒后世统治者:"撞亡秦之钟,作郑卫之乐,欲以兴治,岂不难哉!"(《意杯》卷五)傅玄对汉王朝的统治是十分肯定的。他讲,"汉所以历年四百","斯乃宽简之风"(《通志》)所致。西汉宣帝、东汉明帝,前后也有过"仗法任刑"、"未弘道治"(《古今画赞·汉明帝》)之失,但没有妨碍正道,"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通志》)。至于汉末曹魏时期的政治,傅玄人晋后批评了"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造成"纲维不摄"的弊端,并且认为这一"亡秦之病"沿至晋初仍有相当影响,亟需明"大教"、隆"教化"。这一认识应该说也是他入晋前著论《傅子·内篇》的指导思想。
其次,礼治离不开法治。《法刑》篇曰: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书禁令日法,诛杀威罚日刑。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是故圣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故圣人伤之,乃建三典,殊其轻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议其故而宥之,仁爱之情笃也。
接下来,傅玄又从"柔愿之主"轻刑、"刚猛之主"酷刑这两种极端,生发出如下议论:未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就是说,法不可去,亦不能"偏法";仁不可去,亦不能"纯仁"。既要"持法有恒"(《三国志·傅皈传》裴注引《傅子》),又要"两尽其用","以定厥中"。"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化"之治。如果把礼法、赏刑的手段仅仅看作去取得失的选择,那是无益于治道的。
最后,从现实出发,应该坚持"先礼后刑"的方针。上述《法刑》篇所论,所谓"先礼后刑"、"先刑后礼"的选择,应考虑到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也要看到"圣帝明王"与"暴君昏主"所起的作用,不能就事论事,唯以法刑轻重作文章。从总的原则来讲,傅玄认为"先礼后刑"是可取的。他说: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意林》卷五)这段话其实在建安末年丁仪的《刑礼论》里就有过表述。当时天下已定,曹魏禅代在即,所以丁仪是主张用礼治代替法治的。傅玄之所以要重复当年丁仪的议论,是因为曹魏后期司马氏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禅代魏室不应该抛开礼治不顾。
另外《法刑》篇举先王之例,特别提到"罪连三族,戮及善民",而有"无辜而死者过半"的情形,这是值得注意的,与现实不无关系。正始之后,司马氏执政,"罪连三族"愈演愈烈,激起了士人的反感,导致了方镇的反叛,甚至株连到忠于司马氏的臣僚。①这种残暴行径对司马氏政权很不利。傅玄对此当然不便明言,但借古讽今,这是《傅子·内篇》里常用的手法,其意在于提醒司马氏,既然以名教治天下,就应该"先礼后刑",以德化民,争取民心。
(三)善赏罚与慎赏罚
人君治国,赏罚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赏以劝善,罚以惩恶","明赏必罚"乃"政之柄"(荀悦《申鉴·政体》语)。汉未魏初的政论家对赏罚之道,都主张必行,但怎么执行,意见却不完全一致。崔寔以"重赏深罚"为是,荀悦侧重于"不妄",徐斡主张"不失其节";正始中讨论赏罚的轻重之别、公私之分,或强调"以情",或倡言"用智",或并举以"慎详",甚或推崇"自然",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傅子·治体》篇专论赏罚。文曰:治国有二柄:一日赏,二日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生杀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惧者何?赏公而罚不贰也。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可不谓公而不贰乎!若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
①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司马师执政时,"追刑已出之女",与司马师通姻的荀氏之女适于他族者,亦不得免。何曾出面力争,才权为修改。
"不妄"正是荀悦的主张。怎么才能做到"不妄"呢?荀悦认为,君主"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申鉴·政体》),即劝善惩恶、明赏必罚的"统法"之政就可做到。傅玄则进一步指出,既要"公而不贰",又要有善赏罚与慎赏罚两相结合的灵活举措。赏罚的目的,是要使"威德与天地并","使其民可教、可制",所以不能轻忽。善赏罚可体现威德的客观公正性,慎赏罚则可反映君主立威树德的主观严肃性。二者需要兼顾。也就是说,如果只讲公私之分,强调的是善赏罚,忽略的是慎赏罚;反之,只讲轻重之别,又容易出现片面谈论慎常赏的倾向,而忽略了善赏罚。"审持二柄",不单纯是赏罚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政之威德与民之好恶"相须而济",达到"为治"的目的。这才是人主应该着重考虑的大问题。
赏罚问题是体现礼刑之制的,二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礼刑论先后,这与为政执行什么路线、方针有关,因为有儒家"先礼后刑"与法家"先刑后礼"的区别。赏罚要"不妄",则是在儒家礼治路线的前提下,讨论它的方式、方法如何运用的问题。所以,赏罚是"为治""立政"的,是为政体服务的。汉魏政论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时,常常将礼法之政与赏罚之治混为一体,纠缠不清。例如徐斡《政论·赏罚》、杜恕《体论·法》都是这样,或将赏罚当作"政之大纲",或论法却以赏罚为主。荀悦、傅玄先后立论,都把赏罚放在为政治国之柄的地位上,这是对的。傅玄更细密地涉及到善赏罚与慎赏罚的主客观领域,讨论就深入了一步。
除了礼刑、赏罚的关系之外,汉魏政论家还特别对肉刑问题争论不休。
这就是下面我们要另外介绍的内容。
(四)关于肉刑问题
所谓肉刑,是指黥(刺面)、劓(割鼻)、剕(砍脚)、宫(阉割)、杀(杀头)这五种酷刑。据说这是上古惩罚罪犯时量刑而用之制。后来,人们理解肉刑,多指亡者刖足、盗者截手、淫者割势这些内容,"杀"不包括在里边。
荀子最先主张恢复施用肉刑。他驳斥了"治古无肉刑"之议,认为不用肉刑,无异于"惠暴而宽贼";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荀子·正论》),乃天经地义之理。东汉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引述《荀子》中的一大段言论,极为赞成恢复肉刑,①认为"大辟"之外,"募行肉刑",则"刑可畏而禁易避"。但是,班固之前,西汉文帝时,肉刑已废除,代之以答刑。此后,刑律虽增改,笞刑而外,或赎金,或增役,但仍然不能解决死刑(杀)与生刑(笞、赎、役等)之间的差距问题,缺乏一种中间刑,于是人们又想到了肉刑。汉末天下大乱时,一些政论家重新倡议使用肉刑,引起了持续的争议。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最先提出恢复肉刑的是崔宴、郑玄、陈纪等人。①接着,曹操执政期间,议过两次:前一次荀或赞成,孔融等反对;后一次陈群、钟繇赞成②,王修等人反对。魏文帝受禅以后,魏明帝太和初,亦① 《全三国文》卷二○,曹羲《肉刑论》曰:"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像天地为之惟明;察其用,则曰死刑重而生刑轻。其所驰骋,极于此矣。"① 仲长统、荀悦也是主张恢复肉刑者,《昌言》、《申鉴》里均有这方面的文字论述。② 傅玄之父傅斡也是赞成者,其《肉刑议》文今存。
曾分别议过肉刑,钟繇赞成,王朗等人反对。正始后期,又议肉刑可行与否,李胜、曹彦著文赞成,夏侯玄、曹羲、丁谧等人著文反对,论辩往返,十分热烈。③总之,汉末以来,围绕着肉刑可行与否的问题,议来议去,一直不能决定。甚至延及两晋,肉刑也还继续在讨论,始终没有实行。
关于肉刑之议,大体而言,赞成的理由有二:第一,死刑与生刑之间,应该有肉刑作为轻重之阶,这样既可使不当死而死者免死,又可使惩罚太轻而恶不止者惜身,产生惩恶止罪的作用;第二,肉刑不影响人口繁育,这在汉末以来天下调残的情况下,是很有力的一条理由。而反对的理由也有二:其一,肉刑不仁,它造成人体残缺,有违于名教,不厌于众心;其二,肉刑禁之已久,一时革旧,还不如以加重生刑的程度,或者增加律令的规定,甚至于脆以杀代刑更好一点。
曹魏时期,刑法的轻重失当问题始终解决不好。虽然魏明帝太和初改定了旧律,颁布了新律,但新律规定中增入了罚金、赎抵罪等名目,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明帝宠信左右,纵容身边小人,法律在贯彻中又出现了偏袒亲贵的倾向。傅玄评议道:"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坟内,放长蛇于左右也。"(《御览》卷六五二)又曰:"入粟补吏,是卖官也;入金赎罪,是纵恶也。"(《意林》卷五)卖官是汉末发生的事,赎罪是魏明帝时新出的花样。宽容亲贵与入金赎罪是养奸纵恶的表现。正始时期依然如此。这样,肉刑之议再一次发生了。夏侯玄提出"杀人可也",肉刑是断不可用的。理由是:"下愚不移",故应杀;肉刑不利于"反善"、"改悔",故无取。①他的这番议论在当时很有影响,直到东晋时,还有人推崇夏侯玄。傅玄有关肉刑的言论,主要是针对正始后期夏侯玄等所发宁杀勿刑之议的。
现在,我们来看傅玄的意见。他在《问刑》篇写道:或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日:"匹夫之仁也,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焉。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之心,故日匹夫之仁。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文帝有感于肉刑"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痛而不德",下诏废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于是修改刑律,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答五百,结果受答者大多致死。所以景帝继位后,下 诏再减答刑之数,认为原先"加答与重罪无异","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通鉴》卷一五),即用肉刑不当死者反而因答刑丧命。傅玄从这一事实出发,指斥汉文帝声称"不忍残人之体",却有"忍杀人"的行径,因此从"仁"的角度而论,"除肉刑"站不住脚,只能称之为"匹夫之仁",而与"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的"王天下之仁"有着显著区别。至于正始中夏侯玄等人以人性自然为理由,反对恢复肉刑,却宁肯以杀人重惩,更是"失其所以惩"的不仁言行。傅玄指斥"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人"①,也同样是"匹夫之仁"。
傅玄为了证明恢复肉刑的合理性,还设喻举例,竭力加以论证。请看他③ 李胜、夏侯玄等人关于肉刑的讨论文字,可参见《全三国文》。
① 参见《全三国文》卷二一,夏侯玄文《肉刑论》、《答李胜<难肉刑论>》。① 仲长统《政论·损益》篇也有如是表述。这说明汉末就有滥杀情形。
的意见:救婴孩之疾,而不忍针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众,何异服他药也?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张苍除肉刑,每岁所杀万计;钟繇复肉刑,岁生二千人也。名肉刑者,犹鸟兽之登俎而作肉。(《意林》卷五)
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太和中,钟繇上疏魏明帝,提出肉刑"虽斩其足,犹任生育","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这对人口大量减少的曹魏帝国是有利的,止杀增人当然比"所杀万计"的情形更具现实意义。傅玄又曰: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壮夫断其腕,谓其虽断不死也。(《意林》卷五)
这段话估计是引述李胜之论的。李胜不赞成夏侯玄以杀代刑的主张,写过一篇《难夏侯太初<肉刑论>》(见《全三国文》卷四三)的文章,其中就有慈父乞肉刑、壮夫断其腕的例子。李胜是赞成肉刑的,傅玄引他的文字,当在李胜未诛之前,即正始年间。当时讨论肉刑,曹羲也是反对派中一员。傅玄又引用曹羲的文字,以显其自相矛盾之处:曹羲日:"絷驯驹以绊,御悍马以朽索。"今制民以轻刑,亦如此也。
曹羲的原文出处已不详。不过,御世如御马,这是荀子、韩非道及之理,汉魏政论家常援引为喻。马有悍、驯之分,御之有铁辔、朽索之别。所以傅玄把"释法任情"(《释法》)、"制民以轻刑"比作"执腐索以御奔马"(《释法》)。那么,曹羲既懂此理,为什么要反对用肉刑呢?
当然,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论,废肉刑是一种文明的举措,反对复肉刑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很难说,傅玄竭力赞成用肉刑有什么高明之处,因而值得肯定。但是,汉魏之际政论家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却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刑律不完善,造成重刑被杀者太多,轻刑该罚者又不足以惩恶止罪,轻重之间悬隔太大,亟需有中间刑。当时人想到的是肉刑。因此,复不复肉刑,实际上关系到怎样执行法治的问题。不主张复肉刑的人,同时又赞成滥杀人;主张复肉刑的人,不赞成滥杀,也不赞成轻刑失度。相比较而言,后者于现实政治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大多是儒法兼济论者,急于治世,想恢复废除近400 年的肉刑,以制止社会犯罪,维护法治秩序。傅玄赞成恢复肉刑,正是如此,他以为"王天下"就不可有"匹夫之仁",这道理不错,但方法并不可取。健全法治,首先要完善法律制度,并非只有用肉刑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点上,当时政论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局限,傅玄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傅玄"通儒达道"的观点,就是希望人主实行儒、法兼济之"道"。君要有为,正己于心,息欲明制;接人以信,上下相奉;化下以仁孝,兴天下之利,崇事亲之道;辅之以法刑,达到保国致治的统治目的。只有这样,才可言"无为无不为"的治道。傅玄既批评"释法任情"之弊,又指斥"专任刑名"之失,但更主要的是针对玄学泛滥中贵黄老、崇老庄、倡无为之治的时代思潮,关心的是正始以后司马氏政权如何实现"政乃升平"的大计方针。他举前代开国之君为例: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刘邦、刘秀、曹操都是前代创业有为之主,他们都是在天下汹汹的时代,把握天下大势,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各自成就了一代雄主霸业。因此,对于司马氏而言,怎样审时度势,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傅玄写道: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意林》)这段话形象地说明,儒家的道德仁义是体,礼法互补是用,体用结合,才是致治之道。他所谓的"通儒达道",也可以拿这段话作注解,二者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变无为为有为,儒法并用,这是汉初思想家贾谊的主张。这些主张成了汉代新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一以贯之的统治方式。傅玄十分推崇汉代400 年统治的成功经验,他的政论中吸取贾谊思想的倾向也是很清楚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