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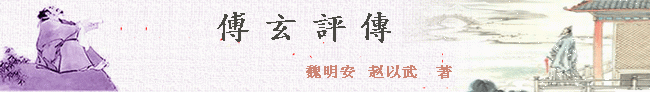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六、傅玄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
傅玄平生写下的诗文作品,数量确实不少。后代人更多地注意并评论他的地方,主要围绕他的创作成就,焦点在乐府诗上。总的来讲,对他的评价不高,贬多而褒少,认为值得称道的作品寥寥无几。这与南朝评论家刘勰、钟嵘的意见有很大关系。因此,问题首先要由此入手,辨明原委,方好作结论。
(一)刘勰立论不涉及傅玄人晋前的作品
刘勰《文心雕龙》论及前代作家,将傅玄作为西晋文人看待。如《明诗》篇举及曹魏时期有成就的诗入,提到的是嵇康、阮籍与应璩三人,就没有傅玄在内。《乐府》篇曰:逮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
《时序》篇讲到晋代文人"人未尽才",内中"应傅三张之徒",包括傅玄。《才略》篇讲到晋代文人突出的成就,则曰:傅玄篇章,义多规谏。
很清楚,刘勰肯定的是傅玄入晋后写出的大量庙堂乐府诗以及奏疏类文章。
刘勰这样概括傅玄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有没有道理呢?有的。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在南齐末年。当时,傅玄"创定雅歌"的成绩是人们公认的,他的文才主要反映在这方面,这是事实。至于他人晋后直言上疏,"义多规谏",又突出表现了他"刚劲亮直"的性格特点,这也极为难得。傅玄的地位是入晋后才变得显赫起来的,他的上疏和庙堂之作又赢得了声名,刘勰划代论创作,只讨论傅玄入晋以后的成绩,当然说得过去。
但是,后来人们讨论傅玄的文学成就,转而注意到他的其他乐府诗作,其实大多是入晋之前的早期作品。范围变了,作品不同了,可仍然沿袭着刘勰限定的结论,评价就不可能符合实际。比如,刘勰评晋代诗作,"晋世群才,稍入轻绩。??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这是总的特点。如果将傅玄作品中常常讨论的诗作也用这两句话概括,就很不准确:"稍入轻绮"可指傅玄入晋后的某些诗作;至于总的情形,"力柔于建安"还勉强说得过去,"采缛于正始"却无论如何说不通。因为傅玄诗作不加雕饰,质朴的特点不比建安之作逊色,是追步建安诗风的表现。
(二)钟嵘论诗不计杂吉,不重乐府
刘勰之后,梁初钟嵘《诗品》三品论人,将傅玄列入下品,而且也认为他是晋代诗人。这有没有道理呢?按照钟嵘的标准,是有道理的;按照后人讨论的范围,是不能成立的。
钟嵘论诗,"止乎五言",五言诗以外的诗体不作计较;提出"自然英旨"。"吟咏性情"的鉴赏标准,批评拘忌声律与拘挛用事。而且,钟嵘贵"直寻",不但涉事不必出经史,使文不必取声律,而且言情也要以"风力"、"丹采"达到"感荡心灵"的效果才好。因此他称赞的诗人,其作品多是咏怀、咏史、咏仙等,从中能直接感受到诗人自己的"性情"。他举例不重乐府诗,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清人许印芳指出,《诗品》是专论五言古诗的,"不宜阑入乐府"(《诗法萃编·<诗品>跋》)。大多数人不赞成他的这个看法。但是,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心雕龙》出现在《诗品》之前,而刘勰论文体,诗与乐府是分开来说的。乐府诗主要是供入乐歌咏的,声韵当然大有讲究,其诗文的情意是次要的,不过是文人有所寄托而已。这就既违背钟峰反对声律的主张,又不合他提出的"直寻"原则,所以他有意避开乐府诗,专就五言诗"众作之有滋味者"立论。三品定人,起码有不重乐府诗这个因素在其中。
然而,傅玄的主要成就在乐府诗创作上。他"吟咏性情"之作,无论是通过乐府诗寄托,还是用其他诗作直抒,"有滋味"的作品多不在五言诗,而在杂言诗。例如他最见"性情"的诗作是:长诗《白杨行》、《云中白子高行》,既是乐府,又是杂言;短诗《云歌》也是杂言不说,又"专用比兴"。即便乐府诗中寄托"性情"成功的作品,杂言的也居多。《秦女休行》、《历九秋篇》、《车遥遥篇》、《燕人美篇》都不是五言。从现存傅玄诗作来看,他的非乐府五言诗,入晋以后写过一些,但真正有"性情"的也就是《杂诗》三首而已。退一步讲,假定将傅玄五言诗连乐府诗也计入考虑,按钟嵘对上品诗人曹植的评价来衡量,"骨气奇高"还可将《挽歌》拿来压阵,而"词采华茂"就难以交代。傅玄的五言诗写得不如杂言,这一点前人已经点明。明胡应麟讲,傅玄"唯五言剿袭雷同,绝少天趣,声价不竟,职此之由"(《诗薮·内编》卷三);清入沈德潜讲,傅玄诗"时带累句","大约长于乐府,而短于古诗"(《古诗源》卷七)。除了"剿袭雷同"一语不免以偏概全外,其他的话是切中肯綮的。
因此,钟嵘在《诗品》里将傅玄置于下品,按照他规定的范围、标准,是基本合乎实际的;所谓"繁富可嘉",大概指的是傅玄入晋后曾写下数量较多而"性情"不足的诗作,这也没有说错。但是,如果不计五言与非五言的界限,不管乐府与非乐府诗的区别,从总体上审视傅玄的全部诗作,那么钟嵘的意见又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三)继承建安风骨,拟古与创新并重
清末叶德辉偏爱傅玄的全部作品,在所辑《傅玄集·叙》里,有这么一段评论:至其侍赋杂辞,皆以行气为主,即无两汉高格,终不入六朝纤靡之径。昔元遗山论诗,以刘越石不及见建安为恨。余则谓傅子与曹、刘同时,当亦可称鼎足。
这是把傅玄提前到建安时代,与曹植、刘桢的诗歌成就相提并论。叶氏之议颇有见地,但人们很少注意。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卷第十一章也为傅玄抱不平,指出:(傅)玄诗,钟嵘列之下品,与张载同称,且还以为不及载,实为未允。玄诗传干今者,佳篇至多,至少是可以和陆机、张协、左思,潘岳诸大诗人分一席地的,何至连张载也赶不上呢!这又把傅玄置后于太康诗人的行列,与当时众多作家相比较而言,认为傅玄不失为大家之一。
以上两种评价都不赞成钟嵘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认同的。
我们认为傅玄应归入正始作家的圈子里讨论,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与稽康相伯仲。以内容而论,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个人情志,这是建安诗的特点,而太康诗不具有这一特点,故"风云气少";表现妇女婚姻、爱情及其反抗精神,这在建安诗里不甚突出(曹丕写情诗较出色),而太康诗变成艳情,故"儿女情多"(《诗品》评张华语)。以形式而论,他的大多数作品质朴自然,不尚雕饰,体制多样,既有四言、五言,又有六言、七言、"半五六言"①、杂言、骚体等,有些诗的句式错落,隔句用韵,并遵汉魏旧韵。这些是在建安诗风影响下,继承与创新、拟古与探索两相结合而形成的,与太康诗风显然不同,与傅玄本人入晋以后的庙堂之作或其他篇什相比,也判然有别。文学史重点讨论的傅玄诗作,其实多是入晋以前的"清峻"之作,与正始诗人嵇康的作品十分接近。他二人的政治态度、理论观点不一致,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倾心老庄学说;傅玄拥护司马氏,热心于名教治天下的理论阐释。但是他俩在性格上,一个"傲",一个"刚";在创作上,都受到汉末建安以来时尚的熏陶,同有"清峻"的特点。而且傅玄开始创作的时间比嵇康要早,风格更接近前辈作家。张傅评论傅玄的代表作,就以为"《苦相篇》与《杂诗》二首,颇有(张衡)《四愁》、(繁钦)《定情》之风;《历九秋》诗,读者疑为汉古词,非(司马)相如、枚乘不能作"②说明受到汉代及建安作家十分明显的影响。当然,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臧否人物,抨击时政,更为激烈,处世为人也好,为文为诗也好,均放达不羁,比傅玄更具批判性,受到后世士人的敬仰,这是傅玄没能赢得的。
①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注曰,"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②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傅鹑觚集》中语。
(四)关于"善言儿女"
明人张傅在《傅鹑觚集·题辞》中讲: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简,台阁生风;独为诗篇,新温婉丽,善言儿女。强直之士怀情正深,赋好色者何必宋玉哉!
这种"天性"与"为诗"似乎不相吻合的现象,不仅张傅感到困惑,而且时至今日,人们对此也还是未释其疑的。张溥强为作解,认为"强直之士"傅玄还兼有"怀情""好色"的另一面。这样理解傅玄乐府诗"善言儿女"的特色,恐怕很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然而,张傅其实不明究竟,他的理解并不准确。
第一,汉乐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形式上杂言为主,五言为次,来源上主要以采集民歌入乐,保存了民歌原有的风韵。而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反映的社会内容很丰富,其中表现妇女婚姻、爱情的题材,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在入乐后的乐府诗中依然比重不小。
第二,汉未文人五言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抒情性,表现的内容复杂,感伤的色彩最浓。其中游子思妇类诗作,抒情的成分最具艺术感染力。
第三,建安其后的魏乐府诗,其实是既不采诗,也很少入乐的,率为文人制作,以五言居多,且"借古题写时事",改变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这一变化直接受到汉末文人诗风的影响,以抒情为主。即便是写到孤妾逐妇的不幸生活,其中也常常有自寓伤感的成分,例如曹植入魏后的一些作品就是如此。
傅玄的乐府诗创作,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我们说,他的文学思想既有"宗经"的一面,又有"通变"的一面,这恰巧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乐府诗的特点。叙事、抒情,兼有汉乐府与汉魏文人诗作的成分;杂言诗数量多,间有五言及六、七言等,这也呈现着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既有摸拟之作,又有古题新意、自制乐府的作品,同样是传统与新变融汇的格调。至于"善言儿女"之作,也完全是时代创作倾向的影响所致。由于傅玄"解钟律",他规摹汉乐府的努力更为自觉。张溥发现了傅玄这类作品有"汉古词"的遗韵,却没有从这一角度理解"善言儿女"的奥秘,可谓未达一间。
傅玄的《秦女休行》,作为一篇长篇叙事诗,在汉魏六朝乐府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人胡应麟《诗薮》称:"五言之赡,极干《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他认为,出现于汉未建安年中的《孔雀东南飞》与后来北朝时的《木兰诗》,可谓前后辉映的"双壁"。这没有什么疑问。不过,如果不拘泥于"五言"、"杂言"之分,而从表现内容上来着眼,那么《秦女休行》亦可与之合而称为三杰。《孔雀东南飞》叙殉情,《秦女休行》叙复仇,《木兰诗》叙从军,都在反映"儿女"之情上有独特的地方。这三首诗都是根据民间传说,经过文人加工后的作品,篇末均附加劝戒评论之词。"庞娥亲"这位刚烈女子,反抗性格要比刘兰芝更鲜明;她在选择自己的行事方式时,不让须眉,表现得丝毫不比木兰逊色。在篇制上,《秦女休行》有230 余字,虽与《孔雀东南飞》(1700 余字)相比要短,却与《木兰诗》(300 余字)相接近;五言为主,六、七、八、九言间而有之,这与《木兰诗》也近似。可以说,《秦女休行》上承《孔雀东南飞》表现女子反抗性的选材范围,又增添了"烈义"的新成分,下启《木兰诗》表现女子英雄气概的浪漫主义手法与夹叙来议的特点。
傅玄"善言儿女"的乐府诗作中,对思妇、怨妇的情态与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腻的刻画。其中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同情,是对现实社会问题严肃的反映。如果把这种选材及其表现内容误以为近乎南朝清商曲的格调,以为不过是热衷于摹写男女相悦或女性美之类,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傅玄《苦相篇》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于它集中反映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女子一生的凄苦命运,因此今天读来仍使人受震撼!显然,"善言儿女"之义未必就一定与作者刚直性格相冲突,倒是他这一性格的生动体现。所谓"善言儿女",既可能得情之正,又可能伤于轻艳。男女相悦、夫妇思念,这正是文学作品中重情的表现,典雅的诗三百篇,诡奇的楚辞,缘事的民歌,入乐的乐府诗,都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只要创作态度是严肃的,表现的内容是健康的,"善言儿女"并不错。而且,就傅玄乐府诗来讲,"善言儿女"是一方面,他还注意反映社会动乱、表现个人情志,写得也是较成功的。因此,傅玄乐府诗创作中"善言儿女"的倾向,与他的文学思想不矛盾,与他的性格也不冲突,与西晋时期出现的艳情之作毫无共同之处。在汉乐府、建安诗与西晋诗之间,傅玄的创作主要呈现着承前的状态,他的拟写之作虽不成功,但仍然可以显示其创作倾向的性质。如果从启后的角度立论,或者干脆置于西晋诗风下讨论,那么"善言儿女"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轻则言其"怀情""好色",重则斥其轻艳浮靡,至于到底是不是真是那么回事,有时就顾不得认真计较了。
结束语傅玄是魏晋之际的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是在入晋以前取得的。
作为思想家,傅玄的主要建树是在政论和伦理道德方面。《傅子》一书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其中内篇集中于"经纶政体",是一部政论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它的理论体系,既本着荀子学说中援法入儒的精神,又吸收融合先秦其他诸子与汉魏思想家、政论家提出的积极主张,以儒为主,兼综各家,显示出"杂家"的特点。它的现实意义,是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针对曹魏后期司马氏执政而不能顺利实现禅代篡立的政治斗争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关于安邦治国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核心是为司马氏谋求"君人南面之术"的,具有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意义。它的思想价值,在于围绕着君主如何统臣御民这个中心,主张为君要以德正身,息欲止欲,有为而治;为政要以礼教为本,举贤任能,安民利民。特别强调:重视法治,既不可任法,又不能释法;君主用人,应当重直臣识奸佞、验实效斥言饰。这些主张和观点体现出唯物主义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带有针砭时弊,并从政治上反对玄学思潮的倾向。入晋之初,傅玄上疏陈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傅玄对伦理道德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他不仅是位政论家,还是位伦理学家。伦理道德具有约束个人言行、处理好人际关系、规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准则性质,它是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乃至集团派别的概念,因而不同学派之间的对立分歧,又是社会变革、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产物。傅玄的伦理道德观,吸收先秦儒、墨、法三家之长,继承秦汉之际荀子学派特别是《礼记》中的思想和两汉学者的某些观点,服务于他的政论主张。在道德原则上,他拥护等级制度,主张实行礼治、推行教化与重爵禄兴利的功利主义相结合;在人性论上,他提出"水性说",认为善恶相因,人性是后天形成的,而且是可以转化的;在个人行为上,他坚持效果论,斥言饰虚伪,重实效事功,并强调要识别奸佞;在社会道德上,他力倡尊儒贵学,加强德治,不排除法治,赏罚并用,通儒达道;在修养方法上,他重视社会教化的力量与个人学习、实践相辅而行的作用,并指出君主要止欲息欲,以德正己,以信待臣,以兴利天下御民,才能"上下相奉,人怀义心";在社会秩序上,他反复强调以礼教兴天下,形成"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良好风气。以上这些内容,在《傅子》内篇里有集中反映,在有关礼制方面的议论文字以及铭赞类作品里也时有涉及。在魏晋之世,傅玄积极主张加强伦理道德的建设,意义是不同寻常的。除了为司马氏政权服务的性质外,他的这些主张还具有拯救被道家消极落后的伦理道德影响下的社会风尚的时代意义。也就是说,反对玄学思潮下排斥道德约束的"虚无放诞之论",在傅玄思想里是明确的。
《傅子》中、外篇,是评论"三史得失"和撰写《魏书》底本的内容。
从现存文字来看,其中有关对历史人物、事件、典籍以及制度方面的评价、辨证或者补充,史料意义与学术价值都非常珍贵。
作为文学家,傅玄的主要成就是在乐府诗的创作上,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入晋以前写下的叙事抒情的诗作。他的文学思想,既有"宗经"守旧的一面,又有"通变"趋新的一面。在创作中,他特别重视以妇女婚姻、爱情生活为题材,反映她们的命运与情感,表现她们反抗斗争的性格;同时继承汉末建安以来的传统,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个人情志,此类作品也占有一定比重,在表现形式上,他作了有益的尝试,杂言、骚体诗更有特色,短诗写得较成功。在风格上,清峻质朴,显示出汉魏本色。
不可否认的是,傅玄的理论与创作都存在着一些不足或缺憾。他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司马氏一边,对司马氏篡政过程中的残暴手段与野蛮行径,缺乏清醒的认识,更没有加以揭露与抨击;在理论上过分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价值,特别是对玄学抱着一种强烈的抵触反感态度,无视其中闪烁的思辨光芒,看不到它在思想史上显示出的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而是主张固守经学传统,提倡尊儒贵学,以抵制并扭转玄学思潮,从哲学意义上审视,其理论不免带有落后于时代的因素。在匡时救世的建议里,有的行不通,有的不可行。例如他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建议冗官务农亲耕等等,完全不切实际。另外,还有的是传统落后的东西,例如他热衷于恢复礼乐之制,一再宣扬夷夏之分(《贵教》篇与泰始五年上疏中第五事及此),说明他受到正统礼治思想的影响与束缚。至于他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宗经"的指导思想限制了他的创作成就,拟古的倾向削弱了他的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五言诗写得不够出色,语言上总的讲尚嫌质涩。
从傅玄的身世与经历来看,他入晋前后境遇、地位的变化,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傅氏一族,自傅玄祖上起,就因郡境失上、寄治他乡,使得族人流寓失本,势单力孤。其祖傅燮于汉末有功不封,殉节兵乱;其父傅斡权变机敏,死得太早。傅玄出生不久,即成孤儿。他勤奋好学,孤贫中成才,以博学赢得时誉;入仕后遭受何晏等人的打击迫害,处于逆境。高平陵之变,给傅玄的政治前途带来希望;追随司马昭南北征战,坚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入晋后的高官厚禄与显要地位,大大影响了他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成就。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正始前后取得,他在政论方面的建树是在入晋之前、之初提出,这既是时世造就的,也深深地打上了傅玄个人的烙印,对他来讲,又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认为,傅玄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说明:司马氏在篡取曹魏政权的斗争中,不但占据政治、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在思想领域也有代言人;不能以为整个士人集团中有思想的人物都站在这个政权的对立面,也不能以为玄学思潮流行的情况下,传统儒学就没有相当的市场。傅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魏晋之际文学创作演变的过程中,还有傅玄这样一位作家不应该受到忽略。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