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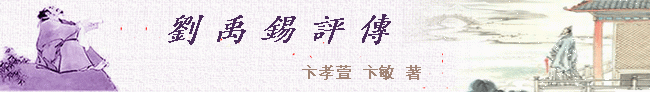
|
三、"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天人之辩
刘禹锡从无神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在肯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以"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理论观点,对"天人"之辩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
在《天论》上篇,刘禹锡一开头就把先秦以来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各种争论,明确地概括为根本对立的两个哲学派别、两条认识路线,即以"阴骘之说"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有神论和以"自然之说"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他说: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俫,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
刘禹锡认为,世上谈论天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阴骘之说"。"阴骘",语出《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思是只有天在暗中决定着人的命运。固执于天是神明的人说,天和人的关系实际上如同影子随着物体,回响应着声音一样密不可分,上天降祸必定是固为人犯了罪过,上天赐福必定是因为人有了善行。作恶或行善是感,得祸或得福是应,天与人之间有互相感应的影响,人在穷困艰难时呼天,上天一定能够听到;在内心哀痛时向天祈求,上天也一定能够回答,如同有个神灵确确实实在主宰着似的。所以,天有意志,有灵性,在暗中决定人的命运的说法就盛行了。
一种是"自然之说",即"天人相异",没有感应的关系。坚持天茫然无知,没有意志的人说,天与人实在是毫不相干的。雷霆震击牲畜、树木,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罪;春雨滋润毒堇、苦荼,并不是选择善类。柳下跖、庄一直被看作奸邪盗贼的代表人物,却很顺利;孔丘、颜回作为圣贤之人,却遭受困厄。这些都说明天是苍苍茫茫的而没有什么主宰者。所以,天是自然物质的说法就盛行了。
"天与人实影响"的"阴骘之说"与"天与人实刺异"的"自然之说",被刘禹锡概括为"世之言天者"的"二道",这在天人关系的争论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对天人关系认识发展史的理论总结。
最初,在先秦人的观念中,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相互沟通的。人们都相信,天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条件,尽管当时对自然、道德、伦理和人性的关系均是不明确的。在周人眼里,"礼"是"天命"的一部分,作为等级名分的制度和作为反映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等都属于"天命"的范围。孔于也相信"天命",从而把"礼"看作既存的、不可违背的东西,并提出"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孟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自我修养,强调个人内在自觉本性的实现和完成,即要求人们不受外界影响,扩充自我德性,达到"万物皆备"的境界。不但儒家这样认为,墨家讲"天志明鬼",道家也讲天人相通。表面看来,老子讲"天道自然无为",实际上老子的"道"既表示自然法则,又表示充满生命意识的神秘主宰物,是儒家或墨家"天"的观念的抽象化与哲理化。庄子想往"与造物者游",圣人、真人、神人溶合为一,强调人只有脱离社会,摆脱"仁义"等伦理羁绊,才能进入与自然为一的境界。当然,这种天人相通的观念所反映的只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的虚境。
"天人相分"是荀子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①,天命与人事各有所分,要"明于天人之分。"②到荀子时代,儒家原先所宣扬的"礼"已名存实亡,荀子从哲学上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其目的是要割断"礼"与"天命"之间的联系,从社会内部矛盾探讨"礼"的起源。荀子解释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此礼之所起也。"③"礼"的规范不是什么超越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的创造,而是人类自己主动制定的。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接受"礼"的教化则是被动的。但是,"礼"一旦确立,就成为支配社会兴衰命运的普遍法则,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因此,"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①荀子强调名教属于"人事"范畴,与自然的天没有直接的联系,"知礼"要"明于天人之分"。董仲舒把"知礼"和"知天命"结合起来,提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②的天人合一论。表面看来,董仲舒回到了儒家原有的"天命"思想,但孔子对"天命"基本上是出于一种自发的信奉,孟子把"礼"看作是"天"赋予人性的一种先天德性,而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③之说,溶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互补了各家的理论不足。儒家的天人合德的思想,墨家的天志非命的思想,道家的天人自然相合的思想,都被董仲舒揉合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来,从自然的、伦理的、个体和群体的结合上提出和论证了以天人感应为根据的君权神授说。
王充继承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和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提出"天地台气,人偶自生"④的观点,批判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思想,用唯物主义的精气说直接解释人的精神现象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虽然否定了人格神的"天"的主宰作用,但却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
魏晋玄学的天人之辩以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王弼、郭象等以"天道自然"的玄学名理,熔铸"礼法名教"的政治内容,又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天人合一说。阮籍、嵇康等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追求返归自然的人生理想,主张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从"越名教而任自然"导致了人生悲剧。鲍敬言的"无君论"戳穿了正统玄学家们把"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看作"天道自然"的神话,提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异端"思想,其实质是一种"无君即自然"的天人合一论。佛教在融合玄学的过程中,以因果报应说装饰玄学的自然名理,① 《荀子·无论篇》。
② 《荀子·天论篇》。
③ 《荀子·礼论篇》。
① 《荀子·天论篇》。
② 《春秋繁露》卷十二《基义篇》。
③ 《春秋繁露》卷十二《基义篇》。
④ 《论衡》卷三《物势篇》。
提出神不灭论的天人合一说。
刘禹锡总结了先秦以来天人之辩的理论思维教训,从儒、道、玄、佛等所共同具有而又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论中,概括出其精神实质是"阴骘之说"。韩愈的天说,是主张阴骘之说;柳宗元作《天说》,是主张"自然之说"。从哲学上说,韩愈宣扬"天人感应"等传统说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柳宗元主张"天人相异",否认有主宰人事之天,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刘禹锡认为,韩愈的"阴骘之说"与柳宗元的"自然之说"都有片面性。韩愈的"阴骘之天"的说法完全是虚妄的,但柳宗元的"自然之说"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因从其《天说》中所讲的话来看,似乎与人是完全分开,各不相干的,中间没有关系,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当然,自然之天本来是没有意识的,不可能对人事作有意识的干预,而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招来天的有意识的干预。从这方面说,"天人相异",天人不相影响。但是,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各部分包括天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刘禹锡就是在这一方面补充了柳宗元《天说》的不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独创性理论。
刘禹锡继承荀况"天人相分"的理论成果,克服以往"自然之说"的某些理论弱点,力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区别"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并阐明二者的辩证关系。《天论》上篇开头就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刘禹锡认为,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天,是有形物中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杰出的。天所能做到的,人固然有不能做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也有做不到的。这就是说,客观事物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各以其特殊的功能胜过对方,天与人也相互作用、相互取胜。刘禹锡与《庄子·大宗师》的"天与人不相胜",的命题相反,阐发了"天与人交相胜"思想的要旨。
从《天论》的内容来看,刘禹锡所谓的"能",大致是指事物的能力、功能、作用。在明确了这一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刘禹锡对"天之能"、"人之能",即天与人各在哪些方面"交相胜"的问题作了论述: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才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PGN0191.TXT/PGN>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刘禹锡把"天之能"还原为"生植"万物的自然演化职能,把"人之能"归结为对自然万物能够加以改造和利用的职能,即"治万物"。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的功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生存竞争、强胜弱败的规律在发挥作用。
春夏之时万物生长、秋冬季节草木凋零;水淹火焚能伤害万物,木质坚实而金属锋利;年壮的强健有力,年老的体弱眼花;智力高的争相为君,体力强的争相为长。这些都是"天"的职能。而人类社会的功能在于制定和执行法律制度,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规范在发挥作用。人们春夏时种植庄稼,秋冬时收藏作物;防治水害而又利用水来灌溉,扑灭火灾而又利用火的光热;砍伐树木并加工成坚实的器物,冶炼矿石并磨厮成金属器具;用正义来制止强暴的武力与恶意的攻击,用礼节来确定长幼尊卑的关系;尊重贤能崇尚有功,建立是非标准以防止邪恶。这些都是人的职能。在这里,刘禹锡充分肯定和论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作用。这一切绝不是韩愈所说的是"为祸元气阴阳",有"甚于虫之所为"①的破坏活动,而正是天人之间"交相胜"的重要内容。
刘禹锡为了通俗他说明"天与人交相胜"的道理,在《天论》中篇举了一个例子: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 </PGN0192.TXT/PGN>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荫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譬如人旅行,成群结队地到荒野去,想寻找茂密的树荫休息,寻找清凉的泉水解渴,一定是身强力壮的人捷足先得,即使是圣人。贤人,也不能和他们竞争。体力强的胜过体力弱的,而人的体力是自然的生理条件造成的,这是"天胜"的一种情况。如果成群的人停留在城市里,要寻求华丽的房屋居住,饱餐丰盛的饭菜,必定是圣贤取得优先,即使身强力壮的人也没法同他们竞争。人是实行法制的。法制是人所立的,是人之道。人在社会范围内可以改变体力强弱相胜的自然状态,圣贤位尊名显就高于普通的人,这是"人胜"的一种情况,即"人之道"战胜了"天之道"。
刘禹锡接着说,假如经过虞、芮这种是非分明的地方,虽然在荒野也如同在城市里一样,必然是礼让的,这也说明是"人胜"了。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是殷王朝所属的两个小国,边界经常发生纠纷,无法解决,去找周文王裁决。到周地后,看见"耕者皆让畔",他们感到惭愧,于是两国不再争执,也谦让起来。但假如途经匡、宋这种是非不分的地方,虽然在城里,也如在荒野一样,必然是争夺的,这说明是"天胜"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游说诸侯,途经匡地,被匡人围困了五天。后到宋国,和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把树拔倒,孔子只得仓皇逃走。区此,从这一天的旅途中,可以看出天与人是互相胜过的。
通过这一个例子,刘禹锡得出结论说:是非是人理,强弱是天理。如果是非存在,即使在野外,也是人理胜天理,即社会的法制与道德观念将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是非,即使在城里,也还是天理胜人理,即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法则将取得胜利。然而天并不是一定要胜过人的,因为只有当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时,就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但人确实是力图胜过天的,因为天没有意志,人通过努力可以胜天。
在"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这个浅近的比喻中,刘禹锡把人的体力① 引自《柳宗元集》卷十六《天说》。
强弱等生物属性纳入"天"的范畴。这样,就人和天的关系说,人之所以能胜天,是因为人能组织社会,实行法制,"人能胜乎天者,法也。"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又由于部分人违反法制,所以也还有"天与人交相胜"的现象。
刘禹锡把人们在荒野或在城市社会法制约束的无效或有效,看作是"天胜"或是"人胜"的标准。由于人类智慧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②人能制定和执行法制,与天争胜;能利用自然赋予的有利条件,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纲纪。
总之,刘禹锡以"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揭示天人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从而克服了柳宗元只是强调天人"各不相预"①,即只看到天人之间对立的一面,没看到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统一的一面的片面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解决,还只是唯物的,而不是辩证的;刘禹锡是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天人关系问题。"交相胜"是天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还相用"是天人之间的统一关系。"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②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之所以无穷无尽,就因为事物之间既互相取胜,又互相利用,天和人不过是万物中最突出的而已。刘禹锡在肯定"交相胜"与"还相用"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指出"天之能"与"人之能"互不相能,"天之道"与"人之道"各行其道,因此天人之间不是神秘感应的关系,而是在"交相胜"的矛盾对立中"还相用",这说明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刘禹锡把《天论》送给柳宗元看,柳宗元回信说他细读《天论》五、六日,没有发现与他的《天说》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并认为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的思相是错误的。柳宗元的《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天之不谋乎人也。彼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PGN0195.TXT/PGN>耶?子所谓交胜者,若天恒为恶,人恒为善,人胜天则善者行。是又过德乎人,过罪乎天也。又日: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余则日: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辞,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
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日天胜焉,一日人胜焉,何哉?莽苍之先者,力胜也;邑郭之先者,智胜也。虞、芮,力穷也,匡、宋,智穷也。是非存亡,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说,要以乱为天理,理为人理耶?谬矣。
柳宗元否定天降祸福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没有意志,不可能干预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人类的生产活动显然有受到自然界影响的这一方面,不能否定人类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柳宗元以天生植万物并不是为人着想为由,对人务胜天提出质疑,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从这封信来看,柳宗元其实没有完全弄懂刘禹锡"大人交相胜"的基本①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②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下篇。
①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答刘禹锡(天论)书》。
②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篇。
思想。柳宗元说天和人交相胜的道理,好象是天经常作恶,人经常行善,人胜过天,好的事情就行得通,这种说法是过分赞美了人,过分责备了天;又说刘禹锡认为天的职能在于生植万物,人的职能在于坚持法治,这样就把判断天和人的职能分成了恶与善、生植与法治四个方面,在柳宗元看来,生植与灾荒,都决定于天;法制与悖乱,都决定于人,只有天和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天和人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相干涉;而荒年与丰年,安定与混乱就是从天和人各自的职能中产生的。显然,柳宗元是过于强调了天人关系中相分的一面。
刘禹锡在《天论》中认为,"天之能"的表现之一是以强凌弱,"气雄相君,力雄相长";"人之能"的表现之一是有礼义。法制。法制得到实施则人胜天,法制、礼义被破坏则天胜人,即把这种以强凌弱的现象也看作是"天之能"。柳宗元批评他是"过罪乎天",因为"法制与悖乱,皆人也",认为社会的治乱都应当从人事上找原因。而刘禹锡在论述"天与人交相胜"这个问题时,天的概念有时是指自然界,有时则指体力的强弱等人的生理条件,柳宗元认为他始终没有抓住天是无知的自然界这一根本原理立论,所以说他的论点"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柳宗元按着这样的思路,对刘禹锡《天论》用旅行所作的比喻也提出了质疑。柳宗元认为,旅行都是人的活动,把一种情况说成是天胜过人,把另一种情况说成是人胜过天,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实际上,在野外"强有力者"占先,是说明了"力胜";在城市圣贤受到优待,是说明了"智胜";经过虞、芮这两个国家的人不得不讲礼义,是因为在那里气力不能发挥作用;经过匡、宋这两个不讲"礼"的地方,是因为在那里智慧不能发挥作用。柳宗元说,是非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找不到它能够用来说明天的理由。
刘禹锡在《天论》中说,"是非存"则"人理胜";"是非亡"则"天理胜"。意思是说,社会上有公正的是非,人们就讲礼义;社会上没有公正的是非,人们就凭强力取胜。柳宗元认为这是把社会混乱作为"天理",把社会安定作为"人理"了,是荒谬的。但柳宗元在这里似乎没有分清自然和社会的界限,所谓治、乱,完全是就社会秩序而言,自然界不是社会,无所谓治、乱。"乱为天理,治为人理",柳宗元的这一概括是把自然界也看成社会,把社会的范畴强加于自然界,因而是不恰当的。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天人之辩,不仅批判了阴骘之说神秘的天人合一论,澄清了他们在"天人相与之际"散布的种种疑团;而且弥补了以往自然之说的一些理论弱点,以对立统一的自发辩证观点深化了荀况的天人相分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对柳宗元的天人"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的思想是一个辩证的发展,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