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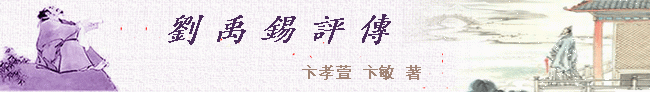
|
五、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法弛"、"理昧"
刘禹锡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通过"天与人交相胜",特别是"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这一思想环节,深入探讨了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关于这一问题,柳宗元曾提出过"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①的命题,对有神论产生的根源进行过揭露,但还没有进一步展开。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刘禹锡也超过了柳宗元。刘禹锡认为,天命论的产生和流行,主要是社会政治原因引起的。他在《天论》上篇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族之贵,给予万钟之禄,处之咸日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日:"天何预乃事邪?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PGN0206.TXT/PGN>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人之所以能胜天,在于制定与执行法制。法制畅行,"是"就成为人们公认为正确的,"非"就成为人们公认为错误的东西。普天下的人,凡遵循法制的必然受到奖赏,凡违犯法制的必然受到惩罚。应当奖赏的,即使封以三公的高官,给予万钟的厚禄,人们都认为合适。这是因为他做了好事的缘故。
应当惩罚的,即使处以灭族的惨祸,遭受刀锯的酷刑,人们都认为应该。这是因为他做了坏事的缘故。在这冲情况下,人们都说天怎么能干预人事呢?
只有在向天表示诚敬,报答天的恩德的祭天活动,或在新君即位、出师征伐或颁布历书等祭天仪式中,才讲到天罢了。福禄可以用行善来取得,灾祸则是由作恶召来,哪里与天有什么相干呢?这就是说,如果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是非清楚,赏罚公平,人们对赏罚祸福的原因看得清楚,天命论就不会产生。
刘禹锡接着分析了"法小弛"时的情况,指出: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
当法制稍许松弛时,那么是非就混淆了。受奖赏不一定都是好的,受惩罚不一定都是坏的。有的人因贤能而得到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名声,但有时品行不好的人也混杂在里面;有的人因犯罪而受到刑杀和羞辱,但有时无辜的人也搀杂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那些应当受到赏罚的而确实受到了,这是合理的;那些不应当受到赏罚的却也受到了赏罚,难道合理吗?于是,人们就怀疑这是天命吧。福禄或许可以用奸诈的手段攫取,而灾祸有时可以侥幸避免。由于体现人的职能的法制混乱,所以关于天命的种种说法也就混乱不清了。人们对不合理的事不明原因,往往就归之于"天命",从而对无神论思想产生动摇。
当社会处于"法大弛"的情况下,要否定天命论是不可能的。刘禹锡指出:① 《柳宗元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神降于莘》。
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法制完全废弛,是非就颠倒了位置。受奖赏的常常是巧言谄媚的人,而受惩罚的往往是正直的人。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克制邪恶,人能胜天的手段就完全丧失了。在法制已经丧失而空有其名的情况下,那些糊涂人还孤零零地拿着这无实的空名,想去抗衡鼓吹天命的人,这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因此,社会混乱,政治黑暗,是非颠倒,天命论就盛行起来。
刘禹锡分析了人类社会执行法制的"法大行"、"法小弛"、"法大弛"的三种情况,概括了由此而产生的对天人关系的三种看法,从实行法制的程度来揭示天命论产生的社会原因。刘禹锡对此作了总结: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
任天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
非天预乎人尔!
在法制广为推行的时候,人们就会说:天怎么能干预人事呢?我遵循法制就行了。在法制完全废弛的时候,人们就会说:法制究竟有什么用呢?听天由命罢了。在法制稍有松弛的时候,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就混乱了。如果要以个人遭遇的好坏,而想证明天命的有无,那就糊涂了。生在治世的人,由于实行法制而是非明白,都知道赏罚的由来,所以得福不感激天,遭祸也不怨恨天;生在乱世的人,由于法制废驰而是非不清,人们不知道赏罚的依据,所以把本来是人为的祸福都归于天。其实,这并不是天在干预人事。
刘禹锡认为,法制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基本分野。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刘禹锡十分重视法制实行情况对人们是非观念的影响。如果充分发挥法制的作用,不仅能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而且还会确立一个严格的辨别是非的标准。在"法大行"、"法小弛"和"法大弛"的情况下,社会的是非观念大不一样。如果法制健全,是非清楚,人们会普遍认为合乎法的为是,违反法的为非。当以"公是""公非"作为衡量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标准时,人们的行为就有所规范和约束,就可以克服某些违反"人道"的人的自然性或生物性,限制"强有力者先焉"的封建强权和特权,社会就可以组织起来,用"人道"去战胜"天道",用"人理"去战胜"天理",用"人之能"去战胜"天之能"。反之,如果法制破坏,是非颠倒,"人能胜天之实尽丧",社会内部和人类本身就发生问题,天命的魔影就要笼罩社会和人们的心灵。
刘禹锡从社会根源上对天命论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应当视为顺宗时代那场政治革新斗争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法大行"的社会,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是非分明,天下太平,人们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是事在人为,赏罚祸福合情合理,这是刘禹锡对"永贞革新"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写照和对理想的社会状态的憧憬。
"法大弛"的社会,是非赏罚完全颠倒,人事无法以常理说明,这是刘禹锡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身遭厄运,从内心发出的感慨。
刘禹锡还揭露了乱世昏君宣扬天命论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和奴役老百姓。他在《天论》下篇指出: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尧、舜根据人道办事,不谈天命,记载尧、舜的书,开头就说考查历史,不说考查天命;幽、厉全凭上帝作招牌,不敢谈人事,讽刺周幽王、周厉王的诗篇,开头就讲上帝,不讲人事。在舜的时候,许多有德才的人被推举上来,只说是舜选拔任用的,不说是上天授予的;在殷高宗时,因他是乘着乱世而兴起,心中明知傅说是个贤人而想任用他,却借故托梦说是上帝赐予的。尧舜时代是盛世的象征,尧舜之时的老百姓难以用神鬼来欺骗;商代的风俗已经败坏,统治者就只得用天命来驱使百姓。刘禹锡根据以上的史实得出结论说,上天是不能干预人事的。天命论的产生和流行,主要是社会政治腐败的结果。
如果说刘禹锡认为天命论的社会根源是"法弛"、"人道昧"的话,他还探索了天命论的认识论根源是"理昧"。《天论》中篇对此指出:古之人易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潍、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泝洄,不能峭为魁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济,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在这里以小河和大河中的行舟为例,说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明",一种是"理昧"。古代的人之所以要称引天的原因,就是对自然的不认识、不了解。用驾船的情况来说,当船在潍河、淄水、伊水、洛水这些小河中行驶的时候,船速的快慢由人操纵,停泊起航也由人决定。在小河中,即使狂风怒号,也不能激起波涛;河水逆流形成的漩涡,也不能耸起洪峰。如果船行得迅速而平稳,这是人为的;如果船倾覆或搁浅,也是人为的。船上的人没有说这是天意,因为事情发生的道理是很明白的。
那些在长江、黄河、淮水、大海里航行的船,不能预知航行的快慢,停泊起航也不好掌握。吹动树枝的小风,顷刻之间就可掀起遮天蔽日的巨浪;车篷大小的云块,一会儿就可引出变幻莫测的怪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船能安然自得地航行,在于自然条件;心神沮丧地看着船沉没下去,也在于自然条件;临近危险而单独幸存,还是在于自然条件。船上的人没有说这是人为的,因为人们不明白事情发生的道理。
刘禹锡以操舟为例,指出"理明"就不会相信天命,"理昧"就必然相信天命,关键在于人能否认识事物运动的规律。刘禹锡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按其规律变化的。人们认识和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就相信事在人为而不信天;反之,人们就会把不能解释的现象归之于天。刘禹锡对天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的看法是可取的,深化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天命论思想的批判。
如果进一步分析,刘禹锡对天命论的认识根源的揭示,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理解。"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①人的苦难不仅在于穷通寿夭的遭遇具有不可违背的现实性,尤其是当人们还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这些遭遇具有不可测度的偶然性。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就成为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仲舒宣称"为人者天"①,认为天命必然决定人生的一切;王充认为"天道自然",而在具体解释人生遭遇时则是"吉凶偶合"②;这种"自然"与"偶合"的思想矛盾,到魏晋玄学演变为"于自然无所违"③的必然与"无故而自尔"④的偶然。佛教的轮回报应说,用神秘化了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双重锁链,把人们的心灵禁锢在永世不得解脱的因果报应之中;而禅宗的"顿悟成佛"说,认为众生与成佛只"一念之差",只要"一念相应,便成正觉",这个"方便法门"就是可由自己主动掌握的突发智慧启开的,从而冲破了由偶然冲动所造成的必然锁链。偶然与必然关系问题上的这一认识发展逻辑,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政权和宗教神权统治下的人们挣扎于现实苦难之中而又无法摆脱的思想苦闷。
刘禹锡继承了"自然之说"的无神论传统,认为人们的现实遭遇是"茫乎无有宰者"⑤的偶然现象,并对偶然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探求。如关于航行的吉凶问题:舟行于小河,人们明白航行的规律,掌握快慢行止的主动权,不仅"迅而安",就是"覆而胶",全都决定于人为的因素,而非决定于偶然;舟行于大河,人们摸不透变化的规律,失去了掌握快慢行止的主动权,不仅"黯然沉",就是"阽危而仅存"或"恬然济",全都决定于天意偶然,"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但是,从刘禹锡的"数势之理"的逻辑来看,"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①这就是说,凡是合乎规律的事物,由小推大必然符合,由人推论天也是符合的。按照这个道理来推测,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贯穿其中的。既然天体的"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②,江河淮海的航行规律也是可以逐步认识的。人们的认识可以从"理昧"转化为"理明",认识的对象可以从未知的偶然转化为已知的必然。人们在"适当其数乘其势"③的认识基础上就可以掌握行动的主动权,从"言天"转化为"言人"。这就克服了王充偶然遭遇论的"天道难知"④,"遇难先图"⑤,即把偶然性绝对化的弱点。
又如关于社会遭遇问题:在法制大行,是非公认的情况下,"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必然性的法则起着作用,"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祸福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联系;在法制小弛,是非混淆的情况下,"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必然性的法则开始破坏,"福或可以诈取,而祸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53 页。
① 《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篇》。
② 《论衡》卷十八《自然篇》。
③ 王弼:《老子注》第二十五章。
④ 郭象:《庄子注·天运篇》。
⑤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①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下篇。
②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篇。
③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篇。
④ 《论衡》卷三《偶会篇》。
⑤ 《论衡》卷一《逢遇篇》。
或可以苟免",祸福与行为之间开始出现一些偶然因素;在法制大弛,是非易位的情况下,"赏恒在佞,罚恒在直",祸福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的全是无法掌握的偶然。由此可见,决定人们遭遇的,既不是天命必然,也不是偶然之天;人们避祸得福之道,既非来自偶然机遇,也非来自豁然顿悟;关键在于对社会法制的遵行与革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阴骘之说"播弄的偶然之谜,也弥补了"自然之说"把偶然绝对化的不足,深化了古代唯物主义者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关系的认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