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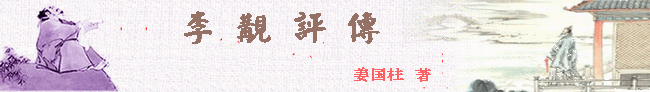
|
二、礼的内容和范围
荀子已经扩大了礼的范围,扩充了礼的内容,荀子的"礼"不仅包括"法"的因素,而且囊括天地、日月、四时、山川、河流等自然万物,礼成为自然现象、社会事物、人伦道德的共同准则。他说:凡礼,始乎税,成乎文,终乎悦校。??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且为万物之极,人道之极,人和万物离开了礼,则发生紊乱,有了礼,则万变不乱,"礼"是完美无缺的,自满自足的,人和万物只能遵循礼,而不能损益礼。这个礼简直成了宇宙的至高无上者。
李觏发展了荀子的这个"礼"的思想,亦把"礼,,视为范围广大、无所不包的极广大、致精微者。他认为,"礼"是包括天地、阴阳、人事的无穷广阔者。所以说:(或)曰:古之言礼乐者,必穷乎天地阴阳,今吾子之论,何其小也?
曰:天地阴阳者,礼乐之象也,人事者,礼乐之实也。言其象,止于尊大其教;言其实,足以轨范于人。由此出发,李觏认为,"礼"是天地阴阳之根,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治国之策,修身之要,法制之总名,道德之大本,等级制度的体现,神学迷信的保留。所以"礼"的范围极其广大,"礼"的内容极为广泛。
李觏一反历史上儒家学者有关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八者并行的传统说法,而以"礼"为其他条目的根本,其他七者都一本子"礼"。
他说:尝闻之,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传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于礼,无乃不可乎?
曰:是皆礼也。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于、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日乐、曰政、日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日仁、日义、日智、日信,礼之别名也。是七者,盖皆礼矣。李觏把"礼"凌驾于于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之上,不是八者并行井用,而是"礼"为其余七者之本,其余七者都是礼的体现和别名,就这个意义上讲,其余七者亦都是礼。李觏还把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把作为礼之本;乐、刑、政作为礼之支;仁、义、智、信作为礼之别名。三支与礼的关系,如同手足与身体的关系;四名与礼的关系,如同筋骸与身体的关系。礼包括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如同人的身体包括手足筋骸一样。就是说,"礼"为本,为体,其余七者为末,为用。
① 《荀子·礼论》。
① 《礼论第六》,《李觏集》卷二,第17-18 页。
② 《礼论第一》,《李觏集》卷二,第5-6页。
从李觏关于"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礼"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欲求的内容,又包括音乐、政治、法律、道德、知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内容,所以"礼"的范围广大、内容丰富。李觏在《礼论》的第二、三、四、五、六篇中,具体地阐明了这个基本思想。在李觏有关"礼"的一系列解释中,告诉人们,"礼"不是抽象的玄谈天地阴阳之理,更不等同于仁、义、智、信等"无其物"的观念,而是论述人事之实的具体轨范,是"有其物"的存在。他指出,如果把具有真实内容,有实际意义的"礼"抽象化。空洞化,变为玄想空谈的概念,特别是把"礼"神秘化、神圣化,进而洋洋阔论,并以教人,使人耳目惊眩,混沌不清,不知所云,不知所取,这便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过。因此,李觏反对玄谈无用之礼,而注重礼的实际内容、现实意义。他说:前世之言教道者众矣,例多阔大,其意洋洋,其文以旧说为陈熟,以虚辞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107 人者之罪也。夫仁、义、智、信,岂有其物哉?总乎礼、乐、刑、政而命之,则是仁、义、智、信矣,故止谓之别名也。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法制者,礼、乐、刑、政也。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智、信。备其物,正其法,而后仁、义、智、信炳然而章矣。在李觏看来,"礼"是包含实在内容的总概念,是有其物的大范畴,不是空洞无物的小概念。他把"无其物"的仁、义、智、信,看成是"有其物"的"礼"的别名。"有其物"的"礼",就是法制,而法制就是礼、乐、刑、政。"无其物"的仁、义、智、信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则是"有其物"的"礼"。因此,李觏主张以人事实际的礼教人,不能以玄谈妙论骗人。李觏的这些思想,在北宋中期,学风空浮,道学盛行,道学家尚天道而远人事,尚空疏而下务实际的学风笼罩整个社会思想的情况下,无疑具有进步的实践意义,也是他的思想光辉之处。正因为这样,李觏的《礼论》七篇写成后十五年,章望之专门著文反对他的《礼论》思想,有人持章文来驳斥李觏。章望之指责李觏的《礼论》是"好怪"之说,是"率天下之人为礼不求诸内,而竟诸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饰焉,终亦必乱而已矣。亦犹《老子》之言'礼者,忠信之薄'。盖不知礼之本,徒以节制文章,献酬揖让,登降附仰之繁而罪之也。"①章望之以为,李觏的《礼论》是教天下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即不求之于主观动机,而务求客观实际。章望之是以唯心主义观点来反对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对于章望之的无理指责,李觏写了《礼论后语》,据理驳斥了章望之的错误思想。
李觏指出,章望之对他的指责是毫无道理、没有根据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这纯粹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的胡说。李觏认为,"礼"是内外一贯,表里如一的。他驳斥章望之道:我的"礼论"观点,何曾教人认为"礼不求诸内,而竞诸外邪?岂尝以节制文章之类为礼之实邪?章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②天下人都没有误解、歪曲我的"礼论"观点,只① 《礼论第六》,《李觏集》卷二、第18 页。
② 《礼论第五》,《李觏集》卷二,第16 页。
① 《礼论后语》卷二,《李觏集》卷二,第24 页。
② 《礼论后语》卷二,《李觏集》卷二,第24 页。
有你章望之才是有目不识、有耳不闻、有意歪曲,才以我的"礼论"为"好怪"之论,真是岂有此理。李觏继续驳斥道:夫章子以仁、义、礼、智、信为内,犹饥而求食,渴而求饮,饮食非自外来也,发于吾心而已矣。礼、乐、刑、政为外,犹冠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
呜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诸内者必出于外,有诸外者必由于内。孰谓礼、乐、刑、政之大,不发于心而伪饰云乎?且谓衣冠非自内出,则寒而被之葛,热而被之裘可乎?夏则求轻,冬则求暖,固出于吾心,与饥渴之求饮食一也。而章子异之,不己惑乎?故天下之善,无非内者也。圣人会其仁、义、智、信而为法制,固由于内也。贤入学法制以求仁、义,亦内也。李觏以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阐明了"礼论"观点,驳斥了章望之对他的指责。李靓指出,章望之以仁、义、礼、智、信为内,以礼、乐、刑、政为外,这是自相矛盾,也是理论上的迷惑不清,这种说法如同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是发自内心而为内者;当吃饱了,喝足了,穿暖了,便是出自外物而为外者。这种割裂内外的做法,显然是一种迷惑之论。在李觏看来,"礼"没有什么内外之分,它是根源于人的物质欲望需求产生的,是合乎人性,顺乎人情而制定的,是人的性情欲望所必需而形成的。性寓于内,礼呈于外,"有诸内者必出于外,有诸外者必由于内",因此是内外一致,表里一贯,不可分离,不容割裂。这就是礼、乐、刑、政等存在和表现的根据。所以说:"性畜于内,法行于外,虽有其性,不以为法,则暧昧而不章。"②李觏针对当时的学风、政风之弊,极力反对玄谈空言道德性命,不讲实事实功,以及妄分内外,重内轻外,主内遗外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内外一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思想,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知道,关于内与外之争,是北宋中期学术思想界,引申而及之政治界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继李靓与章望之的争论之后,王安石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围绕这个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王安石所代表的革新派主张,要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取,进行变法改革,求新图强,兴利除弊,振兴国家,富国强兵,以求改变"积贫积弱"的颓势。因此,他们反对老于消极无为的思想主张。王安石说:道有本有未。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木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王安石所讲的"本"就是"天"、"天道"、"自然";"末"是指人力的制作、创造。他认为,天道是无言、无为的,即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则是有言、有① 《礼论后语》,《李觏集》卷二,第24-25 页。
② 《礼论第四》,《李觏集》卷二,第11 页。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老子》。
为的。古代圣人就是依据人道有言有为的思想,而制作了礼、乐、刑、政"四术",这是为了"成万物"。而老子却说什么"道"是要废除礼、乐、刑、政的。在王安石看来,老子这种强本弃末,显然是把本与末、天与人混为一谈,去掉了末,本也就无意义了。其实质是不察于理的好高骛远之论,亦是消极无为之根。因此,王安石反对老子的消极无为之论,把"本"与"末"区别开来,要人们积极努力,以人力治末而成就万物,这就为其变法革新提供了理论根据。
司马光、程颢、程颐等所代表的保守派,与王安石等革新派恰恰相反。
他们以老子的守本弃末、消极无为的思想为理论根据,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武器。司马光说: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程颢、程颐兄弟,对王安石的革新思想主张,亦是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当时的一大祸害,甚至比佛学还要坏。他们说: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程颖多次当着宋神宗的面攻击"王安石之学不是"。说什么"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②司马光和程氏兄弟一派之所以极力反对王安石及其思想,就在于他要死死抱住那个人所不能干涉、无能为力的"道之本",主张消极无为,率由旧章,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祖宗之法。如果人们去研究"万物之所以成"的"道之末",积极有为,就是违反了祖宗之法。他们所说的"道之本",就是指人的主观精神,道德修养,即所谓"内";他们所反对的"道之末",就是指外界的客观事物以及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制作和革新,即所谓"外"。在他们看来,人们研究客观事物,制作和革新具体事物是"玩物丧志",而不是圣人之学,因此他们主张求于内,不必求于外。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可见"本"与"末"、"内"与"外"、"无为"与"有为"是相应的范畴。所谓"本"、"内"就是指"心"而言,所谓"末"、"外"就是指"物"而言。他们主张"求于内"、"求于本",就是要加强内心修养,从主观内省下功夫,不必求之于外物。因此,他们反对分析研究事物,综合考察事物,认为这样做既不利于身心,又无益于家国。司马光明确提出"治心"的主张,①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抓住了根本,才是圣人君子之学。他说:迂叟曰: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 安以学为?②迂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③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司马光、程颖。程颐认为,人们不必研究礼、乐、刑、政和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只要向内心寻求,反省体验,就是抓住了"道之本",这样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因此,不需要向外寻求,分析研究具体事物,去求那个"道之末",这才是圣人、君子之学。
由此可见,李靓与章望之,王安石与司马光、程颖、程颐等围绕着"内"与"外"、"本"与"未"之争,实质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
②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迂书·学要》。
③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迂书·治心》。
④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