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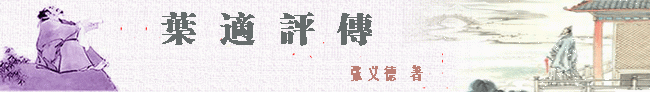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四 庆元党禁和学术争鸣局面的终结
庆元党禁(全称为伪学逆党之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一)庆元党禁的起因
庆元党禁在做法上模仿元祐党禁,但实际上二者有显著的不同。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其实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于韩侂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侂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侂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年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章惇、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侂胄之与庆元党人,本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裁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辩证》卷六,《史部》四)
余先生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元祐党人(后又分为蜀、洛、朔党)即所谓旧党与熙、丰党人即新党之争,是关于王安石新法的问题,而庆元党禁中韩、赵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分歧。朱熹也曾说:"元祐诸公后来被绍圣群小治时.却是元祐曾去撩拨它来,而今却是平地起这件事出。"(《朱子语类》卷一百七)这是说,被列入庆元党籍的人原来并未去惹韩侂胄一党中人。韩赵发生矛盾,是因为一个并不大的问题。
原来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太上皇赵昚逝世,光宗赵昚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赵昚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赵昚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知閤门事,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
朱熹并未参与"绍熙内禅"之事,对赵汝愚此举有所非议;他也曾劝赵汝愚用厚赏酬韩侂胄之劳,赵汝愚不听。因此,朱熹和赵汝愚很难说是一党。但因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还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朱熹。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二月赵汝愚罢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第二年正月死于衡阳。
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都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部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庆元党禁的特点是党禁和学禁相结合,以政治手段来禁止学术。庆元党禁与元祐党禁的不同,除了前面所引余嘉锡先生所说的以外,还有以下一点:元祐党禁虽然也禁程氏道学,但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而庆元党禁则不然,它主要的打击目标是朱熹道学,以政治手段来禁止一种学术,而实际上是使当时所有的学术都遭到禁止。因此,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学禁。而这种以政治手段来打击一种学术,把某种学术(如道学)作为一种罪名的做法,并不从庆元开始。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在孝宗朝(甚至高宗朝)就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在那时还没有真正的实行,没有这样大规模地展开罢了。这种做法的深刻的根源,我们留待后面进一步探讨。
总之,当权的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以道学为罪名、以政治手段打击一种学术的做法相结合,是庆元党禁的起因。
(二)庆元党禁的经过:由道学而"伪学",而"逆党",逐步升级
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更道学之名曰伪学"。当时有人"言道学何罪,当名曰'伪学',善类自皆不安。由是有'伪学'之目。"右正言刘德秀上言:"邪正之辨,无过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他要求宁宗"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
诏下其章。(《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按照以上的逻辑,似乎是把"道学"和"伪学"作了区分.他们只禁"伪学",并不一般地禁止道学。但是,实际上,他门是把"伪学"作为道学的代名词,禁止"伪学",也就是禁止道学。
庆元二年(公元1196 年)二月,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同知贡举、右正言刘德秀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入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上,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毁圣德,几至大乱。"他反对有人"倡为调停之议",而引用历史故事,危言耸听地说:"汉霍光废昌邑王贺,一日而诛其群臣一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应以为戒。他认为,"今纵不能尽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自是学禁愈急。接着,大理司直部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也就是说不许在朝中做官。到了十二月,又有选人余嚞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同上)。
在这当中,并没有人对"伪学"和"道学"作什么区分。王夫之就曾指出过这种所谓"伪学"的说法的虚伪性,他说:"道学者,非恶声也。揭以为名,不足以为罪。乃知其不类之甚,而又为之名曰'伪学'。言伪者,非其本心也,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固曰道学,不言伪也。"(《宋论》卷十三)
到了庆元三年(公元1197 年),道学之禁又升级,由"伪学"而"逆党"。
这是由刘三杰首先提出的。是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入见,论曰: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表,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淡性理之学,言一出口,嘘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盂,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淮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籍其力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后留止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倖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疏入,韩侂胄大喜,即日除刘三杰右正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
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凡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据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又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其实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三)庆元党禁的结果:凡学皆伪,学人遭难
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虽然在庆元以前,张斌、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这样著名学者已先后去世而幸免于难,但是,只要我们对列入《伪学逆党籍》的名单作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仍然样样俱全。
在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中,除了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等政治人物(他们是道学的支持者,但并非道学家)外,在学者当中属于道学家的只占少数。
如果按照《宋史·道学传》,只有朱熹和黄灏二人是道学家;如果按照《宋元学案》,属于道学一派的,还有刘光祖(晦翁同调)、楼钥(晦翁私淑)、彭龟年、吴猎、李皇、沈有开、范仲黼(以上为南轩门人),以及蔡元定等。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他们的道学是假的,那末,真正的道学又在哪里呢?
再进一步看,在列入党籍的人物中,还有朱熹道学的反对派,其中属于陆氏心学一派的,有杨简、袁燮、徐谊等人,他们是陆九渊去世后心学的主要代表;还有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陈傅良、叶适、蔡幼学、薛叔似等人。这两派是从不同的角度反对道学观点的。还有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和族弟吕祖泰等人。他们是东莱学术的继承者,吕学虽有调和诸派和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毕竟是不同于朱学的另一学派。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那末真正的学术和学者又在哪里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庆元党禁中,不仅道学即"伪学",而且是凡学皆"伪";这些根本不成其为"党"的各学派,都被宠统地称之为"伪学逆党"而予以排斥,为这次党禁的一大特色。
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必须在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科举时,应试者必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在当时,朱熹的"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甚至"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宋史·道学三·朱熹传》)"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
庆元六年(公元1200 年)三月,朱熹死于建阳之考亭。十一月,"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因此,"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辛)
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不在党籍,亦非朱熹门生,却能冒死哭祭朱熹。
朱熹一生经历坎坷,临终时处境凄凉。在他死时,连送葬也受朝廷的限制,由此可见庆元党禁对学者打击的严厉。
(四)党禁之弛和对道学的尊崇
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 年)二月,"弛伪学、伪党禁"。当时力主禁学的人已相继去位或去世,韩侂胄"已厌前事"。张孝伯对韩说:"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陈景思劝韩"当勿为已甚",都被韩所接受。(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大学士;党人健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林大中、詹体仁、蔡幼学、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灏、游仲鸿等,皆先后复官自便。又削荐牍中"不系伪学"一节。十月有旨,朱熹已致仕,可除华文阁待制,依条与致仕恩泽。十二月,周必大复少傅,留正复少保。"自是学禁稍稍解矣"(《道命录》卷七下)。
有的论著认为,禁道学是为开禧北伐做思想舆论准备,这是没有根据的,在庆元党禁期间,并无北伐的策划和行动。相反,弛禁倒是与开禧北伐有点关系。据记载,当时韩侂胄"且欲开边,而往时废退之人,又有以复仇之说进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在开禧北伐中,党籍中出任将帅者不乏其人。开禧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击杀韩侂胄以求和、这些人又以附和韩侂胄开边的罪名被罢官远斥。由此可见,把道学定为投降理论,禁道学是为抗战做准备,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l 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指出:"往者权臣(按指韩侂胄)顾以此学(按指道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窃谓当世先务,莫要于此。"又说:"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大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他还重提绍兴年间胡安国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从祀孔于之庙"的建议。但是由于当时西府(按指枢密院)中"有不喜道学者",未及施行。(《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嘉定五年(公元1212 年)十二月,国子司业刘爚,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从这开始,道学得到官方的承认。
宋理宗赵昀宝庆三年(公元1227 年)正月,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二年(公元1229 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国公。(《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 年)正月,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
在以朱熹从祀孔子庙的同时,又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罢黜其从祀孔子庙。不久,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到宋理宗时,程朱道学被定为官方思想。至此,庆元党禁才算彻底结束。但是,在庆元党禁中一起受到迫害的道学以外的各学派,如心学、永嘉学派等,却并没有象道学一样受到尊崇。它们虽然不再遭禁,但没有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仍是民间的。它们与道学的地位不再平等。在庆元党禁中被破坏的学术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五)关于庆元党禁的评价
庆元党禁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从它的起因(韩赵权力之争)看似乎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在大致叙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后,我们要进一步说它是必然的。
为什么在南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以政治手段来压制某种学术的现象(从郑丙、陈贾,经林栗,一直到庆元党禁)呢?原因在于,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从汉代以来一直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孔、孟儒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有一些封建思想家出来进行探讨,把孔、盂儒学加以改造,提出一些新观点,建立一些新体系。这些思想家看问题总是比较深一些,远一些,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就南宋而论,朱熹、陆九渊、叶适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做这项工作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一卷第52-53 页)就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来说,究竟哪一种思想体系有利于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选择的过程;即使这种思想被思想家们创造出来以后,也往往不被这个阶级中的多数人所认识,尤其是不被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所认识。相比之下,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往往不象这个阶级的思想家那样看得深、看得远,他们所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暂时利益和特殊利益,而不象思想家那样代表了该阶级的长远利益和一般利益。由于这种差别,就产生了矛盾,有时这种矛盾会尖锐比起来,形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在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看来,维护封建统治有孔孟思想就够了,不必再提出什么新思想、新体系,出现新学派。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恐惧感,生怕新思想、新体系的出现会引起思想的混乱,进而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从而动摇封建统治。特别是当一种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时,如道学在南宋广泛传播,这种恐惧感就越来越强烈。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传播,都是民间性的,非官方的,如朱熹的大量著作和讲学活动,都是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陆氏心学和永熹学派的学者也是这样,更不必说终身未仕的陈亮了。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由于无暇顾及和思想的局限,往往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缺乏理解,总是对他们不放心,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而这些当权者又是握有政治权力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如人事关系、争权夺利)就出现了同一阶级内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
南宋历次禁道学直到庆元党禁的发生,其源盖出于此。认清了这种根源,并不是抹煞这种学禁对思想文化的残害,相反,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适应)的危害性。以某种学术为罪,惩治思想犯,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特证,在庆元党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主要是压制农民阶级的反抗(尤其是禁铜他们的思想)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惩治起本阶级的某种思想和思想家来,也是毫不手软的。扼杀本阶级的有生气的思想,残害本阶级的有远见的思想家,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这种自相残杀,从历史上来看是暂时的。随着历史向前推移,时过境迁,封建统治阶级终于发现,某种思想(如道学)不但对封建制度无害,反而是有利的,它比原有的孔孟儒学更适应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到了这时,封建统治者就把原来被压制的学术思想(如道学)和学者(如朱熹等人)尊崇起来,上升为官方思想,而且越抬越高,直到当作神灵供奉为止。
到这时,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就表现为强迫人们接受破抬到官方地位的统治思想(如道学),谁如果对此非议,就要受到压制和打击。大体说来,一种思想(如道学)后来被抬得多高,同原来被打击得多重成正比;后来所戴上的闪耀着灵光的桂冠,同原来被扣上的政治帽子,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历史讽刺画。所不同的是,当统治者禁上某种学术(如道学)时,是横扫一切,与此并存的其他学派和学者同时受害;而当一种学术(如道学)被推崇起来时,那些同时受压制的其他学派,却没有受到重视,仍被冷落。在学禁时,各学派的分歧和争论被置之不顾,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打为"伪学";而道学被抬到官方地位时,它同其他学派的分歧却被注意了,被计较了;其他学派虽与道学同当其难,事后却不能分享其"福"。以百花被杀的代价,换来了一花独放的结果,损失是何等巨大。而收获又是如此的微薄。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面,还能企望有更好的结局吗?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