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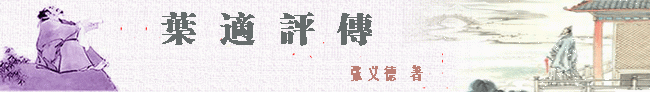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二论"极"
"太极"、"无极"是道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也是道学与心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叶适对这些范畴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在淳熙年间写的《进卷》中,对"太极"还是肯定的,如他说:有《卦》则有《易》,有《易》则有太极,太极立而始终具矣,因而两之而变生焉。(《易》,《水心别集》卷五)在这里,叶适还是把"太极"当作与"道"同一序列的范畴加以肯定的。到了《习学记言序目》中,叶适才对"太极"、"无极"等范畴重新做了考订,认为是古圣贤所不道,《易经》所无,《易传》作者所加而为近世学者(道学家)奉为"宗旨秘义",而采取了否定态度。但是,叶适否定"太极"、"无极",并不否定"极",而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极"作了自己的解释。
(一)认为"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
首先,叶适认为"极"是"物之极","极"不离物。他说: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皇极》,《水心别集》卷七)
这就是说,"极"本身不是物,但是,"极"又是不能离开物的;"极"是物之极,因此必须通过物去讲"极",去"建极",这就是"自有适无";与此相反,离开物去讲"极","以无适无",则"极"无从而建。因此,"极"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有与无的关系问题。"极"不能离物,犹如无不能离有一样,不能从无到无。在这里,叶适实际上是在批判道学家和心学家(朱与陆)关于"无极而太极"问题的玄虚辩论,而自己另辟蹊径,发出新论,与之鼎足而三。
《老子》一书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学家的"无极而太极"(按据清人考证,应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本于《老子》的"有生于无"之意。《老子》书中和朱熹的言论都有关于"车"和"室"的论述,表明了他们的"以无适无"的思想。《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十一章)朱熹说: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朱子语类》卷六)《老子》和朱熹的理论都认为,事物的性质和作用,都是由那些抽象、空洞的原则(老子称为"无",朱熹称为"理")所规定的,而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叶适对老子的上述言论,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老子之为是言也,所以明无也,然适见其无者而已。天下之物,当其有而用者皆是也,何未之思乎?然则有无不足以相明,而道之所不在也;盖老子之所操者虽微而狭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五)
这就是说,老子强调了"无"而忽略了"有",他不知道"天下之物,当其有而用者皆是也",因此老子的思想方法虽精微但偏狭,实际上是片面的。叶适还指出,这样来论事物,是"得其中而忘其四隅,不知为有而欲用之以无,是以无适无也"(《皇极》,《水心别集》卷七)。如房子,"得其中而忘其四隅",没四壁和屋顶,只有空间,那就什么也不是了,谈什么"室之用"呢!叶适运用他自己关于"所以建极者则有物"的思想,对车之为车、室之为室,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老子和朱熹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说:室人之为室也,栋字儿筵,旁障周设,然后以庙以寝,以库以厩,而游居寝饭于其下,泰然无外事之忧;车人之为车也,轮盖舆轸,辐毂辀辕,然后以载以驾,以式以顾,而南首粱、楚,北历燕、晋,肆焉无重研之劳。夫其所以为是车与室也,无不备也。有一不备,是不极也,不极则不居矣。(《皇极》,《水心别集》卷七)
这就是说,"车"和"室"只有构成它们的那些具体材料和部分都已具备、一件也不缺的时候,才具有"车"和"室"的性质和作用;不然,"车"就不成其为"车","室"也不成其为"室",就不能起到"车"和"室"的作用;这就是"所以建极者有物也"。当然,"车"和"室"之所以为用,有其"无"的因素(如"车"之"毂","室"之空间),但这"无"是包含在"有"("车"、"室"的具体材料、部分)之中的,不是离开了"有"的"无"。也就是说,作为"车"、"室"的概念,是不能离开组成"车"、"室"的具体器物,以及作为它们这个整体而具有的性质和作用的。《老子》之失,在于只见"车"、"室"之用的"无"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有"的方面;朱熹之失,在于强调了抽象的"理"而使之脱离了具体事物;他们的共同点是离开了具体事物去讲"极","以无适无",而不知"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这个道理。叶适坚持"自有适无"而反对"以无适无",就是坚持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去讲"极"。根据同样的道理,叶适也反对那种抛开具体的礼乐器物和仪式而空谈礼乐概念意义的理论。他说:《诗》称礼乐,未尝不兼玉帛、钟鼓。??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离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八)
这就是说,礼不等于玉帛,但离不开玉帛;乐不等于钟鼓,但离不开钟鼓;这与"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是一个意思。
(二)"极"是物自身的一种状态
以上所说,是所谓"建极"的问题。那末"极"指的是什么呢?叶适列举了一系列事例,进行了说明: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革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姓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于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导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天地之内,六合之外,何不在焉?立于不测,传于无穷,并包洪濛,执知其终!夫非为其有此极耶?(《皇极》,《水心别集》卷七)
这就是说,"极"是普遍的,"极"存在于各种事物之中,有一事之极,一物之极,一身之极,一家之极,乃至国家、天下之极,既然"极非有物",都不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那么,它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或特性:从"有一不备,是不极也"说,"极"就是事物存在的整体性;"极"是事物内部或物与物之间一种最和谐的状态,事物的这种内在的和谐性是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也是此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界限。圣人掌握了大道,对事物进行治理使之保持其区别(异)而不混淆其区别(害其异),这就叫做"皇极"。
"皇极"一语,原出于《尚书·洪范》:"皇建其有极"。皇意为大,极,屋极;皇极指帝王施政的最高准则。陆九渊认为在天有"太极",在地有"皇极","皇极之建,??根于人心,而塞乎天地","圣天子建用皇极,亦是受天所赐。"(《象山先生全集·杂说》)叶适对"皇极"的解释,以各种事物各自有其"极"为前提,"极"为物之极,"皇极"是帝王(圣人)根据事物本身的规律(道)来进行治理,而使事物保持其"极"。这样的解释,与陆九渊认为皇极"根于人心"和道学家们的超然万物之上的所谓"太极"、"无极",都是根本不同的。叶适和道学、心学在"极"问题上也表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三天道、人道有别的思想和反对迷信古代唯心主义鼓吹有意志的"天"主宰世界、干预人事,人是受"天"之命,宋代道学家以"天理"代替"天命",否定了"天"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性质,但"天理"仍是超然于天地万物的精神实体,实质仍是一样的。
叶适继承古代唯物主义"明天人之分"的思想,主张天道、人道有别,天道不干预人事,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是对宋代道学家的"天理"论的批评。叶适说: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这里说的"天"是自然之天,"天道"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人可以认识"天道",顺应而不违背它;但不能把"天道"和"人道"等同起来,看成是"影"和"形"、"响"和"声"的关系,因为二者是有区别的;对于人事,则应该尽"人道",如果不是这样,而去"求天"、"责天",那就"人道尽废"了。叶适进一步指出: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日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所当阙也。(同上)
天下命人人自命,得失祸福反自身,天道不干预人事,这是叶适对"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基本看法;而那种认为"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的天命论,则是为"古圣贤所不道"、"君子所当阙"的。
显然,叶适的天道与人道有别、天道不干预人事的思想,正是先秦荀况的"明天人之分"思想的继续。但是,叶适却反对荀况"官使天地"的说法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命题。他认为,古圣人为求"知天"、"则天"、"奉天","未尝敢自大其身而曰'吾能官使天地'者也","未尝'物畜而制之'也","未尝'制天命而用之'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四)。
其实,在天人关系上,叶适与荀况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叶适把重点放在"则天"、"奉天",即顺应自然规律方面,但并不取消人的努力;荀况把重点放在"官天"、"制天",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但并不认为人可以无视天自身的规律。比较起来,叶适对人类自身战胜自然的自信心和能动性的理解上要比荀况稍差一些。而思想上的这种差别,则是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的不同:荀况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是奋发有为的;而叶适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已失去了早期那种奋发向上的气势了。
根据天道与人道有别、天道不干预人事的思想,叶适批评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他批评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指出"人主皆以有德王,无德亡"(同上,卷二十二),朝代兴亡与五行生克毫无关系。叶适进一步提出,"水火金木土谷,则五行也",是自然事物,而"正德、利用、厚生",则是人间的"庶政群事也":二者不是一回事。古之圣人利用它们,"欲其顺天行而万物并育",也就是"顺五行之理以修养民之常政";而汉儒却把五行与君主一人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虽有德而智与力不具,则亦无以致五行之功",这就"仅救(人主)一身之阙以冀五行之顺己",用这种"天人感应"的方法来论事,"则汉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同上)。这是对刘向《五行传》的批评。《五行传》把"五行五事联附为一","五事"即《洪范九畴》中的貌、言、视、听、思。叶适说:"五事者,人君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同上),这是人自身之事,并非自然物。《五行传》"以五事配五行",从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至今千余年,终未有明者,殆可为痛哭耳!"(同上)汉武帝向董仲舒征询对天道之要的看法,董仲舒却向他申说阴阳灾异,结果根本无助于武帝。这种"灾异"说在汉代十分盛行,但到千余年后的宋代,对道学家的思想仍有影响。"灾异"说的实质,是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叶适批评"灾异"说,批评"以五事配五行",是反对有意志之"天",同时也是反对宋代道学家把道德赋予"天理"的道德之"天",而还"天"以自然之天的本来面貌,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
按照天道不干预人事的思想,叶适也反对了神怪、风水等迷信思想。他批评《礼记·祭义》中载宰我与孔丘的问答,认为"尤为诞浅而不经"。他说:"且生生死死,人道相续,冥冥而昭昭,神道常存,乌有待人死之气而后为神,待人死之魄而后为鬼者乎?骨肉为土,气为昭明,使神道之狭果如此,岂足以流通于无穷乎?"(《习学记言序目》卷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足以否定鬼神的迷信,但叶适认为对这个问题还是保持孔丘那种"绝神怪而不言"的态度为好。对于封建帝王的"封禅",叶适持反对态度。他说:"封禅最无据。"他认为,古代并没有封禅之说,"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默天也"。他对司马迁"亦知其非,不能论正,反傅会之"(《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深为不满。对于两汉盛行的图許迷信,他认为更是荒诞不经。
他说:"至后汉又以許文封掸,益无据矣。"(同上,卷二十四)他对占验迷信也批评说:"吴范(三国时吴人)占验存亡兴废,无不审中,使如其言,无用人事矣,将天定而人从耶?将人为者天合耶?将如物之形立而影随也。"(同上,卷二十八)他认为,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是人为的结果,而绝不是鬼神所能决定的。高洋敬礼道人陆法和,是由于畏惧"冥祸",叶适说."国之将亡,固听于神也"。他认为:余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智巧于其间;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同上,卷三十五)
又说:然则人力之所能为者,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龟者,又非神怪之所能预,真不足复顾也。(同上)
鬼神根本不能知道人事,更不能改变"天数"(即客观的必然的规律)。
而国家的兴亡成败,取决于仁义忠信这个人之"常道"。对于迷信风水,叶适也予以批评。他说:余尝怪苏公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一身岂能应四方山川之求;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藏穴,门人裹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阴阳精义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通人"指苏轼,"大儒"指朱熹,对他们迷信风水的行为,叶适很不以为然。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