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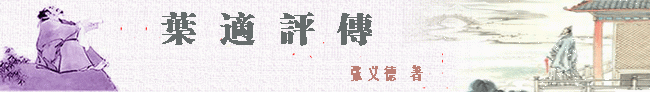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一人性天赋论
叶适认为,人性是天赋的。这里所说的"天",并非有意志的神秘之天,而是自然之天,因此,天赋也就是天然的意思。人和万物都是物,但天所赋予人者与天所赋予万物者有所不同:天对人只能"降衷",也就是"中和之性"为人所独得;而天对人和万物是"降命",人与物同受。叶适是这样区分"降衷"与"降命"的:按《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万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间,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
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盖人之所受者衷,而非止于命也。(《中庸》,《习学记言序目》卷八)这就是说,人与万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觉的意识,能认识事物之当然,因而能"率(循)性";而万物"止受于命",不能"率性",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有自然本性。叶适意识到人与万物的这种区别,是一个正确的开端;但他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事物的这种区别,不在于天赋的不同,而在于人具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因此,他的天赋人性论,不免陷于抽象的人性论。
人性的善与恶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叶适既反对性善论,也反对性恶论。他肯定孟轲"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按指天下风俗大坏),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而入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夺之中"(《孟子》,《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在这里,叶适肯定了"孟子之功,,有两点:一是在人们"搏噬、噬夺"之中发现"人性之至善";一是指出人们之所以互相"搏噬、噬夺",是由于人"不幸失其所养",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所以不得不互相争斗,这是"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这个思想显然与孟轲的"民贵君轻"思想相一致,强调了人性(善性)的维持与保证人民的应有生活水准相联系,是有进步意义的。叶适认为,孟轲关于人性的思想的以上合理性,是与当时天下风俗大坏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不能脱离这个背景抽象地看。对于孟轲的人性善的思想,叶适还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言性之正",还应该以孔丘所说的"性近习远"为准,"非止善字所能弘通"(同上),不能用一个"善"字来概括。他批评"后世学者",不顾孟轲此论的历史背景,"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同上)
同样,叶适也认为,人性也不能以一个"恶"字来概括,对荀况的性恶论也持反对态度。他批评说:"知其为恶而后进夫善以至于圣人,故能起伪以比圣,使之终于为善而不恶,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欤?"(《荀子》,《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四)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能成立。同样,根据孔丘"性近习远"的论述,叶适认为,"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因此,性恶论也是不对的。总之,叶适认为,天赋的人性,本是无所谓善或恶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