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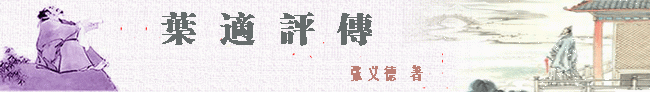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三义利统一论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同理与欲的关系相一致的,分开来说,只是为了理论上论述的方便。义利之辩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利。而我国从先秦以来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往往只讲义与利相对,而排斥利与害相对。因此,在研究叶适的义利统一论时,要从他如何看待利害关系入手。
(一)要不要讲利害关系
南宋晚期(当时道学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的罗大经,曾有一段关于利害和义利的记载和议论,颇能说明问题,兹录于后: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誊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日"害"。张曰:"误矣,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
'利'字,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辨。一揖而退。(《利害》,《鹤林玉露》甲编卷三)这里所记的是绍兴年间的事,当时道学传播不广,在士人中讲利害的还不乏其人,象张登这样只讲义利而不计利害的议论,还是颇为新鲜,与罗大经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当然,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利"是不是只能同"义"相对而不能同"害"相对?应该不应该计较"利害"关系?叶适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不同于道学家的回答。首先,他肯定就利远害是人心之所同。他说:人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远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胶于中者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五)
这就是说,利害之心是"人心"所固有的,其作用是成养生送死之事,出于人求生存之本能,是人的自然本性;而"道心"起着调节"人心"的利害生死关系,使之安其分的作用。因此,叶适认为,计较利害,就利远害,是自然之事,只要不越其分就可以了。
叶适认为,"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官法下》,《水心别集》卷三)他说:"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则无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同上)圣人并不压抑天下之人获利的愿望,而是使获利之门路通而且广,从而使天下之人"程其功能",各得其所;同时"为之立其等秩",据礼仪名分使其得应得之利,按名分应食而食之无愧,不然,则"虽饥且死,不敢食矣"。如果"操利天下之权而示其抑天下之意",那就必然使人们为争利而"天下相攻之不暇",这样,"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为治哉!"(同上)因此,叶适"以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与之之心。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同上)。这就可以达到天下至治的目的。显然,叶适此论与道学家根本不言利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
叶适议论得最多的,还是国家民族的利害、天下的利害。在认识上,他认为,"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十四);在行事上,他认为,"非先尽(去)其害,则不能得其利,害尽去则利见矣"(同上,卷十)。可见叶适的思路是与道学家不同的:道学家认为,利害是不必计较的,凡事只要从"义"出发,有了"义","利"也就有了;而叶适认为,认识要先从"害"入手,然后才能知"利"之所在,去"害"才能见"利"。因此,只讲"义"而不计"利害",是空言;而他自己从"害"到"利"以明天下之大"义",才是实谋。由此,叶适建立自己的改革思想:改革就是去害兴利,改弱就强,最后实现复仇的大义。叶适深入地研究了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积弊(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达到兴利除弊(害)的目的。他认为,"利惟谋新,害不改旧"(同上),因而奉劝孝宗皇帝"究观古今之变,尽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难易之实,解胶固,申挛缩,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同上,卷十五),改革弊政,使国家富强起来。如果说,个人的私利,没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会与"义"相冲突,那末国家民族的利益就有所不同,在南宋,为国家民族而兴利去害,是实现复仇和恢复故土的有效途径,因此,在这里利和义是根本一致的。如叶适所说:"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同上,卷九)道学家虽然不否定复仇之大义,但他们反对计较利害,只想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其"义",实际上是对革除当时的弊政失去了信心。叶适从揭露当时的积弊入手,提出兴利除弊的改革主张,以实现其复仇之大义,是将义与利统一起来的表现。这是叶适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崇义以养利":义与利在观念上的统一
叶适注意研究利害,主张兴利除害,但他并不主张单纯寻利,而是注意把义和利结合起来,以义来约束、规范利。因此,他在义利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士学上》,《水心别集》卷三)。
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对了两个极端:义理之是非在目前者常又不能守,而每以利害为去就,盖自古而然;而又有庸人执以为义理之所在非圣人不能择者,亦自古而然;二端,学者不可不谨察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
这两个极端各偏一面,都不能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因此是叶适所不能同意的。叶适认为,利和义的关系,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不是"自古而然"的。他说: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杀,以力自雄,盖其常势,虽炎黄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尧舜以身为德,感而化物,远近丕变,功成治定,择贤退处,不为己有,而忠信礼让之俗成矣。夫先人后己,徙义远利,必出于心之自然而明于理之不可悖。
(同上,卷三十五)
在这里,叶适认为人类之初有一个不知礼义、为利而以力相争相杀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野蛮时代;后来由于尧舜这样的圣人进行道德教化,才有礼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得到治理。从历史来说,这样的区分并不十分准确。如在原始野蛮时代,虽然氏族、部落之间厮杀频繁,但其内部还是保持着平等和谐的习俗;而在所谓文明时代,虽有礼义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但也不免有为利而进行的争斗。叶适作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说明利与义的关系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并非自古而然,这是有可取之处的。
当然,他还不可能揭示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重要的是,叶适按照儒家的传统,设想了一个从尧舜开始的"圣人之治"作为他的道德理想境界。
在叶适的理想境界中,"民与君为一","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民事上》,《水心别集》卷二);"古之圣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从君民关系说:"盖自君言之,则当先民而后君;自民而言之,则当先公而后私;理各有所正,不苟自晦也。"(同上,卷十)总之,养民与教民、衣食与礼义、生养与道德是相结合的,义和利是统一的,因此叫做"生养之仁"。叶适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同上,卷十一)
这就是说,在古时,义和利是统一的;而到后世,人们把义和利分割开来了,这是古今的分别。后世把义和利分割开来,表现为两种极端的观点,叶适批评说:陋儒不晓,一切筑垣而封之,反以不言利自锢,而言利者遂因缘以病民矣。(同上,卷二十二)在这里,叶适反对了不言利而只言义的空言和言利者不顾义以病民两种偏向。在反对两种偏向的同时,叶适着重反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后世学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这"后世学者"指的就是宋代的道学家。
叶适指出:"《诗》、《书》所谓稽古先民者,皆恭俭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义"(同上,卷二十三),在义与利之间并无偏废。
据此,他批评了董仲舒:"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诡于天下矣。(同上,卷二十)
这就是说,排斥了功利,道义就成了"无用之虚语",这是不合于《诗》《书》所传的圣人之道的。叶适在这里批评了董仲舒,同时也批评了空谈义理的宋代道学家。那种认为"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其言与宋儒大异,盖正其谊,利即在其中,明其道,功即在其中,董氏并无斥功利之意,叶水心痛诋之,以为乃无用之虚语,未免太过"①的评论,是不正确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宋儒(道学家)与董仲舒只有小异,并无"大异"。如朱嘉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又说:"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不要做这一边,又思量那一边。
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朱子语类》卷五十一)这显然是在发挥董仲舒的观点,因此,叶适把董仲舒和道学家的观点一概斥为"无用之虚语",实在是一语中的,并不过分。
① 贺昌群:《论王霸义利之辨》(写于1940 年),载《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以上引文见29 页。
(三)摆脱义与利在现实中的不统一
叶适认为,与"生养之仁"的理想境界相对照的"后世",即现实中,情况正好相反:"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民者";君对民"不养不教,专治民";甚至"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民事上》,《水心别集》卷二);"上下无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斗其力,专其利,争夺而不愧,赡足而不止。"(《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叶适认为,"损益之成理"应该是:"以损之道言之,惟在我者可自损以益人";而"以益之道言之,必在上者自损而可以益下";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世之纷纷乎损人以益己,剥下以丰上"(同上,卷二),以至于"上下苦心劳力奉行刻剥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同上,卷二十二)。实行这种"剥下以丰上"的"刻剥之策"的结果,使得民"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徒相搏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诈淫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民事中》,《水心别集》卷二)。
由上可见,叶适关于养与教、利与义、衣食与道德相结合,即"生养之仁"的理想境界,与他所面对的那种养与教、利与义、衣食与道德相脱节的现实,即"渔食之政",有着非常尖锐的矛盾,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在这当中,一方面是因为民无所养、衣食无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保证,而在道德上"无信义忠厚之行";另一方面是在士大夫即统治阶级里面分裂为"以不言利为义"的所谓"君子"和"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的"小人"。叶适指出: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以为是固当然而不疑也。
呜呼!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无疑,民之受病,国之受谤,何时而已!(《财计上》,《水心别集》卷二)
这里所说的"聚敛",就是前述"剥下以丰上"的"刻剥之策"。由干当时的社会舆论都把仁义道德和理财言利对立起来,把理财言利看成是不合仁义的不道德的行为,君子"徒有仁义之意"而"避理财之名",这样,理财之权就落到了"无仁义之意"的小人手里,小人就把理财变成了"聚敛",只知"刻剥","取诸民而供上用",而且是"务以多取为悦",使得人民和国家都受其害。叶适揭示了"以不言利为义"的"君子"和"无仁义之意"的"小人"互相并存而且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关系,构成了现实封建社会的一幅讽刺画,从而揭露了那些"徒有仁义之意"的"君子"所标榜的道德的虚伪性。在叶适看来,"聚敛"之害,虽是"小人"之所为,但是任用"小人"的"其上"(实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和"避理财之名"的"君子"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因为"其上""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而"君子"侈谈"仁义"而把理财之权推给了"聚敛"之"小人",让他们去"刻剥"百姓,这样的"仁义"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叶适尖锐地批评说: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为是耶?(同上)
"仁者固为是耶"的质问,揭露了那些"以不言利为义"的"仁者"的虚伪性。他们本来是"坐视小人"为"聚敛"之行,并且"以为当然";只是在事后人民怨恨了,才装模作样地"厉色而争",其实不过是为推卸责任而保住自己的名声而已。叶适把"以不言利为义"的空言和行"聚敛"以"刻剥"百姓之实二者联系起来,以揭露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是很有意义的。
叶适既痛恨那些以理财为"聚敛"的"小人",也不满那些空谈"仁义"的"君子",而主张实行一种真诚而不虚伪的道德(其内容仍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从而把"仁义"和理财言利统一起来。从经济思想上,是把理财和聚敛区别开来;从伦理思想上,是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他主张,从"仁义"、"爱民"的思想出发,以定"今之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有余不足之数",发"天下之遗利",使天下之人"得而用之",从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同上)。这就是叶适所说的非"聚敛"的理财,合于"仁义"的言"利"。其实际措施就是"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水心别集》卷九),罢去各种苛捐杂税,使"民所谓不正之敛皆无有"(同上,卷十五)。
这是叶适经济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前面已介绍过了。从伦理思想来说,叶适是主张以"仁义"来规范理财,从而给他的经济改革设想提供思想道德方面的保证。因为任何一种改革,都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其中不免要触犯一些人的实际利益,要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做出一定的牺牲。在这里,确实需要道德起作用。但是,这种道德不是"以不言利为义"的空言,而是义与利结合的真诚的道德。叶适指出,"人之养六畜",尚且"时其饥饱,为之圈牢,求所以利之";但是,上之治民,对"民之饮食居处,上则夺之以自利,是不如六畜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五)。因此,他要求在"上"者有所节制,改变"夺之以自利"的"刻剥之策",使"民之饮食居处"之"利",即起码的生活条件得到保证,然后才谈得上"礼义"。他同意"治人如治水潦"的比喻,认为"若上以礼义为坊,谨而勿慢,如以治水潦之道治之犹可也。"(同上)这就如同积水顺其道而得到疏通那样,以"礼义"为堤坊,使"利"受"礼义"调节,顺其道而得到疏通,从而把"利"与"义"统一起来,上下各得其利,各安其分,都合于"礼义"。这就是叶适为摆脱现实中的"义"与"利"的分离而要求二者统一起来的思想。
应该说,叶适这种义与利统一的伦理思想并不是很高的要求,而且也并未超出封建伦理纲常的界限,如同他的政治、经济改革思想并未超出封建制度的界限一样。他在伦理道德领域中所作的批判,无疑切中时弊。但他没有看到,道德的根源深藏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正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映,而这种虚伪的封建道德正是封建的"刻剥"制度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刻剥"越来越严重,就更需要虚伪的道德来维护它。因此,叶适要求在"上"者抑制"刻剥"其下以利于民和实行真诚而非虚伪的仁义道德,终归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四士人价值论在叶适的伦理思想中,关于士即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论述,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古代,士农工商同属四民,但士作为精神生产者,又与农工商这些物质生产和流通的承担者有所不同。叶适认为,"士农工贾,族姓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圣人作"皇极","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水心别集》卷七),就是对这种社会分工的肯定。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士就有自己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和特性,如叶适所说:士在天地间,无他职业,一徇于道,一由于学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学无仕无已,始终之也。集义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学之成也。(《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水心文集》卷十一)
这就是说,士的社会职能,一是行道,一是为学,都是属于精神生产。
由于这种不同,因此,叶适认为道德修养上的表现也不相同。他在论述"德非种不成"时说:义勇而先,利怯而后,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则廉者种之,贪者毁之也。??为其原不为其薄,治于己不治于人,宁散无积,宁俭无忲,皆所以种而不敢毁也。
朝种暮获,市人之德也;时种岁获,农夫之德也;种不求获,不敢毁,不敢成,圣贤之德也;冲漠之际,万理炳然,种者常福,毁者常祸,天地之德也。(《郭氏种德庵记》,《水心文集》卷十一)
这里所说的"天地之德"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市人之德"即工商之德,它与"农夫之德"一样,都是种而求获的;而"圣贤之德"是种而不求获,虽非士人普遍能做到,但是士人道德修养的高标准要求。"种德不求获",用现在的话说是做了好事不求人报答,也就是"无私奉献",叶适认为只有士人中的"圣贤"才能做到,而农工商做不到,这是他的局限性;但他对士人的道德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很有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认为士人"学无仕无已,始终之也",从而把"士"与"仕"区别开来,是对读书为做官的世俗观念的一个否定,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价值观。他说:方周衰不复取士,冻饿甚者儿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学也,道在焉故也。后世取士矣,师视其取而后教之,士视其取而后学之。夫道不以取而后存也,故愈微。(《信州重修学记》,同上)
在这里,叶适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士的道和学,同统治者的取士,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不取士,师教之,徒学之,道在;取士,师为取而教,士为取而学,道反而微。叶适又说:秦、汉以前,士自为家,造智设巧,意出准量,立表极以号于世而已;??至后世,折衷之学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论之,知所统壹,足以致用,不必自为家焉。然非其趯然出于科举场屋之外,详考而深思者不能也。(《粹裘集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这就是说,那些"出于科举场屋之外"的士,往往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把学业仅限于应科举,那是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成家立派就更不可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凡应科举的士人都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成就。实际上,与叶适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陈亮等,都中过进士,而叶适本人还是进士第二名。叶适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思想境界和治学道路。在思想境界上是不以应试做官为唯一目的,在治学道路上是不以举业为限,而是"学无仕无已,始终之",走着自己的治学道路,做个"详考而深思者",才能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因为叶适自己经历过科举,他对这种制度的弊害有深切的了解。
对科举制度,叶适有一根本性的批评:古者化天下之人为士使之知义,今也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
(《法度总论三》,《水心别集》卷十二)这个对比,反映了叶适对知识分子价值的看法,有颇深的意义。请看他的解释: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盖羡于为士则知义,知义则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穷人情之所欲慕者而不足以动其所守之勇。(《科举》,同上,卷十三)
叶适的理想境界,是"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这就是"知义",其含义就是"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在他看来,爵、禄都是身外之物,"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就是士以自身之贵为贵,以自身之富为富。
也就是说,士本身就具有其价值。那末,士本身的价值何在呢?就是如前所述的"道"和"学",就是士之成为士的那些事业和特性:道德、品格、思想、学问、知识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文章。这些本身就具有其价值,而非爵、禄这些身外之物所能衡量。所以,士之贵以道德品格之高尚为贵,士之富以思想学识之深广为富。坚守其自身之价值而不为"人情之所欲慕者"(如爵、禄等)所动,是士的理想人格。至于这种理想境界和理想人格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现,我们在此不作深究;或许这正是叶适借历史上的"至治之世"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而对不理想的现实的一种超越。
但是,叶适对与此相反的"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的批评,却是非常现实的。如他指出: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砺,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同上)
在科举制度下,总角小童就习举业,以追求入官为唯一目标,而置品格锻炼、义理性命于不顾,从而坏天下之才至于无用,道德与学业两废。这是由于科举制"以利(爵、禄之利)诱之于前而法限之于后",以至于"假冒干请,无所不为"(同上)。在科举制度下,士不以自身之贵为贵、以自身之富为富,而以爵为贵、以禄为富,爵、禄成了衡量士的价值的标准,入官为学业的唯一出发点与归宿。这样,学业本身就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了"敲门砖",入官之门敲开,砖即弃置门外而无用。这就是说,士本身的价值不成其价值,不为社会所承认,也不为自身所持守;而以爵、禄为价值,不入官则无价值,入官以取爵、禄反过来支配士自身。这就是科举制度使士的人格发生了异化。由此可见,叶适批评科举制度"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是何等的深刻。
自从精神生产部门同国家机构相分离,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阶层士以后,如何处理封建政权同这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吸引天下知识分子按照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来为其服务,始终是封建社会巩固和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尝试,但都不够完善。隋唐以来,逐步实行了科举制,较好地处理了封建政权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吸引了天下的知识分子为封建政权服务,并且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制。因此,科举制比起以前的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来,是人才选拔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是很显然的。这些合理因素,甚至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所吸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公务员制度,也不应忽视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历史上的事物往往是得失相伴、利弊相随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以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丧失为代价的。由此而产生的以做官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依附于封建统治者的依附人格),成了沉重的历史重负,使我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其害。有鉴于此,叶适发出了"出于科举场屋之外","详考而深思者"才能在学术文化上做出贡献的议论。当然,这只能是当时部分现实的反映,从总体上看,勿宁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是他对知识分子保持其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和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向往。事实上,科举制度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路程可走,废科举只是到了近代才实现。因此,叶适的上述意识是超前的。
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现了我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共同特点,具有代表性。这共同特点有二:其一是以"利民"、"利天下"为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其二是主张以"义"谋"利","义"与"利"统一。这种功利主义肯定人的私利,但更强调公利;它并未引向利己主义,反对见利忘义。因此,这种功利主义实为一种社会功利主义,或可称为公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与西方的传统功利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为基点和归宿,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是以"群体为本位"(或"家族为本位")的社会,而西方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叶适以这样的功利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反对了理学家"存理去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并论证了兴利去害的改革主张。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