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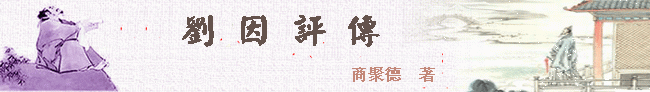
|
三、关于学史
关于学史,刘因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观点,主要有:
(一)学史须以经为本
刘因把经史子集的学习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的过程,其先后次序不能不讲究,他认为,"经"是基础,史、诸子等的学习应建立在学经的基础之上。他说:《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飏,在吾目中。刘因认为,史实是具体的,兴废成败、错综纷绩,读的人如果没有主见,就会被史实牵着走;史书是后人写的,叙事言理,评判臧否,不见得都确当。有了六经语孟在胸中,就有了一个标准("平衡"),有了一面镜子,就不致被某些史家所欺了。②刘因此说,可能是受到朱烹的影响。朱熹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③但朱熹此话仅是在谈论别的问题时附带提及,刘因则把它上升到学习方法论的高度,并对其道理有所论述,理论色彩有所提高。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② 参阅刘因诗:"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 恐有无边受屈人。"(七绝《读史评》,《静修先生集》卷--,页二○ 九)
③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页二九五○。朱熹在给 吕祖谦的一封信中也谈到过这个为学之序的问题,并说是本于程子。 他说:"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了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读史,其序不可乱也。" (《朱子大全》卷三五《答吕伯恭》)
(二)古无经史之分
刘因在谈学史问题时,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著名观点。他说: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刘因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受到王通的影响。王通曾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注:史有记言,求言则制度得矣。)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注:史有明得失,穷政化则诗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史有记事,稽邪正则法当矣。)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注:载言,载事,明得失,皆史职也。职同体异,故曰分。)王通把《书》、《诗》、《春秋》说成是圣人(孔子)所述的史,意在强调三书记言、明得失、记事的不同体裁及其意义。刘因则进而明确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经皆史"的观点,显然是一个发展。它强调的是经源于史,但经过孔子的选择、删定、笔削(修改并赋予一定的寓意)和传述,从而为后世确立了"大经大典",才被人们尊奉为"经"。刘因的这个说法,验诸历史,是符合实际的。《春秋》原是鲁国史,《诗》是古代文学史料,《书》是古代政治制度史料,"史"字在古代含义宽泛,史实、史料、史书、史官,都可称作"史"。如果从史料来理解,"六经皆史"之说,在今天也是可以成立的。
刘因此说,主观上当然并不是要贬低"经",但确实是想抬高"史"。
而从其客观效果说,不可否认,它确实有破除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作用。刘因此说,后世颇有响应者。明代王守仁说:"以事言渭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①李贽也认为,"经史相为表里"②,与王说相近。清代章学诚针对汉学家埋头考据的时弊,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写出来的。③此后,龚自珍、章炳麟也同主此说。④章学诚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破迷促醒的作用;龚自珍所论,更揭开了近代思想斗争的序幕;至于太炎先生,就更是以其说直接参加对旧学的冲击了。由此看来,我们虽不能肯定章、龚等人都是直接受到刘因的启发,但刘因"古无经史之分"之论毕竟开了先河,对其意义应给予充分的估价。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一五。
② 《中说·王道》。《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96 册,第526 页。
①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集》卷一。
② 《焚书》。
③ 《文史通义》中《易教》、《经解》等篇。
④ 参见龚自珍,(占史钧沈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三)学史必读全史
刘因对历代史书都很熟悉,且作了系统地论列。从先秦史书《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到"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下至《晋史》、《南史》、《北史》、《隋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一一作出评价(参见第六章)。进而,他对学史的方法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说:学者必读全史,历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但然明白,时以《六经》指要立论其间,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以此为原则,他进而对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论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刘因"学史必读全史"的观点,从方法论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的有三点:一是要全面占有材料,从实际出发。不道听途说,不以偏概全;二是有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之作为评判长短是非的标准;三是不可断章取义。浅尝辄止、急于要名。这些看法,都是比较深刻的。其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推重,更表现了他颇具史学家的眼力。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六。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