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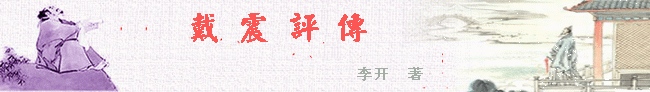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二、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曾经说过:“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按:谓习斋先生,指颜元)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①这里说的《孟子绪言》就是指《孟子字义疏证》。梁启超就戴望的这一著名评论曾说:“子高(戴望字)说戴东原作《孟子绪言》,其论性本自习斋,最为有识。”②戴望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今文经学者,他的身世和颜元颇相象,从其著《颜氏学记》看,又很有些知遇之感。虽时代异隔,仍南北知音,仍是心心相印的。
戴望评述戴震著《疏证》受颜元学说的启发,有无实在的依据,已不得而知,抑或是从身世相象、思想上有联系作出的逻辑推证。梁启超从今文经学角度盛赞戴望的这一评述,显然是认为戴震在思想上与颜元有联系,而戴望首次发现了这一 联系。关于戴震受启发于颜、李有无实证,胡适曾着意寻找其中介,他说:“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 1758. 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氏也许可以从他那边得见程廷祚或颜李的著作。”“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受颜李的影响大概在他三十二岁(1755)入京以后。”①应该说,胡适这种寻求实证的推测尽管仍是逻辑推证,但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从小攻读经书,后来从武进的恽鹤生(字皋闻,常州学派的先驱)那里听到颜李之学,遂写信给李塨,愿拜李为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游至江宁,他屡次登门问学,读颜元《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者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者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②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源③”程廷祚的学问,以颜李之学为为主,参以黄宗羲、顾炎武,故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著书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书订疑》若干卷,《尚书通义》三十卷,等等。对这样一位知名学者,戴震① 《颜氏学记.习斋一》,中华书局1958 年版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37 页。
①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远流出版公司1986 年7 月版18 至19 页。又戴震进京当在1754 年,见本书85至86 页的考证。
② 《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 年版225 页。
③ 同上。
与之结识是可能的。至于程廷祚的族孙程晋芳,出身豪富,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货,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探讨”④。他与戴震友善,深受戴震影响,著《周易知旨》,《礼记集释》等,是扬州学派中的佼佼者,戴震多次旅扬传学,程晋芳介绍他结识程廷祚,也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四库馆开馆后,程晋芳又曾与戴震同供职于四库馆。
程廷祚与李塨相过从,李塨之学是发展了颜元之学的。颜元一生极少出门,交游极少,李塨则常往来京师,广交当时天下名士,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恪敏等都有往还。有一次万在绍兴会馆开讲,题目是“郊社之礼”,开讲前,万说且慢,请李塨先生先讲真正的圣学。颜元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李塨主张交友须令可亲,以广罗人材;颜元主张少读书,李塨认为礼乐诗书非用考据功夫不可,不能废弃书本功夫,故李塨著书很多。颜李之学经李塨书由程廷祚、程晋芳流入戴震之手,也不是不可能的。戴震的有些话与李塨很相象。例如戴震那段著名的论“理”的话与李塨论“理”如出一辙。戴震说:“理者,察之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①而李塨说:“《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见干事,性具于心,命出于天,亦条理之义也。”②“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③“以阴阳之气之流行也,谓之道。以其有条理,谓之理。”④诸种“理”的类别的说法及论“理”的思维逻辑,戴震和李塨是很相象的。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完全说成偶然性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极有可能的是戴震读过李塨的书。又如戴震谴责“以理杀人”,李塨也曾说过:“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高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足,遂好武断。”①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没有程廷祚的媒介,难道戴震就全然不知颜李吗?
早在恽鹤生和李塨交游之际,恽、李书信往还极频繁,恽北上从学李塨南还后去信说:“南旋以存学示人,虽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行。”李塨自喜曰:“颜先生之道南矣。”戴震是遍游京都、淮左名都和江宁的人,一代学人和思想家,不闻其晚近学术大家和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又何需绵庄?再说,即使戴震从未读过颜李的书,也从未听说过颜李,戴震与颜元相近的贫苦身世也会决定他崇尚实学的,戴望能因身世相近而与颜元心声相和,戴震早年的贫苦也决定他会自发萌生求实事功的实学思想。章炳麟曾说:“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②如前所说,戴震从小就过着清苦日子,随父经商,务求实益,长期居于休宁山村,目睹黎民之苦,从小就萌生济苍生的大志,学成以后,著书并无稻梁,仅仅取人④ 《清史列传》卷七二。又《清史稿·文苑列传,程晋芳传》中华书局版44 册13383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理》,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5 页。② 李塨《传注问》,见《颜李丛书》本。
③ 同上。
④ 李塨《周易传注》,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① 李塨《恽氏族谱序》。参见《恕谷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章炳麟《检论·清儒》,见《章氏丛书》,右文刊印社排印本。
面铺中面屑充饥。戴震学术,不论是考释经传注疏,记述成规典制,校勘古籍,钩沉古音义,还是筹算推步勾股之术,无一不求实证,均是以古代文献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实学。求实的生活习性,求实的思维,求实的信念,都会使他在其深层的理性逻辑上促其走到与颜李相悬契的唯物主义认识思路上来,后期《孟子字义疏证》,畅发儒学道本,无非是前期素有的求实精神的逻辑发展,以及后期对学术、对社会更为深刻的实际观察以后的理性反思。章炳麟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①章氏还将颜、戴合称为“颜戴之学”,章氏还探讨颜、戴的渊源说:“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②如此看来,媒介的有无,读过颜、李的书与否,似都无关“颜元、李塨一戴震”的务实思想方法的发展宏旨。侯外庐也曾说过,戴震的“哲学思想和颜元的哲学思想,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有互通之处”③。
李塨虽补充修正和发展师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颜、李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颜、李的一些主要论题,更可看出戴震对颜、李的继承,主要有:倡导新知识论,注重躬行践履,反对静坐读书。颜元的实学强调以尧舜周孔事、物、行为、教育等为贯彻目标,从而采取了复古形式,但同千百年来的训诂笺注、清谈词章和静坐顿悟是对立的。李塨同样讲究知识的实用。他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④ 又说:“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应比,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敝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①彻底批判宋明理学,成为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突起的异军,颜李对理学的批判,比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更彻底,更痛快,时人谓之“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②。除了在知识论上痛批宋儒外,更在性理论上彻底批判宋儒,戴望谓戴震受了颜李的性理论的影响而著《疏证》即指此点。
颜元认为性是人生必备,人性的产生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戴震后来主性、气之说,视人性为元气之分,与颜说颇相象。颜元说:“生之谓性,若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人之生也直等生字解去亦何害。”③又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独自全其生理,方且积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气,以抉宇宙生生之气。”④正因为人生具人性,人性为人形所赋,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故不可能在人的气质之性之外另设一个义理之性,这完全是唯物的认识。戴震后来批判宋儒另设义理之性,与颜元之说也很相象。颜元说:“天之生万物与人也,一理赋之性,一气凝①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② 同①。
③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430 页。
④ 《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见清冯辰编《年谱》引用,清道光丙申年刊本。① 《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89 号。② 王源《居业堂文集·与婿梁仙来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78 号。
③ 颜元《四书正误》卷六。
④ 颜元《习斋记余》卷一《烈香集序》。
之形,故吾养吾性之理,尝备万物之理以调剂之,吾养吾形之气,亦尝借万物之气以宣泄之。”⑤从而坚决反对宋儒的性、理二元说,反对在人性之外再设一个“天命之性”的理来钳制气质之性,他说:“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①此后,李塨又进一步阐明了“理在事中”(已见前)、“气外无理”,坚持和发展了颜元。他说:“即以理代道学,而气外无理??未有阴阳之外,仁义之先,而别有一物为道者;有之,是老庄之说,非周孔之道也。”②颜李的理论,后来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的回响,针对程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戴震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批判(见本书第八章),上述颜李的说法,几乎无不渗透在戴震后期哲学著作中,从思想史的发展看,从颜李到戴震,前后一贯,许多提法如出一辙。戴震和颜元、李塨思想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天然联系。
⑤ 颜元《四书正误》卷四《与何茂才千里书》。
① 颜元《存性编》卷一《驳气质性恶》。见丛书集成初编0672。
② 李塨《中庸传注问》。见《颜李丛书》,1923 年北京四存学会铅印本。三、后期论学和向新理学的转变结识惠栋、惠栋崇古轻宋的导引所引起的反思;读过颜李的逻辑推证,抑或作为一名大学问家和思想家对自己时代的晚近学术和思想的思考,从而输入了颜李大反宋儒的理论信息,成了酝酿新思路的媒触;早年对顾炎武、阎若琼、胡渭、黄宗羲弟黄宗炎等的精心研究,诸哲崇古轻宋的思想倾向,在《河图》、《洛书》等具体问题上诸家对宋儒的不同程度的批判、否定、轻蔑的态度,都曾一次次坚定了戴震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学术信念;江永老师承继朱熹学术,乃至程朱至清初六百多年的知识论传统,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之间的绵延不尽的斗争形成的重视知识价值的主线对戴震早期实学的支配、贯串和滋养,如此等等,都形成了后期戴震重新论学,后期大反宋儒的新理学的确立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今本《戴震集》中有《与某书》,未注明写作日期,从内容上看,应是后期作品。此外,再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古经解钩沉序》,形成一组后期论学的文章。特别是《与某书》,在后期论学中的地位,完全相当于前期论学的三封书信《与是仲明书》、《与姚鼎书》、《与方希原书》。后期论学是前期论学的飞跃,前期不批宋儒,对程朱有所吸收,评其得失中判,后期批判程朱,修正了前期的一些思想,最重要的修正有三条。一是强调闻道,二是全面否定程朱,三是强调新理学的实际作用。还应指出的是,后期戴震仍在从事考据学,如只看到它的新理学,那就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部,更没有兼察前后期之间的关系。或者,只愿看他的考据学,不愿看他的新理学,如朱笥河。也有既看到他的考据学,也看到他的新理学,但认为考据学是学问而无思想,从而由轻视考据而产生某种轻视其新理学的思想,因而不能作出正确评价,胡适等人的看法大致可作如是观。我们的看法是,既要重视其考据学在文化史上的实际贡献,又要重视其新理学的成就,面对前者,作为考据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功夫,又是可以深入剖析其门类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思想,及其进一步抽象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论的。对其新理学思想的阐明,其基础部份也是离不开语言解释学和自然观的。如此看来,后期戴震仍应当是兼有前期的学问家和学术思想家的,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著称于世,这是全面认识和评述后期戴震的一个基点。
强调闻道,这一点在前期论学中也很注重。前期提出的“以词通道”就是强调“闻道”的,在我们作为前期论学著作的《答郑用牧书》中已很强调“闻道”的地位。《与某书》一开头要求对方的也是这种精神,戴震认为,研治古经的本领是多方面的,均要求精深高超,而“闻道”则应是研究者的一种见识和志趣,戴震说:“夫文无古今之异,闻道之君子,其见于言也,皆足以羽翼经传,此存乎识趣者也。”①戴震认为,治经者当综观其行文体格,全面观察,不能光懂得名物度数等的“制义”,让“制义”从经书中游离出来,重要的是要“制义”为治经服务,让“制义”贯于精心研治一经的全过程。他说:“词不纯朴高古亦不贵,此存乎行文之气体格律者也。因题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②这里强调名物度数和研经的结合,实际上是强调名物度数当用于通经通道。至于将治经通道的成果展示出来,很需要“纯朴高古”之词,要有冶铸群经、通观文献的本领,最后才能著成伟词。戴震说他自己是有这种本领的。他说:“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纯翁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也。”①作为文献考释的大家,他的语言表达并不喜欢韩愈,却欣赏顾炎武的貌似干涩的文章。他说:“韩退之氏之言:志于古,必遗乎今。彼所谓古,特文词不类于近今者耳。进而语人以汉儒经师之业,其沈蕴积久,岂古文词比哉!”②由考据学术的需要,戴震力主顾炎武的文章表达,他说:“阎百诗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顾亭林文章较胜。”③特别是考释文章,戴震文字风格宗顾炎武,做成了一篇篇短小精悍,毫不词费的考据学的科学论文。
后期的闻道与前期的闻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呢?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的结合,“学成而民赖以生”④,强调“道”本身的理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贯彻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从而使闻道和闻理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考据学本身能够做到以字(词)通词(辞),也能容纳以词(辞)通道,但由于受其体制的影响,通理义是少量的,全部以考据通理义是有困难的,这样,闻道的方式在后期由考据向冶铸群经,综贯古今,因题成文而转化,甚至突破考据而进入新理学的全面阐述,或者仍是以语言解释为手段而全面阐释之,就将是十分必要的。戴震后期部分地由考据而进入以语言解释为手段求闻理义,实在是闻道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变化以后的逻辑必然。当时,以戴震为旗帜的乾隆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行,也在受了戴震的影响以后强调“闻道”,但大都停留在对古圣贤之道述而不作的层次上,唯有戴震是大炉冶铸,铸成精良,《孟子字义疏证》是其精品,它已不是重复古道,述而不作,而是建立新时代的哲学体系。此外,要论前后期“闻道”的不同,后期排斥宋儒之道是其重要特征。
戴震在对“道”即理,即理义的广泛理解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经闻道通理义的方法,大致说来有:罢黜宋儒,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学理为应用,不仅用于个人修养和心智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用来“措天下于治安”。戴震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帅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② 《戴震集》同上,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6 页至487 页。
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488 页。
④ 《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①这无疑是对“闻道”内容的丰富,也是由闻道而摄取理义的过程。至于对宋儒的批判,无疑成了闻道摄取理义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思维契机。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批判宋儒,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前期论学的主要之点在后期贯彻时都打上了这一新的烙印。例如在本应照办的“以词通道”上,宋儒“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在“十分之见”上,批判程朱才能得此“十分之见”,如此等等。《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实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宋儒以己私见,自称“闻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连古书也没有读懂。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从而使天下深受其咎。这两条,又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有关系的。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①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的纲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其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程朱之学是个“躬行实践”的儒学,这当然是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理学之士的蛊惑,当时的所谓“躬行实践”的说法,实际上是理学家们的虚伪作法,尤其是理学未流,更是表里不一,虚伪透顶,戴震认为,认真理会之,都是由程朱理学本身的理论错误引起的。他说:“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释氏之教亦尔也。”①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颜李学派的王源就指责过这类假道学:“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四达之衢。”梁启超也曾举出清初三位大理学家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的劣迹②。戴震认为,以功利对待理论,往往就会是非不分,而历史上的教训是必须首先分清是非。他说:孟子辟杨、墨,退之辟释、老。当其时,孔、墨并称,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日,是圣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元单途、同时获得的过程。这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中说得也很清楚,《与某书》中在指出宋人“恃胸臆为断”以后,要求读者“平心体会经文”,不要“与后儒竞立说”,真正认识到“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总之,批判宋儒,引起了学术思想上的许多环节的根本变化。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至188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04 页。
③ 同①,188 页。
在强调闻道过程中故训理义二合为一地寻求义理,力主批判宋儒的基础上,戴震强调了他的新理学哲学的人民性和实践性,这正是他的新哲学的全部精华所在,但他的新理学是托干古道的,他把新理学和宋明理学完全对立起来,控诉其“以理杀人”的罪行,这种尖锐激烈的程度,有如颜李学派“开二千年不能汗之口”,又如继黄宗羲《原君》之后的唐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议论。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所不同的是,戴震的此等石破天惊的精辟之言,警世之论,还更带上理论性和学术性。他认为,古圣贤、新理学的理义在于事之中,而宋儒别设一理以制事。他说: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大事。
正是由于程朱“别制一理以制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深层原因,才引起了古学和理学在实行其理的实际过程中的态度的不同。古贤之学,或新理学,能体察民情,体恤民意,宋明理学则是架在百姓头上的刀子,他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
两种理趣,两种态度,实行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戴震说:“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②宋明理学是欺民、”愚民、害民之学,这就是他的结论。
戴震后期论学,修正和补充前期论学的观点,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学术思想家,更应作前后期相衔的考察;而在“闻道”即寻求理义,特别是在批判程、朱,及他的新理学的实践性和人民性的阐述上,标志着戴震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后期作为一名哲学家、思想家,当作如是观。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② 同上。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② 同上。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