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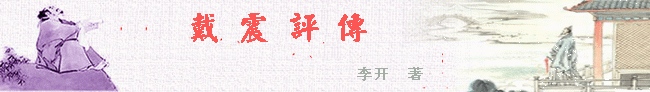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二、理存于欲和对理欲相分的批判
戴震是用语言解释哲学来说明什么是理的,“理”具有语言解释哲学的意义。“理”的解释既是语词释义,也是“理”的概念诠释,而对“理”的意义的开拓,与戴震汲取时代精神,受到徽商经济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撇开后者不谈,戴震关于“理”的哲学解释是揭示理的内涵的,而在揭示内涵时,蕴含和直接体现语言解释哲学的方法,其科学的思路是从客观存在之物出发揭示内涵,可谓一开始就亮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戴震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①这里的理,是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理,它指理则、规律,它存在于自在之物本身。容肇祖曾说:“戴震说的理,以为‘理’不是如程朱所说的‘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他以为‘理’是抽象的,是事物上的法则,是必然的,——即科学上的定律。”②人伦之理何在?戴震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③这就是说,理存在于情。又说:“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④他特别强调指出:“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月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⑤这就是说,理存在于事,存在于人伦日用。又说:“欲,其物;理,其则也。”“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⑥并主张,治理天下,务必注意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①这就是说,理存在于有节制的欲望之中,简言之,理存于欲。在戴震看来,由于万事万物、情性人欲皆源于自然元气和人之血气心知,因而理归根到底存在于阴阳五行之气,存在于禀之自然之气的血气之中,而不在其外,戴震的《疏证》言理的逻辑是个归纳的过程。
戴震正是以他的唯物主义的理则说与宋儒对立起来,并展开对宋儒的批判的。盂坷批判杨、墨,后世又习闻杨、墨、老、庄、释、道之言,思想史上的对垒永远不会完结。韩愈曾说,求观圣人之道,自孟子始。极微妙的是,孟子宣扬“民贵君轻”,称赞上下易位的汤武革命,“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②。故戴震疏证《盂子》字义,以特有的解释学的方式弄清儒道,检核宋儒理学,是有其选择性的,也就是说,戴震是看到了《孟子》中包含的特有的思想成分而选择之,疏证之。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孟子辟杨、墨,韩愈辟佛,戴震批判宋儒,又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由于戴震所处的商业经济繁荣的时代条件,使他辟宋儒的做法打上了早期启蒙思想的烙印。
现在看看戴震是怎样运用理则存于物质,人伦在于情性的唯物主义本体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5 页。
② 容肇祖《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载《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25 年12 月版。③ 同①。
④ 同①,266 页。
⑤ 同①,267 页。
⑥ 同上①,273 页。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6 页。② 《孟子·梁惠王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版42 页。说和道德观来批判宋儒的。宋儒并不一般地否认物的存在,只是以理在超物质之外,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熹说,物有心,犹人有心,理在物心、人心,而心是神明之舍,再说,孟子也曾说:“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即是以多数人认为如此之见为理则,以众人之见为真理。戴震认为,以己见为理,必然造成“负其气,挟其势位”者强词夺理,而那些“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以己见为理,即使其人贤智,没有私心,也会因个人眼界的狭小,“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①。戴震认为,以众人之见,以众人共推的智者之见为理则,也是片面性极大,蔽人之处甚多。戴震认为,说理在人心,“未有不以意见(按:指私见)当之者也。”意思是说,如以为理在人心,那就少不了人人以私见、个人之偏见为真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就是“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②。宋儒因人之嗜欲出于气禀,从而把理游离于气之外。戴震认为,古人言性来源于血气,未言理义为性,但理义同样来源于血气是可以推导而得的。戴震说,耳之于声,口之于味是人性,心之于理义也是人性。而宋儒的目的是要在气禀之外再加一理义之性以超然于元气之外。诚然,戴说将不同质的味觉、嗅觉与听觉、视觉混为一谈,进而又把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与感官能力混为一谈。这是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但都归于气禀,目的是要批驳宋儒在气之外再加一太极之理。本来,孟子讲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不过是个比喻,由于戴震视为同受气禀,同属于性,故认为“非喻言也”。戴氏对理义和嗜欲的关系的看法十分彻底,“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岂止是理义存在于节制之欲,而是理义同于嗜欲,都是人性的功能。这就为展开情性为本的新理学道德哲学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基础:理义和嗜欲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包容存在关系、等同关系,更不用说对待关系了。理欲间有同一性,在戴震看来,归根到底说明“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①。人脑认识事物规则的能力,犹光照见事物的本来面目,“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②。当然,戴震还未从认识论上了解大脑认识规则的抽象过程,以光之烛照事物比喻人的认识能力,说明戴震论人的认识的见解仍然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
宋儒理欲相分,以理欲之界为君子小人之分,说什么“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把理和欲分为二途并予对立起来。戴震认为,人生之基要,在于谋生存活,“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③,不仅要自己活下去,还要让别人也能活下去,从而形成了仁与不仁的基本分野。“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④。戴震认为,只有欲望本身实现时的邪和正的区别,没有理和欲的对立,欲是客观存在的事和物,理是该事物的规则,人人都有谋生的权利,也都有成全他人谋生的义务。己不谋生而让他人谋生,“无是情也”,己谋生而妨碍他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8 页。② 同上,269 页。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2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273 页。
④ 同上,273 页。
人谋生,是为邪,人人都能遂其欲,谋其生,是为正。宋儒也讲谋生的邪正之分,但正如戴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前提是在事物以外还有个制约一切的“理”,故而在谈论邪和正的区别时,“则谓以理应事也”⑤,合乎超验的理是正,不合超验之理的是邪。戴震认为,理与事物,与欲相分,必然与个人私见结合为一,以所谓“理”与私见处事,“是以害事”①。戴震认为,就人类认识的一般过程言,“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②也就是说,一事当前,就会引起大脑的思考,不循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弃事与物而不顾,又如何能获得理?宋儒以“人欲为蔽”,认为“无欲则无蔽,”这一看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有道理的,但极而言之,主张去人欲,就不对了,彻底的“无欲”,情同剥夺人的生存权利。戴震把彻底的“无欲”、“欲之失”叫做私,这和流行的一般“私”的看法是不同的,是道德哲学范畴意义上的“私”。与此同时,他又把“无知”,“知之失”叫做“蔽”。戴震揭示了由事物,由人的欲望而求得理则,以及因“私”和“蔽”不能得理的因果连锁。他说:“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失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实同。”③戴震所说的“以生以养”,正是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去蔽求知,去“私”存欲,因欲求理,这就是戴震的内在逻辑。这中间,既有知识论,也有道德论,既有道德哲学,也有自然哲学,戴震阐明自己的道德哲学时,常常是用综合逻辑方法的。通过深邃的逻辑综合,戴震无疑得到了以下结论:并非君子讲理,小人讲欲;理欲不能相分,更不能分以君子小人之别;理欲相分,只能导入道家和佛教之说。戴震上述的逻辑综合已证明了这一点,宋儒的事实也完全证明这一点,“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①。
宋儒视理在天地、人物、事为之外,所谓“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从而把敬、肆、邪、正都归之为理与欲的区分。戴震认为,实体实事,理在其中。如同他对“理”的语言解释那样,他把“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看作是“理”②。“理”有很高的抽象性,来自于具体事物而回到具体中使用。“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③。这就是客观存在之理,也应当是人心目中的理,“是为心之所固然”,这就是说,主观之理,完全取决于客观之理。理则在天地万物为自然之理,在人伦则为人伦之理。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认为,自然之理存在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人伦之理,则唯物地归之于血气心⑤ 同上,274 页。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4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4 页。② 同上,278 页。
③ 同上,278 页。
知,但有时也说是圣人之理。他说:“天理阴阳之理,犹圣人之圣也。”④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他不是把圣人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而不过犹阴阳自然之气和血气,故而他对圣人的解释极为开明,他说:“圣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⑤可见并不如宋儒所说的那样“理得于天而归于心”,而是得于人而归于人伦日用,圣人之理连同圣人本身皆如此,这是在把圣人降为凡人,破除对圣人的迷信,其意义是何等重要。可谓从道德本体论讲政治哲学中的民主的。这种道德哲学形态的政治民主思想,和黄宗羲从史学谴责君权至上,唐铸万(1630—1704 年)铸论“秦汉以来凡君王皆贼”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采取了哲学形态,不如黄宗羲、唐铸万那样激烈,但如果结合《疏证》全书对“以理杀人”的抨击,这种哲学化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说更为深沉和忧愤。针对宋儒“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指出,即事物求理,理在其中,“理至明显”,如无端廓开“理”字而成“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将“理”装上“物”的光环,从学理上说,将会“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①。宋儒以理为物,且以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理、物二元,并以此为“完全自足”。戴震认为,说“理”是“完全自足”,即绝对圆满的,那只能是老、庄、释教的“真宰”、“真空”,但无论是道家、释教,还是宋儒,一方面讲“理”和至高无上的“真宰”的绝对圆满,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世间的邪恶和愚昧,故而宋儒提出“理为形气所坏”,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复其初”,老氏则由此而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陆九渊、王阳明等主观唯心主义则推本释老,认为从主观精神上全乎圣智仁义,即全乎理。戴震认为陆、王是立足于释教而将儒学引入释教。而程、朱等客观唯心主义者将释、老“真宰”、“真空”转变成超验之“理”,是以释氏之言杂于儒学。针对人世间“污坏天理”的种种情形,宋儒也不得不主张学习,但已不是学以明理,而是“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在戴震看来,程朱理、气二分,将“理”看作绝对圆满,援释入儒,后天的学习也只是找回那失去的超验之“理”,凡此种种,只能引导世人陷入蒙昧主义。作为一名对社会自觉地负有责任的有良心的哲学家,面对较释、老、陆、王唯心论更为精致的程朱理学所宣扬的蒙昧主义,戴震说:“呜呼,吾何敢默而息乎!”①可见是《疏证》不得不作。
程、朱出入于老、释以求道,怎么又冒出个“理”字呢?戴震从宋代理学的内在逻辑上探讨了从“道”到“理”的过程。戴震认为,最初求道于老、释,并无皆弃孔孟之意,仅见其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儒学,特别是子思,孟轲学派的切己体察,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接受的:“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②。但老、释之极致,仅仅是体察“神之本体”,以为如此便足,而程朱后来方知不能把老、释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接受,从而对老、释及其阐释者北宋邵雍指神为人性的做法采取另一种貌似不同的态度,特别是朱熹,“于其(按:指老、释、邵雍)指神为④ 同上,278 页。
⑤ 同上,278 页。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8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社281 页。② 同上,282 页。
道、指神为性者,皆转以言夫理”③。戴震认为,在这场哲学转向中,只有张载的转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大体上抛弃了老、释言性、道即神的说法,转向理在气之阴阳之中的唯物主义。戴震指出:“张子又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斯言也,盖得之矣。”④至于张载所说的神,与老、释的超自然、超阴阳之气的神可不一样。戴氏指出:“张子见于必然之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诚如是言,不以理为别如一物。”①而程朱的理和老、释的神,其实质是一样:“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②关于人伦道德之理,张载没有明确的说法。戴震发展张载的唯物主义,可谓在中国哲学史上破天荒地指出人欲即血气之自然,人欲之节制和正常的满足就是德,就是理,圣人之欲和凡人之欲相同,再一次从道德哲学上破除对圣人的迷信。在人伦之理问题上,戴震揭示老、释、程朱的实质是:老、释见人间邪恶,认为邪恶之根源在凡人的血气自然——欲,纠正之法是静养其心知之自然——性,戴氏指出,此“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③。老、释关于人伦道德致谬误的内在逻辑如此。程朱见人间邪恶,同样认为众人之血气心知之自然——自然之气质,是罪恶根源,纠正的方法是进之于理之必然——性,其内在逻辑是血气之自然和性之“理”二元化,戴震揭示道:“如其说(按:指二程在血气自然之外另增必然之理),是心之为心(按:指血气自然之人的),人也,非天也;性之为性(按:指理之必然的),天也,非人也。以天别于人,实以性为别于人也。人之为人,性之为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始。”④完全以其内在的学理逻辑上捉住了程朱的痛痒之处。至于荀子的性恶论,戴震的剖析是:常人之血气心知之自然——致恶之“不可”存在之物,性;纠正的方法——述以礼义之必然——教。而戴震本人的逻辑是:凡人、圣人无不具备的血气心知自然——欲,正常之欲即理;后天之学——进于血气心知,“使无几微之失”①。他叙述此理欲一元论的内在逻辑时说:“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心知之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②既然理欲一致,理欲共存于血气心知自然,理、欲、血气皆自然,如假设它们共同的更高一级的抽象为“善”,“善”为自然之理,亦当为气血、人性、情欲之理,戴震本体哲学的自然宇宙观“原善”说,道德哲学的理存于欲论,哲学意义上的人性论,是很容易与孟子的“性善论”发生共鸣的。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戴震继承了王夫之。不消说,顾炎武是反对谈“胜与天道”的,王夫之非常重视理欲之辨,也是从读《孟子》中悟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主张理欲统一,理在欲中,“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③ 同上,283 页。
④ 同上,283 页。
① 《盂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84 页。② 同上,284 页。
③ 同上,285 页。
④ 同上,285 至286 页。
①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86 页。② 同上,286 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孟子》。
离欲而别有理也”④但王夫之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理欲对立,如仍说“私欲净尽,则天理流行”⑤王夫之晚年隐居后,开始向佛教让步⑥。戴震的“理存于欲”和对释教的批判,后期是贯始终的。
对戴震唯物主义的“理存于欲”论,服膺戴震语言文字学的凌廷堪(约1755—1809 年)表示很不理解。他在《戴东原事略状》中认为戴震言理是无所谓是和非的“虚理”,没有什么价值。只有稍后的黄式三(1788—1862)著《申戴氏气说》、《申戴氏性说》、《申戴氏理》①三篇,较系统地阐述了戴震的理则说。值得注意的是黄氏把戴震和明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罗钦顺(1465—1547)联系在一起,不失为识戴之见。黄说:“朱子《答柯国材书》曰: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罗整庵(按:钦顺号)取此二说,以明理气之不可分。罗氏又曰: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凡此,与戴氏说同乎,稍不同乎?夫后儒之疑戴骂戴者,为其说之驳程未耳!”②④ 同上。
⑤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⑥ 王夫之《老子衍·序》。
① 黄式三的三篇“申戴”之作均见其文集《傲居集》。
② 黄式三《傲居集·申戴氏理说》。见清王灏辑《几辅丛书》光绪五年刊本。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