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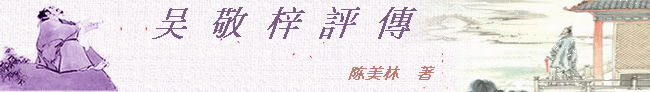
|
六 诗文刊刻
传主自去年春季游罢苏南溧水、高淳一带归来之后,虽然情绪还有些反复,但他仍然坚持在秦淮水亭中从事《儒林外史》的创作。转眼之间暑去寒来,又过了一年。
乾隆四年(1739 年),吴敬梓已步入三十九岁,到次年即乾隆五年(1740年)已是不惑之年了。回顾平生,他能"不惑"么?在三十九岁生日时,他作了一首《内家娇》词:行年三十九,悬孤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垅;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娀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传主吴敬梓在父忧母难的诞生之日,自然要想到双亲仍然寂寞地埋葬在故乡,垅头荒草没胫,乏人祭扫。而自己早年功名颇不得意,屡困场屋,近年的鸿博之荐,也因多种原因未赴廷试,如今老大年华,冉冉而至,既然仕进无门,他就不再希冀从所谓的"抡才大典"中谋求功名富贵,对朝廷也就不再存有什么眷恋之情。并且,传主也进一步地觉悟到既往岁月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走错了路。今后的道路何在呢?他也初步地意识到应该象屈原那样,远游四方以寻觅知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过于看重由科举求得仕宦的士绅、官员,而须从另外一些人中寻求知己,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传主吴敬梓确已能有所"不惑",根据近四十年来的生活经验、现实教训,他终于明白了今后的道路,尽管还不那么明确,然而与过去告别的决心确已初步显示出来,并且填词明志。这是吴敬梓生活史上的一大进步。
传主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且在生活中努力实现。在这一两年内,除了一些亲友的生离死别引起敏轩一阵阵的感唱叹息以外,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无过于谋求赀助以刊刻自己的诗文集了。
乾隆四年(1739 年)秋,吴敬梓再次过江而北,寄寓在真州僧舍中。自从上年春季在凭吊石臼湖邢孟贞旧居时,传主想起王士禛拜托李斯拴"检点"邢昉"遗书"的"风流"故事以后,就曾不断地虑及自己的诗文如何不致散扶。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刊刻问世。因而这年秋季,他就来到真州,为自己的文集能付诸梨枣而筹划一切。在《真州客舍》一诗中就明白他说出此行目的:七年羁建邺,两度客真州。细雨僧庐晚,寒花江岸秋。奇文同刻楮,阅世少安辀。秉烛更阑坐,飘蓬愧素侯。
自雍正十一年(1733 年)二月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到此年前后己有七载,虽然多次出游,但终归回寓建邺。真州之行,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秋冬之际为第一次,乾隆元年(1736 年)秋季为第二次。这首五律的首联就反映了这一经历。从"奇文同刻楮"诗句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实在无力独自刊刻自己的"奇文",因而才远行到离开南京二百余里的真州向至交故友筹集资金"同刻"。但飘泊到此地,天寒日暮,细雨寒花,独居僧舍,秉烛夜坐,又不禁念及告人求助之难,惭愧之情油然而生。诗中的"素侯",即"素封"的意思,指那些虽无官爵封邑但却拥有资财的富豪之家,《史记·货殖列传》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正义》:古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敏轩此诗中的"素封"很可能是指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回到真州的杨凯,至少也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真州的富有赀财的士绅。
吴敬梓曾经写了一首五古《赠杨督府江亭》,诗云:狻猊产西域,本非百兽伦。一朝同率舞,图画高麒麟。三苗昔梗化,戈鋋扰边垠。桓桓杨督府,钲鼓靖烟尘;功成身既退,投老归江滨。廉颇犹健饭,羊祜常角巾,明月张乐席,晴日坐花裀。丹心依天桴,白发感萧晨。方今履泰交,礼乐重敷陈。天子闻鼓鼙,应思将帅臣。
全诗叙述了杨凯前半生的事功,描写了杨凯此际失意时的生活情绪。诗的最后一联,也表现了吴敬梓对他的恭维。根据汪中《提督杨凯传》(《迷学·别录》)、《仪征县志·杨凯传》等材料,凯字起,号江亭,仪征人。康熙时以武进士为乾清门侍卫,后出补为湖广督标中军守备。不久又调职镇筸前营游击。当地苗民作乱,杨凯用奇兵攻占野牛塘、卡洞寨等苗民寨落,以功升辰州副将。雍正初兼任桑植副将,雍正六年(1728 年)被迈柱弹劾去职,但不久又被起用,曾任镇筸镇总兵。乾隆初年,迁任湖广提督。后被史贻直弹劾,再次被革职。此后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至高邮被召见,才以总兵再次起用,不久任命为河南河北镇总兵。但又被鄂容安奏劾,第三次被革职。
杨凯在乾隆二年(1737 年)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后,回到故乡仪征家居。传主吴敬梓这次来游仪征时去拜访过他,还写了上面所引的五古赠送给他。诗的最后一联,虽不免有些恭维,但也为吴敬梓所言中,后来杨凯确被起用,已如上述。杨凯虽然是武进士进入仕途,但幼时颇能作文,受到塾师的称赞。侍卫乾清门时,曾随玄烨从幸汤山,赋诗颇得康熙好评,因而命他与汪灏、陈彭年等人在武英殿编纂《物类辑古略》。又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所记,杨凯还曾被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等人同校书史。袁枚在杨凯的府第中就见大厅上悬有一联:"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这副楹联恰切地反映了这位能文善武的杨凯平生。当他被革职归来以后,角巾私第,与文士诗酒唱酬也就成为他的赋闲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吴敬梓就正在这段时间内与他往还比较密切。
传主此次来真州作客,恰恰遇上绵绵不断的秋雨。正当旅怀孤寂、百无聊赖之际,杨凯却邀请他去舍中饮酒赏菊,吟诗论文,借此正可排遣。吴敬梓所写《雨夜杨江亭斋中看菊》一诗就反映了他们两人交往的情景:秋雨羁慈室,惊传折筒呼。黄花依玉箔,翠叶映琼苏。爱客欣投分,论文恕鄙儒。不因逢胜赏,谁解旅怀孤。
杨凯此时无官无职,赋闲在家,难得遇上象吴敬梓这样的文入,有暇听他自叙一己的汗马功劳、生平际遇,至于被革职的原因,当也曾愤愤不平地向吴敬梓说起。杨凯大战野牛塘的"战功",特别是在桑植副将任上与同知铁显祖的矛盾,他都曾仔仔细细说与传主听。胤禛在雍正六年(1728)四月的上谕中就斥责了他和铁显祖的"文武不和":桑植土民,新近改土为流,文武官弁应当加意抚绥,和衷共济,使苗民得所,慰其向化之心。今据迈柱奏称:"副将杨凯,不能严束兵丁,种种忧累。"杨凯又复禀称:"同知铁显祖私派银两,纵役讹诈"等语。似此抚绥无术,文武不和,断难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杨凯、铁显祖着俱行解任,将杨凯纵兵扰民及铁显祖私派强占等情,俱交与迈柱一一确审定拟具奏。杨凯、铁显祖俱系傅敏保举委用之员,今被参劾,着将傅敏交都察院察议具奏,钦此。
--见同治十二年续修《永顺府志》卷之首杨凯这些经历,传主必是从他亲自讲述中得知详情,回到南京以后,曾经根据杨凯这段历史加以改造,写进《儒林外史》中去,成为汤镇台大战野羊塘以及与镇远府雷太守文武不睦等艺术情节。
吴敬梓不断应酬杨凯,原是对他有所希求的。但杨江亭这位目令虽已居乡但却十分富有的官绅,却把传主当作清客对待,只是偶或"呼"他前来闲谈闲谈,对吴敬梓并没有实际的接济,更少主动关心这位落魄文士的疾苦。吴敬梓一直耐着性子与他周旋,总希望这位曾为朝廷大员的富绅能自愿地资助他一些生活盘缠和刊刻文集的资金,然而杨凯却始终不提及此事。直到传主在寄寓的僧舍中遇上"翻盆三日不复止,慧门丈室苔斒斓;寒花幽草俱飘没,惟见阶下水潺湲"的暴雨之后,想念起仍在秦淮水亭中嗷嗷待哺的妻子儿女,他不得不老着脸决心"明晨冲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雨》),向这位官绅开口求助盘缠,至于刻印文集的赀财,当然更是指望不着这位前湖广提督大人了。
幸亏吴敬梓并非初次来真州,在真州也并非只认识杨江亭一人。他还有不少诗朋文友,知音至交,如吴芗林、方嶟、江昱等人,其中固然有贫寒之土,但也不乏小康之家。
吴芗林,名廷,号嘉树林边吟客,仪征人(见阮元《广陵诗事》卷十)。吴敬梓在真州期间,曾填词《水龙吟》一首吟咏自燃铛,并题明此乃为芗林所作:半升铛里乾坤,问谁巧制同丁缓。香浓圣水,光莹伏火,淡烟徐转。尽日回廊,连宵寒雨,一模常满。羡奚奴去后,几番沸了,浑不用、挥纨扇。
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花阴径窄,兰舟波净,相携游遍。小病初愈,故人重到,乳花浮盏。待餐来温饼,朱衣拭取,验何郎面。
显然可见,吴敬梓此次来游真州之前,曾经小病一场,此病并非新疾,而是旧病,也就是如同司马相如所患的消渴病(即糖尿病)。传主罹此疾虽然累经岁月,迁延日久,但却不能戒酒。此次来游真州,重逢故友,无论在长廊中消磨终日,在书斋中联床夜话,还是放舟湖中,探幽花径,更是非酒不可。传主吴敬梓的任性直到这一地步仍然未能收敛,他绝不肯约束自己,即使在生活习性方面也如此。
与吴廷同为吴敬梓至友的还有方嶟。方嶟,字谦山,一字可村,雍正十年(1732 年)"翰林院待诏",家居时勇义急公,多行善事,因此见重于知县李鹏举(见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九、卷三十八)。谦山极擅于诗,著有《停云集》。他还常与吴敬梓另一好友团界等人相互唱和,刻有《真州倡和集》二卷行世《见《广陵诗事》卷七)。当时原籍安徽寄寓扬州、尔后改籍真州的黄裕,曾将已逝友人的诗作辑录为《黄垆集》,其中就收有方嶟的诗作。黄裕,字北垞,交游极广,工诗,有《白沙江上集》、《金竹居诗存》,后死于真州,由汪晓岩为之收(参见《广陵诗事》卷十、《仪征县志》卷三十九、光绪《江都续志》卷二十五、《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方嶟也象黄裕那样重视友人的作品,不过,黄裕是辑录已故友人之作,而方嶟却资助健在的友朋刊刻作品,吴敬梓"有韵之文"得以刊刻问世,实有赖于方嶟的资助。方嶟此举颇得时人的称美,吴敬梓在南京结识的友人诗人黄河,原也准备为传主诗文集的刊刻筹集赀财,但尚未及付诸实施,而方嶟已先成此事。黄河知晓以后,对方嶟的古道热肠大加称赞,说:"??余方谋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轩薄游真州,可村先生爱为同调,遽捐囊中金,先我成此盛举,古人哉!是皆可传也。"(《文木山房集序》)
方嶟刊刻的这部《文木山房集》,大都是吴敬梓四十岁前的作品,而且权限于诗、词、赋等"有韵之文",其实是不足以反映传主创作的全貌的,甚至连四十岁前的无韵之文也一篇未曾收入。但也幸赖方嶟将它刊刻出来,才使得吴敏轩的一些诗、词、赋流传至今,不但可让我们阅读欣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巨著的作者的家世、生平、思想等情况,提供了无以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方■\嶟还为这部《文木山房集》写了一篇短序:全椒吴侍读公以顺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进士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诗古文辞,与新城王阮亭先生齐名,学者翕然宗师之。嶟之先人,与吴氏称世讲好者近百年矣。侍读之曾孙敏轩,流寓江宁。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今将薄游四方,余遂捐箧中金,梓其有韵之文数十纸,以质之当代诸贤。窃叹全椒吴氏,百年以来称极盛,今虽稍逊于前,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而敏轩之才名,尤其最著者也。余梓其所著。匪独爱其与余为同调,将与天下共之焉。仪征方嶟。
这篇短序,在论及传主诗词赋的价值时仅说"力追汉唐",而没有多加评论。倒是提供了一些有关传主的家世和本人际遇的情况。侍读,是指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考中探花的吴国对,因为在传主吴敬梓的先人中,吴国对的功名最高,所以序文中特表而出之,这是旧时作序常有的习惯,带有恭维的意味。李文贞公,是指康熙时理学名臣李光地。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为吴国对康熙五年(1666 年)主持福建乡试时所考取的举人,康熙十二年(1673 年)成进士。李光地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任顺天学政时,因母死应回乡守制,但玄烨却不准他回乡,令其在位守制,一时舆论大哗,御史沈恺曾、杨敬儒、给事中彭鹏等人交章论劾,认为李光地贪位忘亲。这是当时朝政中的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李光地的事迹,显然为其座师吴国对后人吴敬梓所知晓,《儒林外史》中也曾描写荀玫谋求"夺情"。李光地自幼"力学慕古",但因玄烨倡导程朱,"潜心理学、旁阐六艺",他也就改治程朱之学,因此颇得人主欢心。"《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玄烨)皆命光地校理"(《清史稿·李光地传》)。当他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时,玄烨不但派恒亲王允祺前往奠醊,还赐金千两,谥以文贞。这年吴敬梓十八岁。序中说的王阮亭,是指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十八岁即"举于乡",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与吴国对为同榜进士(此据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卷八;《清史稿·王士禛传》云"顺治十二年,成进士",误),历任扬州推官、礼部主事、刑部尚书等职。王渔洋极擅于诗,为清初诗坛一大领袖,"姿禀既高,学问极博",所为诗"独以神韵为宗",创神韵之说,"主持风雅数十年","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在他死后,乾隆在一次与沈德潜研论诗歌时,曾评说渔洋"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清史稿·王士禛传》)。王士禛诗多抒写个人情怀,诗风苍劲,尤工七绝,并擅于词,著述极丰。方嶟说吴国对所作的"诗古文辞"与他"齐名".未免过于恭维和抬高了吴国对的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不过,这是旧时文人为人写序时的通病,不必苛求;但也不能以此作为评价吴国对作品的唯一准绳。方嶟在序中还说自己与传主有世谊,累代交好长达百年,因而知悉全椒吴氏在近百年的极盛状况,而对于全椒吴氏近时的衰败,方嶟在序中也流露了十分惋惜的情绪。不过,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全椒吴氏功名、家财、声势已大不如前,但"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在安徽、江苏一带仍有相当影响,被认为如同王导、谢安那样的大族,有王僧虔那样的门风。乌衣,指南京的乌衣巷,为六朝时望族王氏、谢氏所居之所,由此,乌衣、王谢均成为高门望族的代称。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也曾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马粪,指南京的马粪里,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及其子王志居住此处,僧虔为王羲之四世族孙,喜文史,善音律,工书法,门风宽恕淳厚,《梁书·王志传》云:(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善巷,??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
马粪实为马蕃之讹。方嶟在序中所说的这段话也并非全属恭维,吴敏轩的表兄金两铭在为传主三十初度时作的诗中就说他"乌衣门第俱依旧",只不过目今"只见阮氏判北南"已经衰落而已。传主本人在《移家赋》中也曾自豪他说"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但在《移家赋》的小序中却不无感慨他说道:"乌衣巷口,燕子飘零",败落之叹,溢于言表。但直到垂暮之年,吴敬梓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乌衣、马粪门第,曾写下《乌衣巷》诗,诗前并有小序,序云:东晋时,乌衣、马粪皆王、谢所居。乌衣巷在城南,有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久倾圮,马光祖撤而新之,堂后建亭馆。
图中所绘浮图兰若,则白塔寺也。寺有唐元奘(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寺在乌衣巷,昔人诗又以朱雀桥对,此谓巷与桥近,则地傍南郊。其浮屠金碧,亦可仿佛长于寺景象。
小序中所说以朱雀桥对乌衣巷的就是前引的刘禹锡诗。吴敏轩自己写的这首诗云:城南送夕晖,春风燕子飞。言寻王谢宅,闾井生光辉。牛心金拌贮,麈尾玉屑霏。广厦久已倾,人往流风微。惟馀旧兰若,茶板出荆扉。
流露了类似"江山依旧"而"面目全非"的感伤情绪,自然也映射出自身家世衰落的无限惋惜和悲愁。不过传主尽管一再感叹家道中落、身世飘零,但并没有全然消沉下去,以致一蹶不振。中年以后,他的功名富贵观念已逐渐淡薄,而是专心致志地去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嶟的序中也反映出他这种追求和努力,方序说他"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这表明传主吴敬梓仕宦不成,步入中年以后就转入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途。这部辑录了吴敏轩四十岁前所创作的有韵之文的《文木山房集》,除了方嶟作序以外,还有雍正时先后任江宁训导、知县的上海岁贡唐时琳写的序。在序中,唐时琳对吴敬梓仕途坎坷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慰藉。对传主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序文说:??虽然,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吾子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又奚让乎历金门、上玉堂者哉!
且士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当代巨公大儒,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
从唐序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当时吴敏轩不仅写有许多属于文学领域的"有韵之文",而且还撰有不少属于学术领域的"研究六籍之文",可惜在现存的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中只保存了前者,后者则没有片言只语留存。江西会昌人、举人出身的江宁知县吴湘皋,也为《文木山房集》写有序文,吴序说传主"承家世文物声华烜赫之后。风流酝酿,力洗纨绮习气"。这些记叙,说明进入中年以后,敏轩与早年那种"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的"跳荡纨绔习"(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生活全然决裂,而与其子吴烺"相与唱和",过着著述生涯,如同吴湘皋序中所说的那样,"父子相师友,名于当世"。
传主吴敬梓的至交好友程廷祚、黄河、李本宣、沈宗淳等人都为《文木山房集》写了序言。程廷祚序中颇为吴敬梓未能被世用而感到惋惜,说:"以敏轩之才,必见用于世,而山水之间,不能不与余以离群之感,为可踧踖也。"黄河序中则说他以能与敏轩"晨夕唱酬"为"至乐"。李本宣序中则说敬梓创作态度严肃,决不轻率下笔,而其所作"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苟无关系者不作焉,庶几步趋乎古人"。自称"南国羁人、西湖速客"的沈宗淳,则专门为传主所填的词写序,称赞"吴子敏轩,夙擅文雄,尤工骈体。悦心研虑,久称词苑之宗:逸致闲情,复有诗余之癖"。这些序言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传主吴敬梓的生活片断、思想面貌和创作情况,极有文献价值。总之,也幸亏传主在友人资助之下刊刻了这部《文木山房集》,方才使他除了为当时人所轻视的稗说《儒林外史》以外,尚有诗、词、赋作品传世。这里倒不妨借用唐时琳序中的话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文木山房集》的刊刻,是吴敬梓此次真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此外在真州还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从母之子",即姨母之子。传主此次出游真州是借寓在寺院中的。该院中有一位和尚,在与传主攀谈中听到全椒乡音,十分高兴。互道姓名后,吴敬梓发现这位姓萧的和尚,原来是他的"从母之子",两人因而分外亲近,相互诉说生平。这位萧姓和尚的不幸身世,引起了敏轩极大的感喟,转而联想到自身的际遇,不禁悲从中来,写下《赠真州僧宏明》一诗: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终天,患难从兹始。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今年游真州,兰若寄行李。中有一比丘,闻我跫然喜。坐久道姓名,知为从母子。家贫遭飘荡,耶娘相继死。伯兄去东粤,存殁不堪拟。仲兄远佣书,遥遥隔江水。弱妹适异县,寡宿无依倚。
兄弟余两人,流落江之涘。髡缁入空门,此生长已矣。哽咽语夜阑,寒风裂窗纸。
诗的前半,是吴敏轩自述身世。所说的"弱冠父终天"一句则须要略加铨释,方能明白吴敬梓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弱冠"一词,据《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所以就以弱冠指代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但并不严格非指代二十整岁不可。《后汉书·胡广传》:"终、贾扬名,亦在弱冠。"终军年十八请缨,贾谊年十八为博士,均未满二十岁,可见此处以弱冠指代十八岁。吴敏轩也是如此,他在三十岁时写的《减字木兰花》同中说:"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这就反映出他的入学年龄也在十八岁。而吴敬梓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写道:"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这十分清楚他说明吴敬梓在服侍父亲患病时去参加考试的,试后不久生父就已去世。接着,传来了入学的喜讯。由此可见传主的生父确实是在吴敬梓十八岁时病死的。传主吴敬梓在自叙生平际遇之后,比丘宏明也诉说了自己令人心碎的身世,《赠真州僧宏明》诗的后半就细致地叙写了他的不幸:家境贫困,父母双亡:长兄远走他乡,生死不明;次兄被人雇用,在大江那边("佣书",意为受人雇用,《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妹又嫁到异乡,守寡无依。这样的不幸,使得宏明终于感到生涯的无限苦恼,终于剃度入了空门。传主吴敬梓与宏明两人在寒风凛冽、夜深人静的寺院中促膝深谈,每当诉说到悲痛之处,相互抽泣,不能自己。传主自忖:比起宏明的遭遇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从宏明的不幸遭遇中,传主吴敬梓对于自己世家大族两级分化的现实情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赴真州途中,吴敬梓还曾与故交江昱再度相遇。乾隆元年(1736 年)秋,传主来游真州时就从友人团昇处见到江昱的书信和新作,他曾经"倚声奉答"了一首《高阳台》。这次来游真州,他和江昱晤面叙谈,当然极为高兴。可是为时不久,江昱就因病先于敬梓离开了真州返回故乡。江昱与吴敬梓的友情极深,是传主"真州老友"中极为重要的一位。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据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可知,江昱始祖汝刚为宋进士,曾官歙州,遂安家于此。直到明末江昱的六世祖应全方迁来扬州,从此入籍江都。他的曾祖、祖、父三辈皆未进入仕途。江昱兄弟多人,昱排行第七,与排行第九的江恂为同母所出,被称为"广陵二江"。江昱仕途也不得意,二十八岁始入学为秀才。乾隆鸿博之试,曾有人准备荐举他应试,他却力辞。不过,江昱虽然是一个老秀才,但却嗜学安贫,不改其乐。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小传说江昱"自中岁罢科举业,一意汲古"。江宾谷并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功名虽无,但却善于安排生活,处理琐事,家庭生活十分和睦。他的同母弟江恂以拔贡远赴湖南任知县,他曾扶持母亲杨太宜人去江恂官署中奉养。在江恂署中,他从不过问公事,但对江都老家的生计却刻意谋划,曾寄书家人。要他们在山庄中遍栽树木,说"老去菟裘身后冢,他年都要此中来"(《广陵诗事》卷八)。江昱为人,据蒋士铨所记,生性刚卞,好面折人过,但与人结交淳真厚道。江昱和他的夫人十分和睦,极得琴瑟之欢。原配陈珮,才情清丽,夫唱妇和,著有《闺房集》,不幸婚后四年就病逝。江昱又续娶郭氏。郭氏虽无才情,但为人贤淑,凡江昱友人来访,她能脱簪典衣,热情招待,毫无怨色。而江昱又极喜交游,他与传主的友人团异为至交,与吴敬梓另一至友程廷柞也相识,还与程廷祚在一起讨论学问,尽管两人学术见解并不全然相同。江昱还与为吴敬梓写有《文木先生传》的程晋芳有交往,程晋芳《勉行堂诗集》中就有《寄江松泉表丈》一诗,从这首诗可以知道江昱曾在乾隆十七年王申(1752年)到过南京,与程晋芳同游六朝故都,"维君与我贪寻诗,六朝遗迹几搜访"。江昱与吴敬梓另一诗友李葂也常在一起游览赋诗(见《扬州画舫录》卷十三)。他与袁枚也有交往,由于江昱热衷于研治经学,被随园视为"经痴"。江昱不但自己喜交游,还教导子侄要多见名人。据《随园诗话》卷十三所记,袁枚每次去江都,他都要其晚辈前往拜见,并且说:"余少时得见前辈某某,至今夸说于人。汝等不可与随园先生当面错过。"江昱还与郑板桥有交往,在《板桥诗钞》"范县作"中,还有诗写到江昱:《江七姜七(名昱,名文载)》扬州江七无书名,予独爱其神骨清;欧阳体质褚性情,藐姑冰雪光莹莹。如皋姜七无画名,予独爱其坚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如闻叹息微微声。二子才思原纵横,二子学术原峥嵘。天南万里诸髦英,俯首听命无衡争。板桥道人孤异行,昌羊别嗜颠倒倾。独椎书画众目瞠,寻诸至理还平平。庙堂若荐牺刚骍,二子应列丹刻楹。
大章《萧韵》《咸池》鸣,景王无射休噌吰。即今别调吹竽笙,世间破裂琵琶筝。我来山左尘沙并,春风夜雨思乔莺。穷达遇合何足营,望君刻苦孤迈征。江书姜画悬臬。枨,欧干卞壁湘秋蘅。或予谬鉴双目盲,请呼老秃嗤残伧。
对江昱的"才思"和"学术",郑板桥极其推崇。象这样一个广交朋友的文土,自然也会成为传主吴敬梓的至交了。
江昱学问甚好,也极擅吟诗填词,有《梅鹤词》四卷,《松泉诗集》六卷。此外,他还有《州渔篴谱疏注》、《草窗集外词疏证》、《山中白云词疏证》等著述。江昱除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以外,还精通小学六书,著有《韵岐》四卷。在经籍中,江昱最擅治《书》,有《尚书私学》四卷,他的儿子江德封、江德坚曾为之校刊行世,传主还为它写有序言。至于《潇湘听雨录》八卷,则记录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见闻,诸如山川、金石,都一一加以精心地考订、评骘,特别对古碑,不但尽心搜寻于穷岩绝谷、废寺破冢、颓垣败壁之间,而且还根经据史,订其真伪,颇为精详(参见蒋士铨《江松泉传》、《清史列传·江昱传》、《仪征县志》卷三十六及四十五、赵青黎《潇湘听雨录序》等)。这样的一位饱学之士与传主唱和谈学,对敏轩学问的长进当大有裨益。两人交往又极其相投,此次真州聚首,虽然为时不久,但友情从此越发加深。吴敬梓即将返回南京的前夕,还写下《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广漠风多寒气凝,布帆霜雪照秋灯。从今只可凭双鲤,问讯相如病茂陵。
长云断岸尽相思,衰柳何堪绾别离。楚鼓数声村落晚,扁舟重遇佛貍祠。
前一首作者自注说"宾谷以秋日抱病归",可知宾谷在敬梓离开真州之前,已因病先行回到江都去了,从此以后只能凭书信来往互通消息。在后一首中,吴敏轩极为深情地回忆起这次重行聚首的情景:地点是在佛貍祠附近,时间在秋季傍晚。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小名佛貍,他率兵击败宋文帝部队以后,统帅军兵直追至六合东南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官,后来就改为佛貍祠。瓜步是南京去真州的必经之地,传主是在赴真州途中经过瓜步时遇到宾谷的。而今独自返回金陵,只见一派天寒地冻景象,风打布帆,桅灯高悬,江面寒气逼人,更加深了敏轩旅况的孤寂愁思和对故人病情的惦念。
回到秦淮水亭,转眼就是春节。过了新年已是乾隆五年(1740 年),传主吴敬梓整整四十岁了。自春至夏,除了与知朋旧友诗酒唱酬之外,依然过着著述生涯。这年夏季四、五月间,他曾出游扬州,但停留不久旋即离开。因为他去投奔的卢见曾获谴戍台,失去了依靠。在送别卢见曾以后,他转道回到故乡全椒去了。
在全椒故乡,传主的族兄吴檠有半园,位在城西南河畔,吴敬梓返乡以后,与他的亲朋旧友金榘、章晴川等人逐日在半园中相聚。后来金榘到了扬州还回忆起这次相聚的情景,写了一首长诗《寄怀吴半园外弟》寄给吴檠(见《泰然斋集》卷四)。这首诗作于乾隆六年(1741 年),据金榘之子金兆燕《告广文公文》中说,金榘在"辛酉、王戌、癸亥客扬州三年"(《棕亭古文钞》卷十),正是乾隆六、七、八年。而金榘在这首诗中有"东来广陵三月余",可见此诗作于乾隆六年。诗中还有"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屈指于今方匝岁,高斋雅集难重约"。半是回忆昔日欢聚、半是惋惜今日难会的诗句,也正可见他们与敏轩相聚于全椒半园,确实是在乾隆五年(1740 年)。
在这首诗中,金榘回忆他们去年相聚的情境,说"二三同人日过从,科跣箕踞互长啸。或斗采戏或手谈,或书赫蹏发墨妙"。所谓的二、三同人,主要就是指吴檠、吴敬梓、章晴川和金榘本人。他们一旦相聚就除冠脱靴,不拘形节。科,即科头,结发不戴冠。《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跣,赤脚,《书·说命上》:"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箕踞,伸足而坐,《淮南子·齐俗》:"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诗中说他们站也没有站相,坐也没有坐相。长啸,《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嗜酒能啸",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这些故事,传主吴敏轩和他的那些朋友都是十分熟悉的。在半园相聚的这几个朋友,在当时都是际遇不佳的读书人,他们效法历史上这些不拘礼节的文人高士的行为,也是不足为怪的。敏轩在诗词中就曾一再表示这种意愿,如《买陂塘》词中说:"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斗采戏,就是下围棋,或者在一幅幅的薄纸上吟诗作文。诗中所谓的"赫蹏"就是指薄纸,《汉书·外戚传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蹏即蹄。金榘诗中写到主人吴檠的表现是"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而主人族弟吴敬梓的狂放之态,是在座中最为突出的,金榘诗中这样写道:"君家惠连尤不羁,酒酣耳热每狂叫。尽教座上多号呶,那顾闺中有呵谯。"惠连就是指的传主。他们每常聚会时,痛饮老酒耳根发热之后,就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而带头发表种种议论的常常就是吴敬梓。他们在客厅上欢聚,喧哗之声直闹得住在后院中的吴檠家属也不得清静,有时不得不到前边来说几句,但他们置若罔闻,仍然兴致勃勃地高谈不已。这样的聚会,使得象金榘这样落拓的穷学究,也一扫黯淡的心情,得到片时的欢娱,以致经年之后回想起这次聚会,仍然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流露出难以再聚的深深惋惜。确实,传主吴敬梓这位连襟兼表兄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在二十余岁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了近三十年的举人,始终未被录取,不得不飘泊各处,坐馆谋生,最后以廪贡资格去任休宁县学训导(嘉庆《休宁县志》卷七)。但他仍然不甘心,不愿终老于县学任上,在五十四岁时写的《生日自叹》诗中,一面诉说往昔令人伤心的失败,"年年打,未饮心先醉。马上新郎君,向余鸣得意";一面又表示"明年又文战,据鞍拟再试"的决心。当时也有亲知好友劝慰他说:"广文亦官人,升斗足生计。"但他却说:"那知我心伤,有如利刃。"(《泰然斋集》卷一)金榘漫长的"文战"经历,他的失败的痛苦和懊恨,他的追求的决心和执着,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必然成为相互"号呶"的重要内容。谁能说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创造的许多栩栩如生的士子形象身上,没有金榘的投影呢?这种狂放不羁、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倾诉不平的友朋欢会,对传主当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就在这次返回故乡滁州所属全椒时,传主的胞姊金氏病死了,甚至有可能,正是由于传主胞姊患病,吴敬梓才转道回乡探视的。对于她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曾经写诗哭悼,可惜此诗已经散佚,仅在他的友人王又曾为《文木山房集》所题的十首绝句的第九首中留有线索,又曾诗云:"试诵中年诗《哭姊》,教人珍重紫荆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诗集后》)。王又曾诗中所说的紫荆图,是借用田真的故事,其事见《续齐谐记·紫荆树》: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
从王又曾的诗意看来,传主吴敏轩与其姊同胞感情极其深厚,因而对她的不幸病逝,非常悲痛,还特地请他的至交程廷祚为其姊写了一篇墓志铭: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国对。宫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
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绍曾字榖似,早慧,能文章,有名于时,而夭。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姑不逮事。夫死时舅年老,哭子得沈疴;以一寡妇人代男子职,奉养丧葬,必备礼。而家道益窘,从姑从母之贤者,怜而周之,仅以存活。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绍曾十有九载。综孺人生平,于世间守节妇,最为坎??。嗣子为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日:"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铭日:"子幼而殇,夫才而夭;块然处室,神瘁形槁。胡茕茕以至斯,苟无拂于我志,而其又何之!"--《金孺人墓志铭》,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八这篇铭文虽然短短二百七十余字,但却是研究吴敬梓身世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程廷祚是根据传主亲自为其姊所作的小传而写成这篇墓志铭的。从铭文中知道金氏原为吴雯延之女,出嗣给吴霖起。因为此铭是为金氏而作,当然要交代金氏的直系亲属关系;她出嗣给人,又立他人之子为鼐作嗣子。其中虽然未交代传主吴敬梓的出嗣关系,但这是因为吴敬梓虽为金氏胞弟,但并非直系亲属,自然不必在这篇为金氏作的铭文中特他说明。不过,从王又曾诗中所用"紫荆图"的故事,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与金氏必为同胞姊弟无疑,他们之间的感情自当不同于从姊弟,敏轩对乃姊早年夫丧子亡的不幸以及方始中年就已病逝,是极为悲痛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同胞关系。
在料理完乃姊金氏的丧事以后,炎夏已过,秋凉渐生。吴敬梓趁此次返乡的机会,曾去乌江附近的山中,看望住在离项王庙不远的伯兄。在伯兄家中,大约住了八、九天才分别。这位长兄,我们无法考知他的姓名,但传主在为其姊金氏所作的小传中既然说"吾鲜兄弟"(见《金孺人墓志铭》),那么这位"伯兄"自非吴霖起之子可知,但从他与这位"伯兄"的感情来看,也不类族兄弟,因为在传主众多的族兄弟中除了与吴檠关系较为密切以外,和其他的族兄弟关系并不友好,他在《移家赋》中就曾愤愤他说过"兄弟参商,宗族诟谇"。此外,这位"伯兄"如果是族兄弟,传主必会交代清楚,在《文木山房集》中写给族兄吴檠的诗、词有若干首,而在最先出现的四首七绝诗题中,就特地志明为"从兄",即《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这也与传主所写《哭舅氏》、《过金舅氏五柳园田居》一样,界限是分明的。由此看来,"伯兄"应该是传主生父雯延的长子。吴敬梓此次去"伯兄"山居中兄弟会晤将近一年以后,"伯兄"又曾到敬梓居处探望,兄弟二人联床夜话,还曾回忆起上次在山居中聚首时的情景。吴敬梓为之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地本烟霞窟,兄为巢许伦。百年歌帝力,十亩乐天真。抱阜宜营室,迂汀许结邻。绿回芳草长,黛染远峰匀。社鼓乌江庙(原注:居与乌江项王庙相近),灵旗牛渚津。山川馀质朴,习俗尚清淳。
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棱新。饧萧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馀稚子亲。
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兼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
蟹簖缘溪富,鱼罾罾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他这位"伯兄"原来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或是希冀自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居不仕的人。相传这两人为尧时隐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们二人,两人都不愿接受。传主把这位"伯兄"看成是与他们相类的人,正说明这位"伯兄"没有什么功名。但这位"伯兄"为人却十分耿直,不谐于俗,所以郁郁不得志,隐居山林,长夜攻读,白昼著述,孜孜不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自得其乐,不改素志,抨击时政,不媚习俗。所以敏轩称赞他的作为与王符、原宪相似。王符名节信,东汉时人,隐居山中著书,评论朝政得失,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愿显名于世,自号"潜夫",著有《潜夫论》十卷。原宪字子思,又名原思,孔子弟子,蓬户褐衣而蔬食,仍不减其乐,坚行其道。后世一般惜用他指代贫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日:"夫子岂病乎?"原宪日:"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对这样一位许时俗而安贫守道的"伯兄",在诗的最后,敏轩表示了与其终身相依傍的意愿:"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佛教指此生尚未了结的因缘为未了因。传主对宋代大诗人苏辙非常钦迟,在《移家赋》里就曾以"苏家则拭辙并进",比喻先世的兄弟关系。此处"未了因"显然也是借用苏拭寄诗其弟苏辙的诗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东坡集》续集二)正因为传主幼时出嗣给霖起为子,所以才与同为雯延所生的这位"伯兄"不能"长相倚"。难得聚首一次,天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禁抑不住,就吟之于诗。此外,从此诗通篇来看,这一时期传主的思想面貌,和早年一度对功名的追求和热衷已有所不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和功名富贵全然决裂,但显然对这种追求逐步感到厌倦,功名富贵观念己大大薄弱,而对时政的弊端、习俗的颓靡,深深感到不满,并步步加深和坚定了隐而不仕、闭户著述的志愿。
此次敏轩回到故乡,正遇上岳丈叶草窗悬弧之庆。这位原籍苏州的老儒医将爱婿挽留在家,欢聚达十日之久。翁婿分手之际,草窗翁已预感到这次晤面可能就是翁婿最后一次聚首,因而特别眷恋。果不其然,不到两年他就病逝了。吴敬梓十分伤痛,写下《挽外舅叶草窗翁》诗: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莳。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匾》。园林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世。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
无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这位老儒医,一方面行医种药、熟读医书,一方面研究《周易》老庄之学,为人厚道,治学勤奋,安贫守素,不求名逐利,倒也十分逍遥自在。传主吴敬梓为他的岳丈无人为之"表微"而有些愤愤。在以功名得失为评品人物准绳的势利社会中,又有谁愿意为一个如同战国时家贫而又不求仕进的隐士黔娄那样默默无闻的寒士作传写铭呢?传主只能自己为岳丈写上一有挽诗,在这篇挽诗中,敏轩既称美了岳丈的高尚品德,又对岳丈贫困勤学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表示了深深的哀叹。
在这一时期,传主不但亲姊金氏、岳丈草窗翁先后谢世,而且不久之后,他的另一舅父又复病死,噩耗接踵而来,很使敏轩悲伤不已。特别是致老舅于不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功名不遂,这对传主的刺激很大。吴敬梓的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卑视,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有时为了不误考期,即使有病在身也勉力前往。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于抱恨病死。吴敬梓极为沉痛地为之写下《哭舅氏》诗: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皎皎明月光,杨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
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颠,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黄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
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在这首痛悼舅父之亡的诗作中,也倾注了传主吴敬梓大半生蹭蹬场屋的愤恨,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主试大人的衡文无准、对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的所谓"抡才大典"的无情讥讽,对这种制度所酿成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抨击,并且表明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贵"或"贱"都是不祥之物,是极不可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吴敬梓的思想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对早年所热衷的科举考试的弊端,除了通过他自身的痛苦教训有所认识以外,更从他的许许多多亲友的失败中有所感悟,"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只不过是由愤激而发出的反语。传主己充分认识到科举之途并非平坦大道,对绝大多数的士子来说确是此路不通!为此,他不仅对八股科举的考试办法、而且也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呼号。虽然全诗已佚,但仅从这残存的两句中,也可看出传主的心声。他的友人王又曾对这样的呼号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后》)这一认识,也是当时社会上批判八股科举的进步思潮的反映。其实早在明季未叶,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界对八股制艺的嘲讽和批判已形成风气。杨慎在"举业之陋"中就指出当时读书人很少通经,也不治子、史,甚至以唐朝事为宋时事,二事合为一事,一人分为两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而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之风已为时人所不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丙辰科会试,"家饶阿堵"的吴江人沈同和,被主考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所"首选"取为会元,以致物议四起;天启四年(1624 年)甲子科乡试磨勘,魏忠贤目不识丁,他的干儿王绍徽辑《点将录》,"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当时就有人作传奇《百子图》予以嘲讽(《茶余客话》卷二"明考试之弊")。于这一科始中举人的江西文人艾南英(著有《天偏子集》)因为久困场屋,对这种科举考试极为痛恶,写有《应试文自叙》述说他的坎坷,做了二十年老秀才,参加乡试七次才中举。明季末叶,甚至有"断送江山八股文"的议论,在朝堂上曾发现有书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的大柬,可见有识之士对这一考试制度的痛恨。这种批判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映,明清之际的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的小说《鸳鸯针》,是四篇白话小说的汇集,第一篇《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参加乡试一事,揭露了嘉靖时期科场舞弊、官场营私的黑暗情景。清朝初年,曾有画师绘八股图,图上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评书法名画、或调琴、或奕棋,目既不见,毫无所得,讽刺作八股的人如同这八替(见《清科举考试述录》)。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在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涉及科举制度,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指擿。除了形象的刻划以外,还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予以抨击,如《王子安》一篇"异史氏曰"这样写道: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皆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而不己,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类似的揭擿和批判,在《聊斋志异》的《司文郎》、《贾奉雉》、《褚生》等篇中均曾出现。蒲松龄所塑造的形象、所描绘的情节、所发表的议论,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所产生的恶果。这些批判的画面,在《儒林外史》中则以长卷的形式充分展开。
在传主吴敬梓时代,不仅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嘲讽科举罪恶的作品,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批判科举弊端的著述,例如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特别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十八房"、"经义论策"、"科目"、"明经"、"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与彦和甥书》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许多环节的种种弊病和黑暗情况,都有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也不亚于顾炎武。这些进步学者的思想,显然对传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吴敏轩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有着屡困场屋的痛苦经历,又目睹了亲友在追逐科第过程中先后调亡的残酷现实。在接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之后,传主终于进而从理性上对这一制度积习难返的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传主吴敏轩这种进步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到四十岁左右,当他的舅父病故时方始大体完成。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