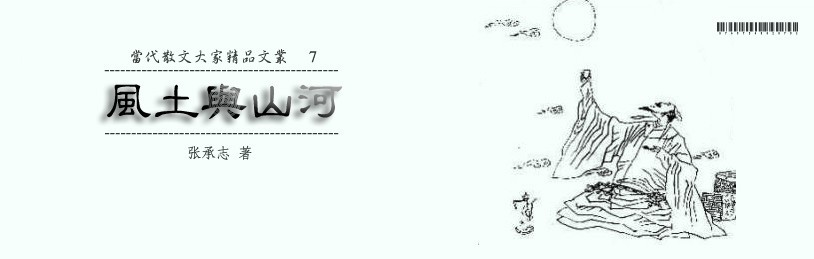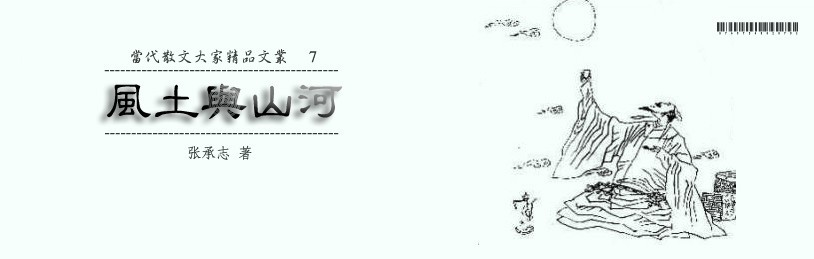|
|
一页的翻过
|
|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曾经未加思索地写道,游牧草原的循环不已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这么感觉的原因,是由于那时开始出现了定居,虽然只是草拌泥房子的定居。而且,一年中迁徙的次数在减少。此外迹象还有很多,比如,一直成为大草原形象的木轮子勒勒车,有被工业生产的铁筋车取代的可能。
而今天,这"最后的一页"已经掀得雷鸣风吼。它破坏着,替代着,唆使着,蔓延着,带着粗俗而生机勃勃的欢叫,恣情地在延续了十数个世纪的旧营盘上摧枯拉朽。
何止八瓣轱辘的自制木车,连轻便铁筋车也几被废置。草原的交通与驮载,正在被拖拉机和客货吉普车所替换。越冬、春羔、驻夏,加上秋季追逐草籽和营养的频繁走场迁徙,已经变成了一座砖房和一座毡房的基本定居。热乎的火炕,夹墙后的啤酒,使年轻人不愿动荡地搬家。都市里时髦的话题--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首先在一座座砖房周围开始了。
嘉陵、铃木,一辆辆摩托在嘟嘟穿梭。马群里的乘马发肥,赛会上难得挑出善奔的骏马了。而且三年两年不骑,驯马暴烈难御,还原成了"生个子马"。牛则几乎都是生个子;女人们缺乏驯顺的牛去拉车打水,从百步之外的水井打一缸水,居然要男人启动柴油拖拉机,一路黑烟地兴师动众。确实,女无乘车男缺坐骑的问题,牧人不愿意骑马的问题,破天荒地出现了。
Motar是什么意思?taisen是什么意思?还有yidang、erdang、lieji,听不懂的都是借词。它们分别是摩托、铁丝网、一挡、二挡、离合器,随潮水般的汉语借词涌入草地。加上啤酒瓶子、三轮货郎、盲流小偷、运牛车装修队,如今奔向乌珠穆沁草原的一切,使人目不暇接心慌意乱。
雇工即"使人"已非常普遍,而这个词曾被译成"剥削"。新页才掀开一角,就已经淘汰了第一批牺牲者;由于懒惰、病死、继承无人等原因,熟识的家族系谱中已经消失不止一家。当然相应的是迅速富裕起来的家庭,政府奖励了一个铜牌挂在哈纳墙上,上面刻着"小康户"。蒙文一侧读着让人忍俊不禁:这个词在六十年代译成"上中牧(农)"。
政治的社会秩序忽喇喇地坍塌了。当年被阶级划分理论打入凄惨底层的人,那些牧主和富牧子弟,今天不仅多是富裕人家,而且心思已在荣誉--比如热衷赛会的夺标。讽刺的是,当年的贫协主席又率先沦为贫困户;在吃光了最后一只羊以后,他和他的家庭都消失了。有人说他已去世,有人说他儿子正在某地当雇工。我听得目瞪口呆,不知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如今牧民养狗,盼着狗真的敢开牙咬人。草原上日益增添的喧嚣和络绎往来的小贩浪人,使牧民不知怎么过日子了。一层毡的蒙古包,不可能装防盗门,它只被一根皮条随便拴住。这扇门的文化,需要一种对传统的默契。闯入者使他们紧张。
活动半径缩小了,游牧被铁丝网圈定在自家十里方圆的草场。偏偏地球变暖,雨水稀少,羊毛跌价,草地沙化,因受益于最初的改革政策而骤然富起来的牧民,因经营和运气在后来岁月里败北的牧民,感到缺乏判断明天的经验,感到自己的无力。
于是人心向神明聚集,处处是新堆起的敖包。著名的大敖包祭会,如今是年中最要紧的行事。小敖包则密不可数;在自家领地制高的山顶,在大路或辙印的当途,在逝者指引过的地点。敖包(abō),这个在蒙古学术中经久地被人讨论不已的名词和现象,或许只是在今日才闪现出一点它的本意。
诗人纳楚克道尔吉有名篇叫做《MiniNutug》(我的家乡),这个词也被我反复学习过。它兼有营盘、家乡、草原、祖国几重含义。而今天nutug一词的语感多了对私有的强调,并且愈来愈频繁地指向草场承包以后,用铁丝网围住的那一小块"地盘"。
以上种种都是观察的视角,慢慢写来不忙;惟有环境的事,确实紧急:
前年回草原时,以前羊群珠散草海的风景,被挖上了疮疤似的黑窟窿。原来是承包了这片草原的一支采矿队,挖开青草,开出一个个采铜的土矿坑。采矿坑或是矩形的探槽,深数米;或是坑道,深不可测。
以前,牧民们讲述四周地名的时候,说到奥由特(oyotu),总是带着神秘的语气。"有翡翠的地方",它既是牧民的古老家乡,也是我插队的最初营地,听着我自然也很喜欢这个地名。谁知古老地名是一种原罪,因为它招灾酿祸,引人入室,天生就是破坏安宁和自然的情报。
马驹在矿坑里摔断腿,掉队的羊被人盗走。前年发现,牧民兄嫂的神经已经失衡,我也目击了游荡成群的闲汉,夜间轰鸣的载重卡车。黑洞愈挖愈多,南边山坡一片疮痍。采矿队每天用大拖拉机运水,水井几近干涸,在水草丰足的乌珠穆沁罕见的水纠纷,终于出现了。争执时一片混乱,各自嚷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家家的狗都晕了,不知该叫该咬。草原上甚至奔着两三头猪;这使牧民的小儿们大感新鲜,舞着马竿子追逐。去年夏天再回草原,牧民兄嫂更加憔悴了,他们求救般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在都市里,我们习惯了不安的生存。换言之,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在可怕的喧嚣中,让双耳渐渐失聪,让眼球终日充血,让心被扯出一根线,川流不息地抽丝失血。我们在大都市里,以憔悴换回存活,忘了安宁也是自己的权利。
而北方的大草原则不同。那里静谧得--据说能听见四十里外的一只獭子咳嗽。草海的潮动能吞吸近在咫尺的声音,所以经常是当汽车一直开到鼻子下头,才被人听见。
原来养牧五畜的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几千年时间渐渐凝结了自己的传统。他们享有几十里空阔的前庭,又枕靠同样几十里空阔的腹地。所以视野里任何一星人影都为他们了解,知道那是谁家的老人寻马找牛;同样哪怕夜深时分的一声响动也能为他们判断,会意到那是某某趁月色运草。
环境的巨变,安宁的打破,不仅是对一种千年未改的古老心理的压力,也是对一种特殊能力的破坏--牧民们对自己不能判断感到慌乱。无力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
总之,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游牧民的一项奢侈。虽然愈是比较都市,愈感到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怎样,安宁被打破了。
一连三年,每个夏季我都返回乌珠穆沁的草原,为的是在渴望的安静里休息身心;没想到,却看够了历史翻页的实相。
一年的富裕使我惊奇而满足。第二年门口就出现了闯入者;对来串门的采矿队,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叨叨些保护草场,心里却满是烦恼。我的安宁也被毁了,千里迢迢地,来看破坏植被。第三年牧民兄嫂要求我立刻去为他们上诉官员,他们已经急得乱了方寸。
窥见了历史的翻页,究竟是一种收获呢,还是一种痛苦?
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无论拉水的牛比赛的马,讲起来都是一本经,套套解数娓娓动人。无论语言的体系或一个单词的色彩,分析到底都会现出真理,闪起朴素的光辉。在如此世界里,男女老幼生死悲欢,无不存在得生动感人。它深藏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些人的基本问题。
若是培养它的环境存在,它就存在。反之它会逐步消失。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决定要改变这个环境。尽管世界上还有各大牧区,牧养(而不是厩养)的文化还在继续;但是,如乌珠穆沁那样的,相对纯粹的游牧文化类型,过去就曾经罕见,今后更临近终结。
随着一种强力的推动,在人对富足与舒适的追求之中,在对青草和对人的侵犯之中,机械人声轰鸣嘈杂,历史在以旧换新。
2000年4月再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