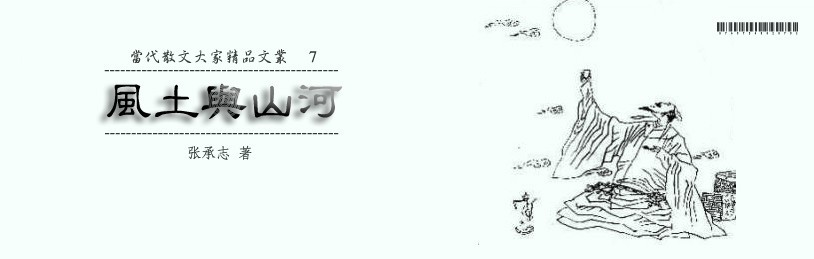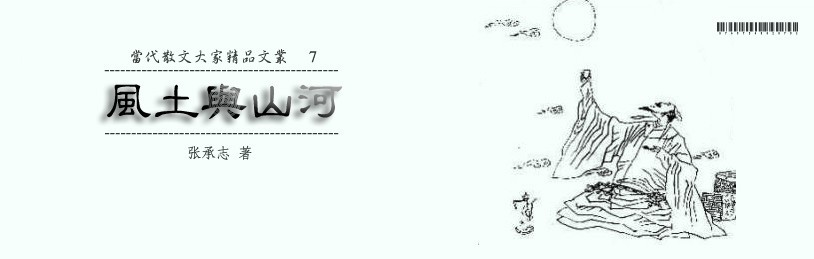|
|
从大坂到鱼儿沟
|
|
一
那一年我毫无目的,走了神一般地到了新疆。
到达以后,我从冥思中醒来,明白自己并没有任何非来的理由。所以那年的旅行特别随意,在吐鲁番的冬日乡村,游游走走,看看艾丁湖之类以前漏过的地点,和一些青年阿林讨论些学问。
如今我不再考古;到处都是我自己的,所谓青春的遗迹。已经是不用确认,也丝丝入扣地熟记着一些地点。走在火焰山背面的土路上,斜阳映在前面戈壁上的,就活脱像是自己往昔的影子。
弄不清目的,就一个个地找旧地点,然后用二十世纪最末几天的眼光,把它打量一番。正值白拉提的月份,村子里人人都忙,谁也没有留意我的情绪。三十年的结果,就是获得了在村子里这随意的徘徊。
渐渐地,心里忆起了昔日的同路人。我因为没有什么急事,心里就油然生了见他们一面的意。若能遇见,那就有趣了。天地人间,这些年沧桑变化,若能推心置腹畅谈一顿,该多么痛快。
牙尔湖,胜金口,默默地我们走着。如今的坐骑,已经不是泉子街公社的马,而是一辆价值60万的丰田越野。它无声地驰过崎岖山路,使我缓缓地穿过绵软松陷的、火焰山南麓的黄土。陪同的都是哲合忍耶的弟兄,他们只想着陪我旅一个游。
没有见到一个旧人。没有那一块走下冰川的向导,那赶毛驴的东干汉子,那寂静的三叉戈壁居民。没有迎头遇上一个维吾尔的牧人,或哈萨克的小姑娘。
二
那些一瞬的朋友,现在忆来,模糊而亲切。那么关键的时刻,是他们伸出的一臂,成全了事情也成就了你。
后来分了手,视野中的他们,就如车窗侧后疾疾退去的树,永远地退去了。留在车窗里面和现实中的,只剩了你。没准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回忆。但是他们再也不曾重现。
呜呜的寒风裹胁着白色的雪尘,锐利的风哨里,屋子都低低蹲踞在戈壁滩上,视野里,是冬季的吐鲁番。这对我是陌生的,我和路边的塑料袋、和白色污染般的旅游客一样,从来没见过吐鲁番的冬雪。
盯着初逢的,这片著名火洲上的积雪,我突兀地想到了一个,又是一个。这么近,能不能看看他们呢--脑子里的这个念头,刚出现就挥之不去,它鬼一般,立刻缠住了我,使我摆脱不开。最后迟疑着迈开了一步。
一丝念头油然而起。你渴望一次再见。确实,隔了三十年你懂了:只有窗外树木一样疾疾退去的他们,才是你的挚友。
"有一个赶毛驴的,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脸上有些麻子。八○年的九月,从吉木萨尔的大坂下来……"
我接着讲了那个故事,讲冰大坂上我得了人家好大的照顾,若是能寻上,当面道个谢多好。听着我的话,陪着的波音师傅(他开一辆像波音747的巨型大轿子车)和他兄弟都立住了脚,表情很认真。我一边说着,一边也渐渐把话当了真。我被自己的讲述拥裹着,说着说着,心思成了决意。
他俩寻思着,眼里一股遍知全吐鲁番的各族人等的劲头。我一面费力地回忆,一面描述着。好像是脸上有几颗浅麻点,个子嘛不高,黑棉袄,赶着五六个毛驴。从泉子街那边过来,天山里有一个维族人的地窝子……他俩听着,脸上渐渐浮出有了结论的神情。"怕不是算粒儿姐夫吧!"他俩说。
猛然间,脑子里掠过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直直地觉得,没准最要紧的事就是这个,去寻访曾经深山大漠地邂逅的人们,随便回顾。
这么一见,就是打开着肚皮,让两个心砰地撞上。已然不能再回那天山的地窝子,但可以在一处白杨黄泥的庄户小院,喝一个热茶,感叹一阵子那时的行头穷窘,野营孤单,叹惜一番大坂风景。可以一道摇摇头,苦笑着,彼此体会一阵--不好意思的热乎乎滋味。
可不是么,没有更要紧的事了。
那个算粒儿姐夫,能见得上么?
走,上车!他的家,就住在这河湾后头。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下山路上,在三岔口以前的一条山沟旁,他和我分了手。我记得他左拐弯,吆赶着他那五六个毛驴驮子,顺着山沟朝左走了。当时我在鞍上,用斯坦因的地图打量过他的方向。一个叫桃树沟的地名,被一条路连着,标在南麓的斜面上。
三
而这里,是交河流淌过的绿洲,是葡萄最茂密的地方。它和那寸草不生的狰狞南麓,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久没有这么害羞般的紧张了。在波音师傅兄弟身后站着,当他们拉着手问候的时候,我打量着这位姐夫。
像么?脑子里记忆一阵清晰,当年的毛驴客如现眼前。虽然眉眼姿势都不同,头发也已然花白。我等着紧紧的握手。过了十几年,他不就是应该变成这样么?
两兄弟介绍了我,仔细叙述了我讲的十几年旧事,并问他们的姐夫是否记得。说罢他们停住嘴,看着我们俩。
算粒儿姐夫沉吟了一会儿,开口了:"找的,怕不是我,"他盘算着说道,"从七五年起,我就再也没走过大坂。手里没有毛驴的日子,就更早了。"
我是否失望了?说不清。似乎我也盼着这么个结果。
--发生在那么大的山里,发生了那么久的事情,若是都能够心想事成,若是不论怎样相忘江湖的人,都能拐个弯就到了他的门上--难道那才不失望,那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
我正这么想着,却听见,波音师傅一边就这么说了。
四个人呵呵笑了,接着进屋吃茶,喧了一阵各式各样的话题。这个家院很静谧,和几家邻里都隔着一面坡。干葡萄的晾房,红辣子的串挂,看得我出神。一条分汊从大河里流出来的水,波光粼粼地,从山崖处绕过来,护着他的门口。对面视界开阔,能望见天山隐约的雪顶。
这里确实是波音师傅的算粒儿姐夫的家。他也是半辈子在两麓跋涉,赶着毛驴驮着葡萄。他和那年我在山里邂逅的回族毛驴客一样,甚至连长相都一样;微驼着背,个子不高,有几颗淡淡的麻子。
虽然说,人若相像时简直两人如同一个;但是,算粒儿姐夫并不是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冰川上,把一条棉裤让给了我的回回毛驴客。
不是他。我没有找到那一个。
四
在这块盆地,我还有一个念想再见一次的人,里铁普。
那时遥遥望着北面的天山,我忆不起自己曾怎样从那儿下来。那时他不抽烟,而我正对莫合烟爱不释手。太累的时候他也卷了一支。被他胖胖的妻子埋怨,说我教坏了她丈夫。我是怎么听懂的呢?
夜里那么随意地,就宿在维族聚居的鱼儿沟。吃过香甜的拉条子,就在里铁普的泥坯小院里闲坐。里外飘忽着好听的维语,多么和平的时光!记忆漫漶不清。究竟我怎样度过的那一夜?我一句维语不会,但好像我们一晚上都在交谈。
清晨,在小院门口,孩子要骑我的马。决定放弃马,改用毛驴车是再后一天的事。我们围着骑马的孩子照了一张像,然后就世事茫茫。
我凝视着照片上的那个维吾尔小孩。如今你已是一个维吾尔男子。此刻我终于明白了,惟有他们才是我的证人。我不埋怨拖延得已经太晚,尽管我跑得太远,不知为了什么浪费自己,而没有抓紧。我应该回去,找到他们,取回已经寄放太久的,我的珍宝。
如今只有照片最忠实。甚至它记录着鱼儿沟口的,一座圆拱建筑。你是一座拱北呢,还是一座寺?暗自问着,我听见自己声音颤抖,随即又被掩饰了。
关于里铁普的心事,我没有对波音师傅兄弟说。我想,如果我决意办这件事的话,我会不远万里再来。
捏着照片,我突然想:照片在那年交给了吐鲁番文管所,请他们代交。可是他们践约了吗?我凝视着。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你已是必须承担责任的男子,你是你的维吾尔民族的青年。你是在种葡萄么,还是当了一名学经的塔里甫?你还记得么,在你当巴郎子的时候,你曾经随着父亲,陪一个人远走戈壁。你还记得骑过那人的枣红马么?
越野车无声地驰过戈壁,可以看见罕见的残雪。如今我满心奢侈;认定里铁普的毛驴车,胜过正为我服务的丰田。这一次,就算是来看冬日的吐鲁番吧。时机不到,可以让脚印保持尘封,让往事继续沉睡。反正就在这儿,我们埋下了记号。
而且背景是那么巨大;有火洲的积雪,天山的斜面。吐鲁番如今对我是亲切的,处处有里铁普兄弟和算粒儿姐夫。
我沉浸在满足的感觉中,随着浪头一样的舒服颠簸。是的,我们不仅打发了岁月,而且把私人的痕迹,埋进了铁色的戈壁,和神秘烟村之中。
它们是来世的矿藏,挖出来的人,会分享我们尝到的滋味--它甜美又奇特。
2000年7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