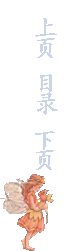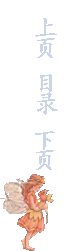|
秋天的早晨,爱米路两旁已排列着几十个小菜摊了。一缕淡黄色的阳光,才射出来便显得疲软无力地,胡乱找个怪腥臭的东角落里歇起脚来。那角落里的鱼贩着了慌,他知道自己的货色:十来条冰得结结实实的大黄鱼。虽然五更时曾替它们在腮上染过红,在肚上涂过黄,但总像四五十岁老太婆搽脂抹粉般,逃不过一般识货者的眼睛了,更何况给太阳这么一晒,光线虽弱,却也不到中午,定要从肚皮里流出腐臭的黑水来。现在就靠这堆小黄色撑撑场面,虽然小得还不到一筷长,但总可以不必着色,在爱米路上已经算是很出风头的了。
“小黄鱼,仅仗亮,三角洋细买一两!”鱼贩在摊旁大着喉咙喊,麻脸涨得通红。刚想咽下一口唾沫时,瞥见摊前有一个娘姨停步下来,便连忙把她呢住了问:“阿嫂,买条大黄鱼好俄?透骨新鲜个,再要好的爱米路上既没上了。”
“桂格小黄鱼卖几初一两?”娘姨偏不要大黄鱼,却指着那堆已经卖掉大年,剩下来只不过七八条光景的小黄鱼问。这些小黄鱼麻脸的想靠它们吸引顾客,以为兜售大黄鱼地步,所以一时还舍不得脱手。
“依要小黄鱼本,三角洋钢一两,二角九分我也不卖。——大黄鱼便宜些,就算仔二角半吧!”鱼贩慷慨地说。
“大黄鱼臭也臭脱哉,啥人要买?小黄鱼算仔二角半吧。”那娘姨一边说,一边就挑拣起来。
麻脸的火光了,劈手夺过小黄鱼,一面把她速速往外推,嘴里骂:“走开!走开!吃不起鱼,来寻啥开心?十好好黄鱼会是臭的,你妈的X才臭呢!”
正说间,一个厨子模样的人过来了,手里捏着秤,向麻脸的连连点头:“喂!大麻皮,今天给我串五条大黄鱼吧,我们东家要做羹饭。”一面说,一面顺手拿起一条来嗅,嘴里嚷:“喂,怎么你的鱼这样不新鲜?”
大麻皮挤挤眼,凑过去低低说:“大司务,这鱼实在不坏,不过日脚多些。算仔二角洋钢一两,你落得便宜些。多放些料里又吃不出什么来。”
厨子犹豫了半晌,他在理欲交战。又想贪便宜多揩几钱油,又怕滋味不好了东家要骂。
在他犹豫的时候,还有一个在摊前犹豫着,那是一个中年妇人,颧骨生得高高的,相貌还不错。她呆呆立在摊面前,又想买,又舍不得钱,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儿扯住她衣角,口口声声吵着道:“妈妈,我们买条大黄鱼吃吃吧!”
妈妈把小菜篮放在脚跟旁,伸手想去拣黄鱼了,忽又编了回来,迟疑半晌,拎起禁篮子就走。那个女孩儿急了,眼泪汪汪的直喊:“妈妈买鱼呀!妈妈买鱼呀!”做妈妈的硬着心肠哄:“阿因乖,快些跟妈回家去,妈已给你买好一斤萝卜了。”阿因望着小菜篮子连连摇头道:“萝卜不要吃,黄鱼好!”
那妇人看着她心里觉得老大不忍,小菜篮里除了一斤萝卜,几根盐菜以外,确是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只空着带回来的油瓶,滚来滚去,在与萝卜碰撞。于是她咬紧牙齿下个决心,重又把篮放下,一手拿起秤,一手去掏小黄鱼,嘴里安慰阿因道:“你别吵,妈就买条小黄鱼给你吃吃吧。”
“我要大黄鱼!我要大黄鱼!”阿因指着那些肚子快要流出黑水来的大鱼尸体说。
那时厨子终于觉得逃骂要紧,放下大黄鱼掉头走了,鱼贩便把他放下的那条抓起来递给妇人看,说道:“这条是还落价钢,二角半一两,物事刮刮叫。”
那妇人并不伸手来接,只看了眼,心里想到钱,便说:“小黄鱼好。阿因,你小孩子吃小黄鱼好!”
“不!”阿因倔强地回答:“我小孩子偏要吃大黄鱼!”
麻子看了阿因一眼,笑道:“还是小妹妹识货。——喂,阿嫂,再给你便宜些,二角二分一两吧,要不要随你。”
那妇人只是呆着脸,她在暗暗计算够不够。手紧紧捏着的算来只有一元几角钱,怎么能够买大黄鱼呢?于是她坚决地说:“我买两条小黄鱼好了,见钱一两?”
鱼贩的笑容消失了,他脱了她一眼,没好气的粗声回答:“三角一两。少一钱不卖。”于是,掉过头去同别人搭讲了。
那妇人拣了两条又大又新鲜的,掂过斤两,觉得太重了,便换了一条小的来秤,秤尾往上翘起来,麻子心火也冒起来了:“秤得平些!甘两头秤是不卖格。”
妇人也叽咕一声:“谁又用过甘两头秤来?”说着,便把秤锤移开些,仔细秤下几次,待讲价钢了,忽又发觉这两条中有一条是雌的,便又另外挑拣起来。麻脸的已连问过三四个人:“透骨新鲜大黄鱼要毗?”结果都是失望,便把气移到那妇人头上来,他恶狠狠地瞪着她问:“喂!拣好俄?都像你这样买二条小黄鱼要拣上大半天,我们别的生意可不用做了。要买就爽气些买,勿买就走开。”
妇人也有些动气了,把两条鱼扑托一声扔到他面前来,说道:“五两重。——你去秤吧。”
鱼贩便把鱼秤过,又问:“你说几两?”
“妈妈讲是五两。”阿因的记性倒好,抢着代妈回答了。
“五两?”麻子用他的大鼻子哼了一声,扑的一声把鱼丢回原处去了。“半斤黄鱼就是五两,亏你秤得出?”
“你不相信末,可借别人的秤来试试看。”那妇人一面说,一面仍旧拾起黄鱼:“五两重,给你一元五角钱,卖不卖?”
“要就两元四拿去,少一钱不卖。”
“一元六吧!”
“你又不是叫化子,要你一角钱。——拿来!”麻子鱼贩劈手板住她的菜篮,想攫出这两条黄鱼来,不料拍的一声,篮子扯坏了。
那妇人看的急了,又带着气,她的眼珠凸了出来,颈上青筋暴涨,直看喉咙怒喊道:“你这算是什么?怎么把我的篮子都夺破了。”
“是我夺破了你的篮子,你待怎样?”鱼贩也不肯让人,“买不起黄鱼去啃啃鱼骨头吧,别来这里瞎掏了。”
“我吃不起黄鱼,你又是吃得起的吗?吃得起的买了鱼自己吃去,还做什么鱼贩?”
“我做鱼贩又不是做你姘头,叫你找上门来作啥?”
“别放屁!赔我的小莱篮来!”
“哈哈”麻脸涨得通红地干笑两声,喉咙像怪果一般:“你倒会敲竹杠,自己破了的篮子叫我陪?暗暗,这几条大黄鱼统统赔了给你,好不好?”
阿因吓得快要哭了,躲到娘的腋下去。
妇人也有些胆怯,又舍不得篮子,只得转向身旁牛肉摊上的中年汉子说道:“你瞧,天下那有这种道理?不卖不要紧,如何夺坏我的篮子。”
“是呀,”那汉子也觉得义不容辞,挺身出来做鲁仲连了:“不卖就大家拉倒,你嫂子不用再同他吵了。”
“我要他赔篮子!”
“老子陪你的不姓王!”
“妈妈,我要回家去呀!”阿因听他们吵起来,看的哭了。
“阿因不要怕,”她妈气得快疯了:“我们找巡捕去。”
“去呀!不去喊巡捕就不是人养的,老子等着你。你这种泼货,臭女人…”
“你是强盗!你不讲理厂女人拿起破篮子,发狂似的向爱米路中跑去了,阿因在后面哭喊着追,给青菜担子一绊,便跌倒在地。
“哈哈哈哈”麻子高产怪笑起来:‘看她喊巡捕来捉我坐监牢去,臭婊子!”
“大家马马虎虎吧!”牛肉摊上的中年汉子在劝着他。
“妈呀!妈……”阿因哭。
“孩子绊倒了!”旁观的人喊。
“你这短命的小东西,连跑路也不会呀?”女人红着眼睛夺回来,一手用力托住篮子,一手把她搀起,更不安慰,拖着便跑,嘴里狂喊:“巡捕呀!巡捕快来呀!”
但是爱米路上没有一个巡捕的影子,许多人都站住了瞧热闹,有的互相窃窃私语,有的且跟过来看。妇人已经奔到大都路口了,还是找不着巡捕,只得又沿着爱米路跑回来,想到德华东路上找去。跑过那个角落时,鱼贩便笑着挪榆她:‘艰,你的孤老巡捕可找着了没有,老子好好等在这里有大半天了,干吗还不来抓人呀?”说着,心里感到一阵痛快,便无心再做生意,连鱼肚子里快要流出黑水来的事情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好容易,那妇人在德华东路的中段,看见有一个巡捕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过来,“巡捕先生呀,”她骤然遇着救星似的哭喊上去,阿因给拖得怪叫起来。“一个麻脸的鱼贩扯坏了我的小菜篮哪!”
“大家马马虎虎罢!”这个巡捕也是个怕多事的。
“他还骂人哩!”
“马马虎虎算啦!”
“请你到那个角落里去看罢,他……”
巡捕无可奈何地朝着她所指的角落里看去,忽然得了主意,对妇人说道:“那角落里不是我管的,你到爱米路上去找巡捕好了。”
“我已找遍了,找不着一个。”
“他们等歇就会来的。”说着,他自己就加紧脚步跑开去了。
那女人见没个下台,更加怒牌啤哭嚷起来,说道:“你不管也不要紧。等我自己去同他拚命罢!”说着,把阿困扶起,一手托着破篮子,飞奔向鱼摊来。
离角落不远时,又有一个戴眼镜的巡捕骑着脚踏车过来了。
“巡捕先生呀,”她第二次怀着希望狂喊,一面指着麻子鱼贩,“他把我的篮子弄破了,还骂人哪!”
“什么?”年青的巡捕跳下车来,摸出一本小簿子,要抄姓名了,女人心中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她上去指手划脚的,详细叙述情形。
巡捕同着她走到角落里,看热闹的人都围拢来了。
巡捕很得意,他知道自己此刻像个小说中仗义的英雄,拿眼睛向四周瞟了一下,便回头问鱼贩:“你怎么讲?”
麻脸上的一团高兴早已没有了,但还不得不强装笑容,他捏着喉咙低低说道:“你老爷不要听那婆娘的话呀,巡捕老爷,阿拉是规规矩矩做小生意的。那女人硬要拿我的鱼去,我急了,把她的篮子扳住。——她的小菜篮本来是破的,我碰也勿曾碰它过。曼歇外国头脑来了你也这样告诉他好啦……”
“我就是头脑,你这个坏蛋!”戴眼镜的巡捕听他说起外国头脑,心里大大不高兴起来。
“是啦,是啦,”麻子更加心慌了,一面努力挤眼睛,一面拚命露出排黄牙齿笑:“不错呀,你老爷就是头脑,我同头脑讲…你讲得咧!那个臭女人……不,那个女人家的话是假的,我…我晏歇送你两条透骨新鲜小黄鱼……”
巡捕的眼睛眯了一下,依旧想扳脸,但再也板不起来了。他朝着女人说:“我已替你说过了,你现在就算了罢。”
“我要他赔篮子!”
巡捕皱皱眉,不高兴地瞟她一眼:“破了也没法晖,你的篮子本是旧的。你们女人家做事总也不要太过分……”
于是旁观的人都你一句,我一句劝女人省事罢,一半像在拍巡捕马屁,一半像是真的嫌那个女人太多事了。那个女人没办法,想想众怒难犯,阿因又怪可怜的哭着,只得委委屈屈的掰着篮子,拉了阿囹一把,想回家去了,那时刚巧又有两个外国巡捕走过来。
“有啥事体?”一个高大个子的操着生硬的上海话问。
先来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国巡捕赶紧耸着肩肿过来,英雄气概全消失了,暗中还瞪了女人一眼,似乎戒她勿许乱讲。他露着牙齿笑,眼睛挤得没缝,一面纳纳地讲:“这个女人同鱼贩吵架,我已替他们讲过讲好了。”
“啥事体吵?”外国巡捕问女人。
女人擎起篮子,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但是外国巡捕听不懂她的话,只管自己揭起棍子赶旁边瞧热闹的人。戴眼镜的巡捕也连忙帮着赶,一面恶狠狠地连瞪那女人几下。
“我要赔篮子!”那女人说完事实,再补充一句。
“她的篮子本来是破的。”中国巡捕代鱼贩解释。因为他瞧见鱼贩已经把两条项大顶新鲜的小黄鱼在用稻草串起来了,定是预备送给他的。
外国巡捕点点头,对他们说话都似懂非懂,他只凭自己直觉裁定评判,他向那女人说:“你要买黄鱼,现在就买罢!”
女人弄得莫名其妙,她睁大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牛肉摊旁的中年汉子向她解释了,他说:“头脑叫你买黄鱼,你便秤两条罢,价钢不会吃亏的。”那女人知道说也说不明白,只得越趄着上来把鱼贩串好预备送给中国巡捕的那两条小黄鱼胡乱秤二下,一个外国巡捕便跑上来代看秤花,八两重,照限价只要一元六角钱好了,那女人喜出望外,看看阿因,便笑音音的付钱讫,一手托着篮子,一手抱起阿因走了。
外国巡捕去后,那麻脸鱼贩只得苦着脸,拣了一条大黄鱼送到戴眼镜的巡捕跟前,那巡捕源了眼,冷冰冰的说道:“那条大黄鱼是早已晒臭的了,我不敢领情,放着卖给别人去罢!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落水要性命,上岸要包袱雨伞的,刚才不是我替你在外国头脑跟前说好话,你此刻早已给他们带到行里去了。”
麻皮撞了一鼻子灰,诚惶诚恐,重新拣了二条小黄鱼出来。正拿稻草串时,只听得一声女人的怪叫,中间还夹着小孩子的哭声。看热闹的人又蜂拥过去了,不到片刻功夫,本额大的已打听明白回来,他们抢着报告大家,说是刚才的那个女人一手托着小菜篮,一手抱着女孩子回去,走到大都路转角时,突然有一个瘪三跑上来,把那放在上面的两条小黄鱼抢了便跑。篮子是托着的,一摇动还会不掉下来吗?于是萝卜在地上骨碌碌打滚,油瓶早摔得粉碎了。等女人放下孩子,一只只拾起萝卜时,看的问的人倒有一大群,那抢东西的瘪三早已从容逸去,再也没处追寻了。“那种瘪三也是怪可怜的,这女人晦气,孩子哭呀哭,她们该是没福气吃黄鱼罢!”报告的人报告完了,便下这么一个公正的结论。
“真的,这种臭货那有福气吃我的黄鱼?”麻脸又是一阵痛快,连忙把送巡捕的鱼串好。
巡捕接过鱼来,他听得正高兴,故事便完了,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他想:要是瘪三抢去黄鱼时,再打女人一巴掌,或者女人拾萝h时,让孩子给车轮辗伤了多好,谁叫她这么泼辣,刚才在外国巡捕跟前扫了自己的脸,又把鱼贩本来想送自己的两条较大较新鲜的鱼儿买去了呢?现在总算那瘪三替自己报了仇,好快意呀!他毅动着嘴唇,正想附和着说上两句幸灾乐祸的话时,忽然想到自己究竟是个巡捕,见了瘪三枪东西理应上前去捕捉的,怎么可以说风凉话呢?于是赶快瞧了小黄鱼一眼,沉着脸孔向鱼贩道:“这么小的黄鱼,叫我怎么吃法?再加两条,改天我一并给钱罢。”
钱贩虽然肉痛,却也不敢违拗,想想这两条又两条的意外损失都是那个臭女人作成他的,现在幸而那个具女人照样也破了篮子,丢了黄鱼,跟自己一样倒霉,倒底老天爷是有眼睛的,心里便也痛快了一阵。
那时候,太阳也似乎听得高兴起来,它便卖弄气力,由淡黄色光线变成金黄色了,那些大黄鱼哪里还经得起它的猛晒,早已一条条都从肚子里流出腐臭的黑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