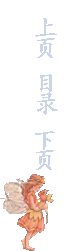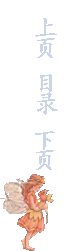|
幽幽的月光,稀疏的星,庭院静悄悄地。明珠站在窗口,心想今夜要防空,恐怕没有朋友会到这里来了吧。没有朋友来的时候是寂寞,朋友来得多了的时候会烦恼,来得少了的时候可无聊,而当他们回去之后却又使她感到无限的空虚。她对他们说:她爱静。于是他们都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她一面想,一面对着庭院痴痴望。只见门外有辆车子停下来,她的心里就一惊。接着她瞧见隐隐绰绰地飘进来二个影子,是男与女,手挽手儿,看上去像在交头接耳地谈话。他们走到明珠站着的窗前,男的忽然把嘴更加凑紧女的耳际去说了句话,于是女的就把头一偏,低声哗他道:“当心给人家听见!”可是明珠已听见了,而且听得很清楚,二个影子很快的又飘逝而去。
明珠瞧了眼幽幽的月光,稀疏的星,马上就把黑线窗帘放下来。厚的,重的,黑沉沉的帝幕,替她隔开了这静悄悄的庭院,隐隐绰绰的影子,以及外边的整个使她不安的世界。
她茫然站在房中央,房间黑黝黝地。是春天了啊,空气还是这么的阴凉。她看不清这房里的一切,但是嗅着,嗅着,她能够嗅出一切东西的所在:当中是一张床,床边有台灯,灯罩是绿玉色的,只要用手一板开关机,它马上就会吐出幽幽的光辉来。“要不要开灯呢?”她暗暗问着自己。自己说:“不开灯真是太阴凉了。”但是她虽然找出了要开的理由,却仍!日没有勇气去实行,脚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动弹不得。
刹那间,黑暗与僵冷,寂静与恐惧,一齐袭击到她身上来了。她觉得自己的膝盖已经冷得发抖,但是她得用力支持着,深恐一不留心会乘势跪下去,向全世界的人类屈膝。她想:她是只肯向上帝求救,而决不肯向这个庸俗的世界屈膝的。
但是今夜里上帝似乎也冷酷得很。他像是冰块塑成的东西,晶莹洁白得连尘埃也染不上。他不能接触热情,她的热情才一流向他,他便溶化了,很快的变成水。她怕水。她常把自己的心境比做蔚蓝的天空,可以挂一轮红日,可以铺密密浓云,就是怕下雨。雨水冲洗过,一切都干干净净,便又空虚了。
她不能不怕空虚,犹如她不能逃避空虚一样。她走到那儿,空虚便追到那儿,向她挑衅,把她包围,终于使她无以自在为止。她也知道,唯一解脱的办法,便是睡觉。地睡着了,空虚便给挡驾在外,不能追随她入梦,侵扰她的梦中的热闹。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她也很多做些事情来消遣时光,但是事情做完了,或者好梦醒转来之后,空虚又会找上她,冷冷地向她一笑道:“你总不能撤弃我吧?我的乖乖!”
她茫然站在房中央,瞧到的是空虚,嗅到的是空虚,感到的也还是空虚。没有快乐,没有痛苦,什么也没有,黑暗的房间冷冰冰地,只有她一人在承受无边的,永久的寂寞与空虚。
我要……!
我要…!
我要…呀!
她想喊,猛烈地喊,但却寒噤住不能发声,房间是死寂的,庭院也死寂了,整个的宇宙都死寂得不闻人声。她想:怎么好呢?开了灯,一线光明也许会带来一线温暖吧?……但是她的眼睛直瞪着,脚是僵冷的,手指也但冷。
渐渐地房间门开启了,一个颀长的影子悄悄溜了进来。是鬼还是人,她也不暇细问,只向他做个手势,似乎在命令他速速开灯。拍的一声,绿幽幽灯光喷射到床上了,被单是洁白的,湖色织锦缎棉被折成小方块放在上面,显得单薄,也显得有些孤寒。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寂寞吧?”客人笑嘻嘻地说,样子有些轻薄。明珠更不答话,心里很恨他,同时也有些喜欢他。
“怎么?你的脸色这样讲!病了吧?”客人逼近问,伸开双臂,似乎想抱她,但马上就放下了。明珠仍不答话,身躯本能地颤动了一下,似乎有温暖从心内发散出来,弥漫到全身。
灯光幽幽地流着,流到洁白的被单上,流到湖色织锦缎的被面上,流到站在床前的客人身上。客人穿着黑漆光亮的皮鞋,笔挺的条子西装裤子,深蓝色,象征着庄严的美。渐渐地,灯光似乎集中了力气,一齐照向他身上来,他也知道自己已成为焦点,.于是便挺起前胸,肩膀显得更阔了。白衬衫领子硬绷绷地,高托着他的俊秀的面庞。他的皮肤是象牙色的,眼珠乌黑,眉毛很浓,头发有些几卷曲。
“明珠!”他颤抖着叫唤一声,声音低而嘶哑。灯光强烈地刺着他的眼,他的眼睛带着迷惑,但却富有吸引力,终于把明珠牵过来了。“明珠!”他再喊一声,热情地,迫切地。明珠没有作声,她的颊上发热,眼睛再不敢瞧他,只默默对着床旁的灯。
于是房间里空气都换了样,阴冷是没有了,却有些陌生与新鲜刺激。各人的心里似乎都像火药般要爆炸起来,但却又恐惧爆炸,紧紧地按着使不许动。光与热,情欲与理智,在紧张地战斗着,灯望着客人,客人望着明珠,明珠又望着床旁的灯。
“今夜是防空呵!”客人说了声,明珠没有回答。深蓝色的条子西装裤移向床旁去了,拍的一声,电灯随着熄灭。明珠觉得很紧张,但是紧张更加逼近人来,欣长的身躯似乎就站在她面前,她的心里像马上要爆炸,但是手指却阴凉的。
阴凉的手指颤抖着,不知安放处,摸摸自己头发,却又滑到胸口下去了,另外一只手很快地就把它捉住,接着它感到那只手又热,又软,又有力。便是一阵无声的诉说,他的嘴已经凑紧在她的耳际了,她颤抖着,欲答无话,欲哭无泪。
房间是黑黝黝的,空气紧张得很。她嗅着,嗅着,便知道一切东西的所在。她知道他拥她到了床旁,洁白的被单,湖色织锦缎棉被,……一切的阴凉都消失了,火般的热情,手挽手儿,两人同人于疯狂的世界。
他说:“我不会使你养孩子的。”她点点头,眼泪直流下来。她知道,她此刻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份存在。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
“请你…··请你不要让我有孩子呀!”明珠垂泪恳求他,屈辱.地,似乎已经向这个庸俗的世界求饶了。但是他更不理会,只是猛烈地吮着她,她咬他耳朵,他也不退避,两个人身子贴得更近,心思却离得更远了。
黑暗的房间,更加黑暗了起来。明珠的心里充满着气恼,厌恶,恐怖,以及莫名其妙的新的空虚,他吻着她,轻轻说:“恕饶了我吧,明珠!”但是听出这声音里没有温存,没有喜悦,只有无限的疲乏与冷漠。
“别同我敷衍!”她恨恨地说,猛力推开他。但是他更不靠近来,只是懒洋洋地摸一摸她的下巴,说道:“不会有孩子吧,只这么一次。”
扑灯的绒,为了追求热烈,假如葬身在火焰中,还算是死得悲壮痛快的。只怕是灼着而未死,损伤了翅膀,给人家笑话,飞又飞不动,跌落在阴冷的角落里,独个子委委屈屈地受苦。“不会有孩子吧……只这么一次……”明珠痛苦地反复辨味这句话。这是句不负责任的话,他说过后就要扬长而去了,她还能向他要求些什么?
她对他说:她爱静。
他想了一想回答道:他知道,以后再不敢多来吵扰。
于是他们便分了手,陌生的,平淡的,再也没有新鲜的刺激,他知道她不爱他,她也知道男女间根本难得所谓爱,欲望像火,人便是扑火的蛾!
于是她更加沉默了,即使在白天,也要放下黑绒窗帘,把房间这得黑黝黝的。她不再咒诅空虚,只想解除痛苦,唯一的留在她身上的最大的痛苦。
她找到了一位产科女医生,女医生说,要解决这件事起码要两万元,手术是靠得住的,她犹疑着自己钱不够,但是那位女医生却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说:“何不向那位荒唐的先生去要呢?他做错了事,不该负责任吗?”
明珠退了出来,默默地更不说话。她想起教堂里碰见过的一位外科老医生,从来不结婚,性情相当怪僻,然而待她却好,她找到了他,羞惭地把一切经过说了出来,老医生更不多话,只把她引进手术室里,关上门,只让她一个人坐着。
当你等的时候,
全世界向着你笑,
但在哭的时候,
却只有一个人了。
明珠默默地念着这两句话,空虚地,却又带些感伤。她想到了自己的房间:有床,床旁有台灯,灯罩是绿玉色的,拍的一声把它开了,它便吐出幽幽的光辉来,照耀着洁白的被单,湖色的织锦缎棉被,以及床周围的一切。但是眼前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就想嗅,也嗅不到,生命是值得留恋的,就是给火灼伤了翅膀,也还想活着。
手术室的门开了,老医生穿着白外套幽幽地进来。他严肃地握住明珠的手,说道:“好孩子,不用怕,快睡到床上去。”
一阵阵剧痛,痛得明珠快晕了过去。她想不到不要养一个孩子也要受这番痛苦,痛苦得没有代价,穿竟是为了什么?老医生严肃地在旁边站着,瞧着她痛苦,似乎并没有不安。她的心里骤然起了阵反感,心想可恶的老东西,原来他不肯结婚,就是不愿女人有小孩,不想人类有后代……
但是老东西的脸也模糊起来了,瞧不清楚。她只痛得忘记了愤恨,忘记了恐惧,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庸俗的世界。突然间,一阵热血直冲了出来,她知道这是一个小生命完结了,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呼吸过空气,没有在人世上生存过一刻。
她觉得后悔起来,人世毕竟是可恋的,生命也应该宝贵。她杀了自己的孩子,为了顾全面子,为了怕麻烦,可耻的妇人呀。她现在才知道扑火般欲望为什么有这般强烈,有了孩子,便什么痛苦也可以忍受,什么损失也可以补偿,什么空虚也可以填满的了。
多愚笨呀,她自己!多残忍呀,那个老医生!
于是她恨恨地瞧了他一眼,低声向他说:请你走开吧,我要静。
老医生默默地走开了,心里只感到后悔。假如有一个孩子能带回家去,放在当中的床上,捻开了绿玉色罩上的台灯,用幽幽的光辉瞧着他小脸,那么该多么好。那时候,阴凉的房间便变成温暖,沉寂的空气便被沙哑的声音打破了,永远是春天,春天般兴奋。扑火般热‘请不是无目的的,它创造了美丽的生命,快乐的气氛。
但是现在呵!
老医生幽幽地进来了,两眼噙着泪。他颤着声音对明珠说:“孩子,我害了你了,我早知你如此,便不该替你动手术。现在你是后悔了,我也后海得很,这都是我的错误。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受人奚落,因此起了变态心理,一方面怨恨自己的母亲,一方面看轻一切的女人。自从我在教堂里遇见了你,孩子,我便觉得你的可爱。我是不想害你的。不料今天你犯了罪,我深恐那个孩子养下来要遭受同我一般的命运,因此我便把你引进手术室里来了。可是,孩子,如今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痛苦,我便觉得后悔起来,我觉得以前我母亲……”
“你的母亲是不错的!”明珠流下泪,认真地说。
“是吗?”老医生替她拭去眼泪,一面额上直冒汗:“我想不到你会如此痛苦,现在我是连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我只好先送你回家,替你安顿好,希望你早日康复,好好嫁个人吧,不要再胡闹了。”
明珠默默地听从老医生把她送到了家里,房间仍是黑黝黝地,因为老医生恐防她吹风,早已替她把黑绒窗帘全放下了。她侧卧在洁白的被单上,盖着湖色织锦缎薄被,眼睛只望着绿玉色的台灯,老医生歉疚地问:“孩子,你在想些什么,可要告诉我吧?”于是明珠亩动着嘴唇低低地回答道:“老医生,请你不要笑我,我是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