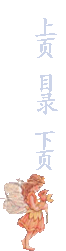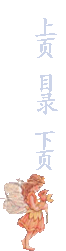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
我在青岛耽搁了几天,其中只有一次是与姊姊单独在一起的,她对我说了许多肺腑话。
“唉,小眉,我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只可怜母亲白养我一番,她把辛苦积蓄下来的钱给我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如今却落得如此收场。”
“姊!”我听她说得难过,便想宽慰她几句,然而泛泛的几句安慰话又有什么用呢?她卧病这许多时,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自己的一切,举凡防搭话说以及有关补饰的各种药品方单地都详细看过了,她的医学常识--尤其是关于肺病部分的一一简直丰富得惊人。有一次我在上海报上看到美国将运来大批“肺病特效药”的消息,兴奋异常,便赶紧写信去告诉她,仿佛此药一到,核菌就马上可以赴尽杀绝似的,不料她瞧了此信后淡然一笑,对国保说道:“所谓肺病特效药,乃是叫做斯屈罗吐梅新,在美国杂志上早有此类宣传,但他们并没说是特效或什么的,只不过讲此药对于肺病可以有帮助(help)罢了。”当时国保听着未免扫兴,便问:“那么绝对有效的药可有没有呢?”妹姊苦笑道:“到现在为止,实在还没有。我也只恨世界上那些科学家太没用了。”国保反问:“然则可否先找几种比较有益的--至少是无损的药品来试试呢?”妹姊答道:“有益的药品据我所知就有一百多种,无损的更不计其数了,那里能够一一都试遍呢?”总之,她对于自己的病一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对此简直无话可说。
她见我喊了一声“婉姊”以后又不说话了,大概也知道我是无话可讲,便又自己说下道:“小眉,我不知道人死了究竟有鬼没有?以前我是个无鬼论者,现在我倒希望能够做个鬼也好,我可以到A城去看看母亲同你的孩子,到上海去看看你,或者仍回到青岛来看看世材哥他们一家子。人死了若是什么都没有,那真是太……太无趣了。”她说着又轻轻咳呛了一声。
我痛苦地说:“你也许不会…的。”
她苦笑道:“怎么不会?我知道我一定会的,只差个迟早罢了。我已经活到三十几岁,原也不算太短命,只是我自恨生活得太单调了。从小学到大学,整整十六年中,我只知道用功念书,拼命省钱,吃的穿的什么也舍不得花费,省下钱来想买些书,哪知道到了今天,医生却禁止我,不许我再看那些伤脑筋的书呢?我只能每天看看报纸,连广告里的图画与文字都统统给我记熟了,真是无聊得很。其实我就是多记得些别的书本里的文字图画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反正什么都完了,白费了一番心血了。”
我惋惜地说:“真的姊姊,你也实在太要好了,太用功了,这才损害你的精神与体力。假使你当初读书肯读得马虎一些,现在教书肯教得马虎一些,也不至于如此了。”
她答道:“就可惜我从前不肯这么想呀。在读书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用的是母亲千辛万苦节省下来的钱,怎能忍心不好好的求学问呢?于是朝也用功,暮也用功,结果背也弯曲了,眼睛也近视了,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考了个第一名,母校教授恳切留我在校中当个助教。在大学里当助教原是件难堪的事呀,好比用惯了娘姨的少奶奶骤然去替人家当根姨了一般,但是我还是答应下来了,为的是留在校里,做研究工作较方便,而且将来出洋留学的机会也多。小眉,你可知道这十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梦想着去留学的呀,抗战时期我随学校迁到内地,生活是够苦的了,但我还是把仅有的几个薪水节省下来,托人兑换美钞,以便将来有机会出国时可以贴补费用,还要留下一部分来供母亲使用。谁知道一切希望成了泡影,我的身体就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一天天坏起来了,同时我又不能及早疗养,只是拖着病去上课,上课。我也知道肺病原是一种顶讨厌的病,因此在人们跟前总不愿提起这个,后来人家似乎也疑心到了,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我只回答说我家的人生来都是如此瘦的,没有关系。有时候我觉得喉头奇痒,就拼命自己忍住,不愿咳嗽出声来。到了真真忍不住的时候,我只得向人解释说是自己最近患感冒了,人家朝着我冷冷的笑,多难堪的,这种恶意的,怀疑的,令人难受的笑啊!小眉,我不是没有卫生常识,也不是不讲究公共卫生,我也知道自己的病菌传染给别人以后,是于人有损而于自己无益的事。然而我又将怎么办呢?进疗养院吗?没有钱。连向校方请假都不可能,因为我是教一天书吃一天饭的呀。可别说这样一个小小助教位置,钻谋的人多得很哩,我若说出生病,人家就会强劝我休养,那时候饭碗便保不住了。于是我只得昧着良心装无事人,直等到第一次鲜血直喷出来,这才不得不自己识相一些中途退出伙食团了。于是以后的事情更忙,上课教书以外还要自己在煤油炉上做饭菜吃,没心思或者没气力做时我便在外面胡乱买些来吃…情一天深似一天,人家成绩比我不如的都一个个得了出国留学机会,不久又从国外得了学位回来了,当教授的当教授,有几个甚至于当起系主任来,只有我因为身体不争气,竟自当了七八年助教,还是前年调到S大学来,才升任为讲师的,可是…可是现在又不得不辞职了。你刚才不是说我做事太努力吗?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女教员,要是不卖力做事,又有谁肯容留你呢?这几年来总算人家还待我不错,但我自己老是战战兢兢的觉得心里不安,我的病……”
我说:“姊姊,你就别再多想着吧,我知道这些年来你是太辛苦了,现在你应该舒服一些。我知道你是什么也没有享受过的。”
她苦笑道:“现在失业了,还讲什么舒服与享受。只有这次病中,在医药方面的钱倒是花了不少,如X光摄影啦,打葡萄糖钙针啦,吃的还有维他命丸,鱼肝油精,退热药,开胃药,安眠药,止痛药等等,这也许可以说是医药的享受吧?……”说到这里她又忍不住干咳两声,似乎觉得此刻可决不是讲笑话的时候,于是又改变语气说下去:“可是你知道现在西药又多贵呀!我只有这一些积蓄,想来是不够多少时间花的。要想回A城去又不能够。住院虽说可以打一个折扣,但是算起来至少也得二元钱一天哩。国家从来没有厚待过我们公教人员,我能够积蓄这些钱,都是靠平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那里知道现在竟会完全花在医药上呢?唉,小眉,想起这些钱来我就伤心…”
我听着也觉得惨然,连忙阻止她说:“但是,姊姊,医病也是正经用途,这是要紧的呀。”
她冷笑一声道:“你以为要紧吗?一般人却并不以为如此哩。即如世材哥与世材嫂吧,他们虽然热心替我买药,有时也常送小菜来,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心里也是并不以为然的。他们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死并不重要,有病就随便吃两剂药,不好也让它去,又何必如此认真花大钱呢?不过现在我所花的还是自己的钱,所以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假使将来有一天我要开口向他们借了,那就恐怕另有一番景象吧!不过这个我也并不怪他们,家庭中的一般人物都是如此想法的,即如世材娘去年她自己病了,也是死摸着钱不肯放松,宁可拿一条性命同细菌拼,结果大概是她的天然抵抗力强,居然也好起来了,于是她便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便不要紧的。我们女人生来是苦骨头,不大容易做毛病,就是做了毛病也会带病延年,不比得他们男人家要紧。古人有句话,这叫做男人是七宝金身,女人乃丑陋之体。如何可以一样看待呢?‘这是我们女同胞自己讲出来的话,你想听着气人不气人?偏我这根苦骨头又不争气,毛病一天一天拖下去,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假使……”
“……”我想要阻止她,却又说不出话来,心里觉得一阵阵的酸楚。
妹姊似乎也知道我的难过,使改口说别的道:“小眉,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这里隔壁住着一个男病人,他也是肺结核患者,进院不过才半月光景。他的太太每天亲自送小菜来,鸡啦肉啦,吃也吃不完。听说那位先生在好的时候是嫖赌吃着件件都来的,如今病了,依旧家兴不减,常常对看护小姐说:’做人有什么道理呢?我是吃也吃尽了,穿也穿遍了,玩么玩厌了……在世的时候见识过花花世界,死后碰着阎王老子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交代了吧?‘原来他认为人生是以享受为目的。可怪他的太太在旁听着非但丝毫不着恼,而且生怕他真个去见阎王老子办交代了,便抱着眼泪鼻涕一把拉住地道:’你别这样想呀,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到那上面去呢?阳间里东西总比那面好。只要菩萨保信你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你要玩只管玩,我如今是想明白了,再不多说多活了。‘男的听着便点点头,安心睡着想他的花花世界玩意儿去了。但是昨天忽又吵起来,说是住在院里怪闷气的,他要回去,理由是:’好又好不了,死又死不了的,天天叫人躺在这里算是什么?这里的饭菜又不好,看护服侍又不周到,而且全夜开着电灯,走廊上人声不断,害得人家睡也睡不着了,你们这算是骗我铜钱还是什么呀?半夜三更人家刚要模糊合眼时,看护倏地推门进来,拿着报又硬又冷的寒暑表往人家嘴里一塞,吓得我心头乱跳,还以为是白无常要弄死我哩。要死也死到家中去呀。
我插嘴问:“后来他就出院了吗?”
妹姊笑道:“还没有。因为医生说他必须缠石膏,恐怕要在医院裹住上一两年哩。”说完以后,她重又想起自己的事了,说道:“在医院裹住久了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只是我无家可归,世材哥家里是不能去的,你在上海又只有两间公寓房子,母亲在A城带着你的孩子……唉,可惜S大学给我住的一间宿舍又给他们收回去了,我的行李书籍都寄放在世材哥家里,上次我曾关照他们喷射些消毒药水在这上面,我如今…知今想起来做女人还是平凡一些好,老老实实的嫁人管家养孩子,这就叫做幸福呀!与众不同是不行的。希望就是件骗人的东西,害人的东西,这十几年来我完全给它骗了,给它害了!”说到这里她的颧骨泛红,我怕她太兴奋过度,又要发热起来,急中生智,我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就对她说:“姊姊,我有一句要紧话忘记对你讲了,世材哥从人家处打听得来,说是有一种草药叫做龙舌兰的,对于肺病很有效,姊姊,我看你何妨试一试呢?”
她凝思片刻,在凹进的眼眶里终于又射出希望之光,一面欣然问:“龙舌兰又是什么东西呢?你明天最好去买一本《本草纲目》来给我看看,我对于中国的药是一直不明白的。不过……若这药吃了没有坏处,我想就买来试试也不妨吧,好在草药的价钱从不会太贵……”
谢谢天,她还没有放弃“生”之希望,她没有忘记钱的打算,她愿意让我们买些龙舌兰来试。他们原来是平凡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