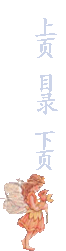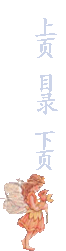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
鸣斋先生是我的公公,这个人也有一谈的价值。
当我最初嫁过去的时候,他简直是高兴极了,遇见客人就说:“瞧瞧!女人总是读书有学问的好,小眉虽然年纪轻,但是肚里明白,说起话来也斯斯文文的,那里有像她婆婆这样笨头笨脑呢。”这类话,他甚至于当着婆婆的面前也说,我觉得怪不好意思,却又无法可以阻止他。
有时候,他忽然恨起承德来了,便骂他:“不中用的东西,我花了这堆很洋钱给你读书,你还要留级,瞧,小眉虽然比你低两级,但是她的程度比你好;看你这个不害臊的,当心给自己老婆追上。”因此承德也迁怒于我,动不动就说:“像我们这种不中用人,那有资格同你女才子讲话?”我常常有口辩解不清。
在我们的新房楼下,住着一位田家妈妈,她是鸣斋先生好朋友田老板的妾,田老板的家里。儿子孙子已经有一大堆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胡调,所以娶这个妾的时候是瞒着家里的,到后来还一直瞒着,虽然她已替他养了一个女儿。他把她寄住在黄家,是因为自己不常来过夜,恐怕她独个子过活会有靠不住的地方,所以把她搬到这里来,以便托付鸣斋先生监察着。鸣斋先生不收她的房钱,但她总是常送贵重的礼物来,言语之间也是竭力奉承着的。
自从我进门后,鸣斋先生便笑呵呵的对她说道:“田嫂子,你瞧我的媳妇怎样?还长得不错吧!田家妈妈嘴里当然说:“漂亮极了。”但她在背后却常同姨娘等华撇一下嘴巴道:“我瞧这位新娘子呀,漂亮虽漂亮,但是没福根的。我料准她不得从一而终,她的八字是官杀混杂……”后来这类活也有些给鸣斋先生听到了,他在自己太太跟前大发脾气道:“以后不准理这种下等女人,我的意思就是说田家那个坏货,懂吗?谁也不准理她!一个有知识的女人那里会像她…哼,做小老婆的人那里有好货,我们田老板一生讲究道德文章,却坍台在这个坏货身上……谁也不准理她!”
但是爱理她的不是别人,却是他的亲生儿子承德。他常跑到她家去闲坐聊天,田家妈妈问他:“新娘子很得人意吧?”他冷笑一声道:“她是女才子,我们实在高攀不上。”田家妈妈似乎很满意这个答复,便又问:“上海女人都漂亮吗?”承德使指手画脚的谈个不了,最后还说他以前在中学时候的女同学仇莲华,她也在上海,跳舞跳得顶好的。
我的心中像给戳了一针似的,痛苦良久,虽有鸣斋先生拼命袒护着我,但是一个女人既不被爱于她的丈夫,还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接连养了二个女儿,这可惹得鸣斋先生也不高兴起来了,他常常在婆婆面前叽咕着说:“这可算是什么呢?一个丫头不够,还要再养出第二个来,亏她也不害羞!”婆婆劝他不要心急,说是他们两口子年纪都还轻哩,那怕日后没有七子八孙的?鸣斋先生听了仍不能释然于怀,他竖起拇指来说道:“寡欲多男,总是承德这孩子爱胡调所以才来了一个女的,又来了一个女的!若我与你,不是我们老夫老妻讲笑话,要求不养,现在若养出来准是个小子……只是你……一根骨一层皮……真倒胃口。”
但是承德还是有一个姊姊,她已经出嫁了。嫁到本城,一口气替丈夫养了三个男孩子。呜斋先生循俗不得不做催生衣服,到了满月的时候,又不得不做满月衣服等等,他眼看着一社一杠的把锦绣衣服抬出去,肉痛不过,便又骂婆婆:“偏你这个没用的女人,要养出赔钱货来,赔了嫁妆还不够,还要一个个替人家养儿子传宗接代,却叫我做爷的当瘟生,替他们满月催生。”婆婆劝他快不要说啦,大吉大利的,吵吵嚷嚷算是什么。他很得把拳头在桌上猛敲一下说:“放你的屁!什么大吉大利?人家添孙子又关我们屈事?你将来还想吃外孙做的羹饭吗?哼!我们送出去是一杠一杠的,他们的回礼货是什么?这种人家不懂礼貌,我是连瞧也不要瞧,唉!总之都是蚀本生意就是了。”
他的女婿家境不如他,因此他总觉得送来的东西欠贵重,这种人家不懂礼。但是我家也是贫寒的呀,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到:“都是蚀本生意”的话,我就觉得他意思之间也当然包括我家在内的。婆婆不会答话,给他骂不过时,只自拾起抹布来拭泪。
当承德在大学毕业的那年,恰巧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了。呜斋先生不肯放他出去做事,只自搬家到乡下东躲西避的,连元泰钱庄也关门了,因为鸣斋先生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好在他家富有积蓄,就是坐吃一二十年也不要紧的。
承德的姐夫也失业,有时候叫他姊姊来借此元,鸣斋先生总是愤然说道:“什么?现在是什么时代你知道不?这叫做朝不保夕,我是连一条性命都保不住呢!还有力量来照应你们?”有时候他的姊姊恰巧在我家,空中鸣警报!鸣斋先生便急急推出她们母子,说:“快些回家去!快些回家去!嫁出的女儿拨出水,要死也得死在你公婆家里去!否则,若一个炸弹不小心掉下来,连小孩子都炸死,你的公婆不要怪我绝他家后代报吗?去,快去!”但是紧急警报鸣后路上是不准通行的,他姊姊抱了孩子出去,在三岔路口常给警察拦阻回家,鸣斋先生不知就里,只是拍桌大骂:“叫你回去偏要换回来?是同我有什么过不去,一定要叫我为难?你说什么?警察会管这些事?他们又不是吃屎的,一定要叫人家把嫁出的女儿死留在家里。”
后来国军从上海撤退了,从南京撤退了,鸣斋先生便认为上海又太平了。但是有一点使他顶痛心的,便是他从前贪图利息厚,把所有现款都买了公债,后来又忙于逃难,没有把公债卖出去,现在却是国家打败仗了,公债也就变得不值钱了。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不识相的宋文卿还要对他说:“老板,我早就想到这一着的,心里很想告诉你,只为你这一向来避难到乡下去了,没有碰面谈话机会。唉,真可惜呀,真可惜的。”他听着这种话更像火浇油似的怒起来了,心想我避难到乡下,又不是逃到外国去了,你既想要对我说,难道不可以来找我的吗?不料跟我这多少年的宋文卿也会如此不忠心的!你一家子都靠我给你事做,你才能养活他们,你儿子的生意是我荐,虽然我不肯做保,但我从来不肯做保的呀,也不是对你不起的事,如今你的儿子赚到些钱了,因此我把钱庄关掉你也不可惜。这次我避难到乡下虽说没有通知你,但那是紧急时候呀,连夫妻都如同林鸟似的,大难到时要各自飞哩,别说是朋友了。你既知道公债要吃亏,就该设法通知我一声,乡下又没有什么飞机炸弹……
鸣斋先生毕竟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虽然后悔自己不该不把公债卖了,但嘴里却冷等一声说:“啊,文卿,不是我又要说你,你们到底眼光短一些。你以为偌大的中国从此就会完结了吗?不,不会的!有人替司令算过命,他是已日日生的,是土命,今年恰逢丁丑流年,于他不大利,但不到几时就好转了,那时候,哼哼,他老人家便岁寒知松柏,动荡识忠臣,怕不把这些投机分子,发国难财的一个一个都嚷嚷砍下头来?即使不杀头呀,给他们一个全尸,枪毙总是免不掉的了。人枪毙以后,财产还要充公,只有像我们这样不舍得把公债抛出去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国分子,公债还本加利不算,说不定还要送爱国匾额哩。”宋文卿听他说得振振有辞,心想他老板素来是个精明过人的,这次藏着公债不卖,其中一定有奥妙道理,因此他也后悔自己不稍留下一些,唉,即使是一些吧,总也还可以聊表爱国寸心,如今却是后悔不及的了,于是他便怏怏不乐回家。
鸣斋先生瞧着他忧愁样子,心里虽也痛快了一阵,但却抵不过公债不值钱的悲哀,他想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考虑数目的结果,便决定全家搬到上海住去。
在上海我们起初住的是统三楼,鸣斋先生有气喘病,楼梯跑上跑不怪吃力的,不久便搬了家。后来又因二房东太凶,楼梯头的一只电灯拍达柏达开关不停,承德与我受不过气,同她争吵了一场,于是我们又搬家了。这样接连迁移了几次,战事更加不利,日本人索性进了租界,鸣斋先生也就灰心起来,知道这爱国匾额是一对恐怕领不到的了,他就决心在上海长住,自己顶了一幢弄堂房子。等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家布置定了以后,这才想到钱已不够,承德是在中学里教书,收入只够他自己零用,鸣斋先生想要再做生意,但他把过去的光阴大都花在寻房屋及家中一切琐碎上,竟不知道市面情形已大不同了。换句话说便是他的这些钱,现在已经少得可怜,要想当资本运用是不可能的了。“家有千金,不如日进纷纷!”他叹口气说。一个人必须迎合潮流,天天奋斗求生下去,他当初以为自己的财力可以坐吃一二十年,不料法币日贬值,现在党是连数年都难以维持的了。同时宋文卿的儿子辈,在上海却大得意起来,他无颜去拉他们之类来投资,自己单独出资本又不够,所以虽然天天说要做生意,生意毕竟也做不起来。
人家见他坐食不计划什么,总以为他是存底丰厚,所以落得坐享其福做寓公了,他无法声明这点,也不息声明,只好含着眼泪听人家恭维。有时候他也试着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人诉苦说是维持不下去了,要想做些小生意,人家总是露出无论如何不相信的样子答:“你老板还要说什么笑话?你是金的银的一大堆,用也用不完的,那里会想到在这种地方做苦生意。唉,像我们这种度一天是一天的人叫做没法呀,日本人管得凶,带些货色出来动不动就是皮鞭抽,脚踢!假使我们有休老人家这样一半身价,也就坐在家里吃口现成饭了,谁又高兴去受那般鬼子的气?小老板现在那里发财呢?”
鸣斋先生不愿意回答人家说是承德在教书。现在教书是最落伍的职业,他觉得羞耻。想想一个剃头司务要赚多少钱一月?而他们堂堂大学毕业生却落得如此!他天天恨儿子不长进,谚云:“过海是神仙”,谁又叫你们不能过海的呢?还有我这么一个读过书的媳妇,也还只能在家里吃回现成饭,不及人家当女招待的反有小帐之类收入,每天可以带着大棒现钞进门来……
他的气喘病更厉害了,但赌气不肯吃药,说是不如让他死掉了干净。承德的态度也改变了,天天往外跑,像在活动什么似的,我又第三次怀孕,虽然不知是男是女,家庭里面整天阴森森的,住着实在怕人。
“总是上海人心太坏,所以这才乱许多年的。明年是癸未,后年是甲申,到了甲申年,无论如何会…唉,我的公债……一定会涨起来,就可惜我也许用不着了。”他在病中哼哼卿卿说:“小眉现在又有了喜,这次一定是男的,古人传下来说是’祖前孙‘,我平生积德不少,我的孙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唉,可惜我不能眼看着他长大……”
他就是这么的游着许多希望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