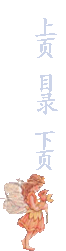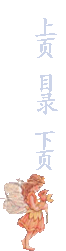|
我终于见到他了。
原来张律师还来不及打点,这事情据说已经给上面晓得了,下手谕要军法处速提审。
我拾了一网袋食物,鹊立在铁门外等接见。圆脸孔的兵士点头招呼我过去,在横桌上领了接见证,又叫我等着。六个拎着空篮的人退出来了,圆脸孔兵上推我说:“快!快进去。”我拎着网袋跟众人飞奔过去。
进口处有四张大桌阻挡着,桌旁坐着几个兵立,粗声命令我们把食物拿出来检查。其中有人带了一包瓜子,给丢在地上,说是里面不许吃的,叫他带回去,但瓜子已经散满在地上,也来不及把它们拾起了。另有一个人夹带了几枝香烟,给兵士刮两下耳光,把他推出去,说是今天不许他接见。
我静站在桌前,看检查完了,没有什么,但心中仍旧忐忑不安。里面的门开了,一片铁索琅档声,史亚伦已蓬头垢面的站在我对面了,他们六个犯人并立在桌子里边,我们六个家属则立在桌子外边,这一桌之隔,就仿佛悠悠无尽的天河!于是大家乱糟糟讲话,只听见声音,却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我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的西服已皱得不像样了,里面发黯,胡子满腮的,几乎使我认不出来。见了我,他似乎悲喜交集地喊了一声:“小眉!”下面的话也听不清楚了。不到二分钟光景,兵士就来赶我们出去,我不敢稍停留,到了转角时,不禁回头一望,只见他也正在走进去呢,我却瞧不清楚他的脚上有没有镣铐。渴望多天的面谈,就是如此匆匆一面又完结了。
晚上他又送信出来,叫我设法走看守所所长的路,先来个“特别接见”再说。他又在信中叮嘱我莫惜代价,只要他能够无事,就把这些“货色”用完了也甘心。唉,他如今事到临头,原来也要命不要钱了。但是我还是摸不着道路。
有一个陌生的人来找我,说是史亚伦的同室难友,他可以替我设法特别接见。他说起牢房里的情形:“全间只有像你家的床一般大呢。”他说:“关着六个人,还加上一只马桶。史先生给你写信便是拿这马桶当桌子的。他整天发愁,焦急起来又乱抓头发,我们担心他快发疯了。晚上睡的时候,简直像一听沙丁鱼,还把你的左手同我的右手铐锁在一起,要大小便时两人都得起来,唉,史先生恰巧是同我连在一起的,所以叫我出来找你,替你想法子办到特别接见。”
我听他说得详详细细,当然相信了。后来我们就讨论如何走所长的路。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与所长是换帖弟兄,他可以托那个亲戚先去探探所长的口气。他又关照我,这种活千万不可在输送信进去时提起,因为这是关系着所长的,他要是赫然震怒,史先生便要因此送命的了。我说我知道了。第二天他就很高兴的给我回音说事情已经说妥了,他的亲戚费了许多唇舌,最后所长总算看他面上答应下来,代价只要一根大条,因为这特别接见照规矩须得司令部里科长以上的亲笔字条,否则他做所长是有很大的干系的。我起先听了嫌代价太大,但再想想又无别法,只得应允了。他叫我准备好金条,明天上午九时他来陪我同去。
但是明天不到九点钟光景他又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看样子还很威武的。他替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他的亲戚王先生,住在淮海路十号A,同所长是要好朋友。我说:“一切全仗王先生帮忙。”王先生也就客气几句。于是史亚伦的难友,就叫我到别室去谈几句,问我“东西”预备好了没有。我说预备好了。他就同我商量,这“东西”最好先交王先生送去,因为我们在监狱里,见了所长不好当面行贿的。我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况且他又陪着我同去,不怕出什么毛病,便将一根条子交给姓王的先持去了。
到了九点多钟,他就陪我到司令部看守所,这时候铁门已开,外面长蛇阵似的又排列着普通接见的人了。他叫我在稍远处等候着,不要多说话,这种事情给别人知道了是要出毛病的。于是他就进去说是先要向所长打个招呼。半晌,他出来了,对我说道:“所长讲这时候恐怕人太多,进进出出似乎不很方便。不如到下午二时再来特别接见吧。”我无奈只得快快要回家去,他还说我们不必回家了吧,就在外面吃了午饭,再到这儿来。我想吃午饭还早着哩,也没有心思同生人多应酬,便坚决要回家,叫他到了下午再来接我。谁知道这次可出了毛病,我在家里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晚上找到淮海路十号A问时,那里又有什么姓王的呢?这才知道遇着骗子,然而却也不便声张,只得自认晦气罢了。
不过后来我毕竟也达到特别接见的目的了,是张律师替我设法的,没花半文钱。所长对我很客气,叫我坐在他自己的房里,而把史亚伦叫人带出来同我面谈。
史亚伦这才详细告诉我事情经过的情形:他本想骗他二条活动费到南京去的,混了几天便回来,说是活动费已用完了,事情一时还没有把握。后来想想横竖是一个骗,索性骗得大一些阳,就告诉犹太人说事情已谈好了,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军官答应帮忙,只要你把二十根金条付出去,被扣的货色在三天之内就可以发还给你了。犹太人本来不肯,说是先付半数吧,待货色发还后再行付齐。史亚伦便作色而起说这样可不用谈了,他本来是替朋友帮忙性质的,能够省事还是省些事好,请你另托别人吧。犹太人瞧着没奈何,也就答应下来。不过这金条一定要当着军官的面交付。史亚伦说很好。于是他又想一个办法,同军官约好--他同军人根本没有说起过这么一回事,只说有个外面朋友要请他吃饭谈谈,于是大家仍旧到三台酒家去。犹太人先到,不久他同军人也去了,他把犹太人拉到一旁,附耳告诉他说军官因为颜面关系,不愿当面接受,只三人言定了,他要先走一步,那东西由我带去交给他就是。犹太人因那个军官既已面谈了,想想也就不妨,便答应下来。那天他们在三台酒家定了一间雅座,完饭时间又提早了些,所以周围更无别人。可以畅谈无忌。那个军人是不懂英语的,犹太人又不懂中国语,于是他便从中捣鬼一番。吃饭毕,他对军人说是犹太人还有别的事要同我讨论哩。于是军人先告辞走了,他就这样骗到了“东西”。我问:“但是那个军官将来若知道了不会出来作证吗?”史亚伦笑道:“他这次在事实上虽然是给我做傀儡的,但在别人眼里看来他的确也像个同谋嫌疑犯呀,他是自己避祸还来不及哩,那里还敢挺身出来替犹太人作证?我若再小心一些,至多也不过打他一个招呼,给他些好处罢了。况且我在进来的前几天知道,他已经不在上海,到南京去了。”
“你没有告诉犹太人说那个军人在某团吗?”我又问。
他说没有。他只告诉犹太人说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军人,他不愿意太暴露身份,犹太人因为事涉纳贿,知道人家小心之必要,也就不追问了。
我想起了窦先生的话,便问:“你既不是军人,他们后来怎么又到保安司令部去告你呢?”
他皱着眉毛答道:“这就是他们做的圈套呀。后来犹太人请了一个性林的律师,大概就是这个姓林的坏蛋替他出了主意,说是中国法院办事顶糊涂的,这种官司着正式控告起来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了结呢,于是他们便在保安司令部里铺好路子,说是我与该部某军人同谋,这样司令部便有理由可以受理这案件了。其实犹太人也明知这军人不是属于保安司令部的,而且他又不知道这军人的姓名,而交付金条的事又没有确实凭证。按理这类事件,保安司令部是不能受理的,不过他们用了钱,我猜想他们一定是用了钱,保安司令部派人来密侦我了。那天他们得到报告说我在某处跳舞,他们便在该跳舞厅门口等着我,见我出来了,遂绑票似的把我绑到这里。当时我要求他们拿出拘票来给我看,他们说你到了那边自然会知道,没有大关系的。”
“到了那边又怎么样呢?”
“我就看见犹太人已先在里面了,还有一个自称林的律师也陪着他。后来司令部里的人就替我们调停,要我写一张条子,承认拿过他二十根大条,说是写了这字条就放我出来。我起初不肯写,后来禁不住他们威吓,就是不写便要灌冷水了,我一时急昏过去,使胡乱写了一张。唉,不知道不写还好,写了以后他们就说这是证据,把我正式押下来了。”
我听了没有什么话说,只觉得心里十分害怕。
他接着又告诉我那天军事法庭开审的情形,“是一个秃顶老法官问口供的,样子很凶。”他若有金库地说:“他问我为什么骗犹太人金条。我说我根本没有拿过他的金条呀。又问我那个同谋的军人是谁。我又推说既无骗钱的事,自然更无什么军人同谋的了。那老头儿听着大光其火,你说现有证据在这里,这字条明明是你亲笔写的,你还敢赖吗?从速招出军人是谁,以便本庭拿来一并问罪。我当时本想说出这字条是我到了司令部里被胁迫后才写的,于法无效。但再想想又怕因此而得罪了司令部里的人,他们也许要办得更凶,所以一时意回答不出话来。那法官见我不开口,便冷笑一声,谕令还押,改期再审。我回到监房之后,却又想出了一个理由,下次再审时我一定要对他说,就是:假使犹太人控告我诈欺取财的证据就只有我的这张笔据,则当此笔据尚未写时,该犹太人是凭什么来控告我,贵司令部又是凭什么受理这件案件而来拘捕我的呢?不过,小眉,辩论是辩论,听不听还要随他们的便呀,这军事法庭很厉害的,据里面的难友告诉我说,他们一不高兴就判上十年八年,又不能上诉,这样我还不是完结了吗?现在我真悔不当初,小眉,你快替我多方面活动活动吧,只要使我能够好好出来,我一定要改过做人。这些钱本来不是我的,用完也就算了。不过你要当心再受骗,那个与我同室的人有是真有的,他本来是一个拆白党,你这次只给他骗去一根金条还是大幸哩。小眉,我在里面万事不能同你商量,一切只好请你代我决定吧,就是弄错了我也不怪你。我在里面天天只想着你,觉得只有你过去所说的话是金玉良言,我后悔已嫌迟了。小眉,救救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