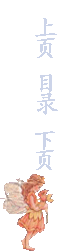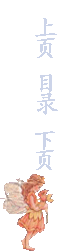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
为了解决失业中的食宿问题,好容易给我找到了一个XX妇女补习学校;该校专为成年失学的妇女们而设,每月膳宿费十八元,杂费一元;而住宿者至少须选习一科,学费三元,共付过国市二十二元正,总比自己租屋便宜,于是报名入学,静听程度与我学生差不多的教师讲解去了。
当然,我是醉翁之意不在于听讲,乃在乎寝室之间:但这寝室却也简陋得可以!不很方正的一间,铺了两张床,容股都有些勉强。朝两两扇窗,夏天晒太阳,冬天想是阴森森的了;臭虫多得怕人。至于食呢,桌大两碗小,十二个人团团圆圆的坐满了一桌,财触时的,夹菜时得用死劲。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四菜一汤:黄豆芽,鸡毛莱,应有尽有,很合素食运动之道;汤中飘着三五片肉片儿,真是"薄薄切来浅浅铺,厨房娘子费工夫;等闲不敢推窗望,恐被风吹入太湖"。早膳要到八点多钟始开出来,四碟菜中倒有三碟是昨天午晚两餐中匀出来的,勉强可以铺足盆底;其中唯一的新鲜位膳品要算半条油炸桧了,可是短短八段给十二人分配起来,至少总有四双筷落空。
学校里功课很马虎,训育却十分认真,平回校务主任把浴水不要多用哩,电灯迟开早熄哩,撒尿毋庸抽水哩,种种节省物力的大道理,无不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海之不倦。至于热水呢,须自己拿出钱来向外面老虎灶冲去,而娘姨又千呼万唤的不肯出来,闹到训育处去准是学生吃"牌头",谁叫黄妈和校长太太是亲戚呢!而且她也兼作校务主任的耳报神,哪个学生在外面吃饭的次数多,校务主任对她的笑容也多。
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为博得校务主任的好感起见,特地约了密斯王去亲戚家晚膳;真是半月不知肉味,不禁大嚼起来。回校时黄包车夫又不做美,半途爆裂了一个车胎,就搁了好一回,抵校时已九点零三分,校方刚拉拢铁门。我们连忙跳下车来,摇手诚地开开,老张已把钥匙纳入锁孔了,校务主任跳出来止住:"这里的规矩九时前必须回校,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忙抢步上前解释,并拉黄包车夫作证,请原谅一次。
"这没有原谅,"他打着镇江官话摇摇头,"你们今晚决不能进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宿一夜吧!要是关了铁门可以重开,学校将不胜其麻烦了。"
"叫我们到哪里去呢?"胆小的密斯王几乎哭了出来。
"开旅馆也可以。"校务主任拉长了脸转身过去。
我们着急了,攀住铁门喊:"先生!恕我们这次吧!我们身边的钱还不够开旅馆哩。还有,晚上要泡浴,要换的衣服都关在寝室里…"
"把你们放衣服钞票的地方告诉我,我去拿来给你们。"
我们又没有挽回余地,只得把皮箱钥匙从铁门递了进去;不久他便把我们的马甲短裤拿了出来。
"袜子还没有呢!"密斯王喊。
校务主任可真不惮麻烦,又跑进去替我们拿了两双短袜来。
"还有我……先生……"密斯王忽然想到了要换月经带,又不好店口叫校务主任再去跑一趟,只好咽住了。
这夜我们不好意思再回到亲戚家去,在马路上荡了半夜,将到戒严时才硬着头皮走进一家小旅馆。
又有一次,校长家里有喜事,全校师生都送了礼;我们是新生,没给请帖,也是不客气了。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了三个人,黄妈同老张都给喊去帮忙了,八点半还不见上饭。我们见不是事,预备自己掏腰包外面上馆子吃去,只是看看钟点已距关校门的时候不远,想起上次被拒在铁门外的苦楚,两只脚便再也不敢动弹。
"我们还是来吃些饼干吧。"密斯王提议。
我不响。站起来摇摇热水瓶,只只都空空如也。我们就饿着肚子挨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卷起铺盖,校务主任毫无挽留之意,膳费没得找,还催我们拿出仆役的赏洋来。一月来食不饱,寝不安的,出去检查一次体格,果然体重减了五磅,面孔黄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