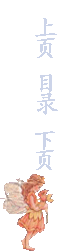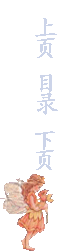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
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把旗袍脱去,换上套睡衣睡裤。睡衣裤是条子绒做的,宽大,温暖,柔软,兼而有之。于是我再甩掉高跟鞋,剥下丝袜,让赤脚曳着双红纹皮拖鞋,平平滑滑,怪舒服的。
身体方面舒服之后,心里也就舒服起来了。索性舒服个痛快吧,于是我把窗子也关好,放下窗帘,静悄悄地。房间里光线显得暗了些,但是我的心底却光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我的房间,也许是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但是那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坐在椅上看书,伏在桌上写文章,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我的房间,也许是龌龊得很,墙上点点斑斑,黑迹,具虫血迹,以及墙角漏洞流下来的水迹等等,触目皆是。然而那也没有什么,我的眼睛多的正好是幻觉能力,我可以把这堆斑点看做古希腊美术,同时又把另一堆斑点算是夏夜里,满天的繁星。
我的房间的周围,也许并不十分清静: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孩子哭声,妇人责骂声;而外面弄堂里,喊卖声,呼唤声,争吵声,皮鞋足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嘈杂声音,不断传送我的耳膜里来。但是那也没有什么,我只把它们当作田里的群蛙阁阁,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平已,决不烦躁。有时候高兴起来,还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静听,听他们所哼的腔调如何,所写的语句怎样.喊卖什么,呼唤那个,争吵何事,皮鞋足声是否太重,铁轮车推过时有否碾伤地上的水门汀等等,一切都可以供给我幻想的资料。
让我独个子关在自己的房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然而,这样下去,我难道不会感到寂寞吗?
当然——
在寂寞的时候,我希望有只小猫伴着我。它是懒惰而贫睡的,不捉鼠,不抓破我的旧书,整天到晚,只是蜷伏在我的脚旁,咕哈咕哈发着鼾声。
于是我赤着的脚从红纹皮拖鞋里没出来,放在它的背上,暖烘烘地。书看得疲倦了,便把它提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它的眼皮略睁一下。眼珠是绿的,瞳孔像条线,慢慢的,它又闯上眼皮咕嗜咕啥的睡熟了。
我对它喃喃诉说自己的悲愤;
它的回答是:咕啥咕喀。
我对它前南诉说自己的孤寂;
它的回答是:咕哈咕咯。
我对它轻轻叹息着;
咕喀咕喀。
我对它流下泪来。
眼泪落在它的眼皮上,它倏地睁开眼来,眼珠是绿的,瞳孔像条线,慢慢的,它又闭上眼皮咕喀咕哈的睡熟了。
我的心中茫茫然,一些感觉也没有。
我手抚着它的脸孔睡熟了。
于是我做着梦,梦见自己像飞鸟般,翱翔着,在真的善的美的世界。
自己的房间呀!
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我是寄住在亲戚家里,同亲戚的女儿白天在一起坐,晚上在一起睡。
她是个好絮话的姑娘,整天到晚同我谈电影明星。
"XXX很健美吧?"
"晤。"我的心中想着自己的悲愤。
"凸凸凸的歌喉可不错哪!"
""晤。"我的心中想着自己的孤寂。
"你说呀,你到底是欢喜XXX呢?还是凸凸凸呢?"
"…"我说不出来,想叹息,又不敢叹息,只得阖上眼皮装睡。
"唉,你睡熟了!"她这才无可奈何地关熄灯,呼呼睡去。
我独自望着一片黑暗,眼泪流了下来。
这时候,我再也不想装睡,只想坐在椅上看书,伏在桌上写文章。
然而,这不是自己的房间呀!拘束,不自由。
长夜漫漫,我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不敢动弹,头很重,颊上发烧,心里怪烦躁。
莫不是病了吗?病在亲戚家里,可怎么办呢?睡吧!睡吧!睡吧!我只想做片刻自由好梦,然而我所梦见的是,自己仿佛像伤翅的鸟,给关在笼里,痛苦地呻吟着,呻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