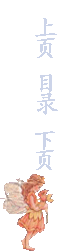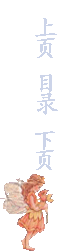|
一个女人在处女时代和母亲时代的种种不同相。
一个初中时代的女友突然写了封信给我,说是她在六个月前随夫到了南京,最近因镇海家中有事,决定带了她的"小天使"回去一趟,拟于明日上午八时乘京沪特快车动身,抵沪后拟在我家宿一夜,以便与我畅谈一切云云;末了还加上一个附启,说是最好请我于该日下午二时半左右至北站相候。这"小天使"三字使我起了无限好奇之意,张继杰也有了小天使吗?七年前在民众大会演说台上高喊"奋斗"时的情景宛然在目,后来听说她曾因反对父母代订的婚姻而出走,经过不少波折,终于达到目的,与徐鸣秋同居于杭州。"她的小天使一定养育得很可爱",我想起自己的小女儿薇薇还丢在奶妈的手中,自己却住在上海逍遥时,不禁起了愧见她们之意,这夜我做了许多梦,梦见她抱着秀兰邓波儿似的孩子望着我家薇薇胸前挂着的大悲咒袋子发笑。
次日我匆匆吃完午饭,略一梳洗,便披上大衣到火车站去。贤笑我一定会失望,他的意见是:"小天使虽是乐园中(富贵人家)的点缀品,但同时也是普通人家的累赘物;可爱敌不过可厌。"但我不以为然;于是分道扬镳,他出去干他的公务,我自向北站走去。
等了半点钟光景,车始到站,于是旅客纷纷出来,我站在收票处尽瞧,再也不见她母子俩。看看快到三点半了,出来的人更加稀少,忙去买了张月台票走进里面去,好容易在一节三等车上发现了她,一手抱着一个紫红缎袍的孩子,一手提着两块屎布在没作安排。
"啊,你等得我好苦!"我趋前大喊,又恨又喜。但她的态度却是坦然,告诉我:车到时极拥挤,得让人家先走;待要下来时孩子却拉屎了,这可不能不让他拉干净,塞在肚里怎么办?他在车上吃了不少东西,拉了倒干净。拉完屎就得替他揩屁股,总不能沾着屎就到你家来。有孩子的人可不比从前做学生时代,车到了提起小网篮就好走。她唠叨说来,好像还怪着我不知人家辛苦艰难似的,总不成刚碰面就同她吵嘴,只得笑着拦住:"算了,算了,总是做妹子的心太急不好,现在总该动身了。——你手里那两块宝贝东西还提着干吗?"
"亏你也是做母亲的人哩,孩子屎布刻不可少,还说得出丢掉?况且我这次带的又不多,……""好,好,好"我怕她又要滔滔讲下去,"但你这样提着总不成话儿,我们找张纸包起来吧。"一面说一面在邻座拾起张报纸来铺在椅上,叫她快把屎布放在上面。
"字纸怎么好包屎布?"她又出了花样。
"有罪我一人来当!"我不禁发起脾气来。这才喊了个工役来提皮箱及小网篮,还有许多罐儿盒儿之类,她抱着孩子,我夹着一包屎布,一同出了车站。
到了房中坐定,我们预备来叙一下旧,七年不见了,要讲的话多着呢,于是我开口:"听说你与徐先生结合煞费周折,现在目的居然达到,而且又有了这个小天使,很幸福吧?"
"唔,唔,"她且不回答我,自己脱去了高跟鞋,在小网篮中扯出一双皮拖鞋来套上,顺手递给孩子一包东西;那孩子早已爬到我床上,把我的那个白印度绸枕头抱在怀中当洋囝囝,见了那包东西,便立刻把枕头丢下,将那只沾着鼻涕的小手伸进袋去,摸出许多柠檬糖放在白毯子上,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但杰却毫不在意,拿手帕给他揩了一下鼻涕,接下去说;"你刚才说的我却以为也不见得——啊,保儿,你怎么把糖坐到屁股下去了。"她一面说一面替他把坐在屁股下的糖摸了出来,塞到他嘴里,"其实男人总是差不多,什么恋爱不恋爱,只是处女时代的傻想头罢了;有了孩子,哪个还有这闲工夫来讲爱情?我很后悔那时太伤了母亲的心,世间上只有……"说到这里,只听得"斯"的一声,保儿已把我那张用画钉钉在壁上的考尔白画片拿下来撕成两片:"啊呀!"杰忙把他搂在怀中,摸摸他的手,"快不要弄这个画钉,刺痛了手可不是玩的。——你也真孩子气,这种女明星画片也爱拿来钉在壁上;现在被他撕坏了怎么办呢?"
"不要紧,我也并不怎样喜欢它,撕了就算了。"我勉强笑了笑,"我也有了个女孩子,你可知道?"
"知道的,就是你那个在金陵女大的表姊告诉我的。─-就是你这里的地名也是她说给我听。"
"妈,蕉,……蕉……"孩子忽然发现了我早晨放在书架上的香蕉。
"给他吃吗?"我问。
"不给他怎么行?"于是我拿了只给他,一只给杰,自己也拿一只;但那孩子吵着不够,杰把她的一只也剥了皮递给他;对我笑了笑:"孩子总是好吃的,他断了奶后天天要吃上不少零食,肚子痛了他爸爸却怪我不好,我俩常因此吵架。倒是你们还在吃奶的孩子好弄;你的小宝贝多大了?"
"快周岁了。"
"我们保儿已一岁零八个月;刚好相配,我们两家对了亲吧。"
"你在说些什么?"我不禁愕然了,"你自己不是曾因反对旧婚姻而出走的吗?"
"这个我早已对你说过,实在一些没有意思!试看你们是父母之命结合的,现在夫妇间感情也不见得不如我们。秋同我虽是自由结合,可是自从生下保儿后,两人就常闹意见,譬如说:保儿撕坏他的一张图画,那值得什么呢?再画一张不就完了吗?但他却爱面红赤筋的同我闹;难道一个儿子还抵不上一张画?就是说孩子不好,又不是我故意叫他这样做的,这几岁的人知道些什么呢?还有……"
"你看保儿在做什么?"我打断她的话。她忙回头看时,只见孩子在掀自己袍子,忙把他抱过来道:"他要撤尿了,快拿痰盂给我。"我如言把痰盂递了过去,尚未摆定,尿已喷至我的腕上,等我把痰盂的位置放妥时,水淋淋的一大泡尿大都撒在地板上了。于是洗手,抹地板的忙了一阵。
"他虽然还只一周岁多,尿是从来不大撒在裤上的;有许多孩子到了六七岁,夜里还要把尿屎撒在床上哩。"杰很得意的告诉我。
我正待接口赞他几句时,贤回来了,于是大家客套几句;孩子见房中又多了一个生人,吵着要出去,于是杰独自抱着他到北四川路看电车汽车去了。贤见我的床上纵横都是香蕉皮及碎纸等物,枕头已被丢在地上了,不禁望着我一笑:"如何?小天使把你的床弄得这样了。我想今夜就让她们母子俩睡在这张床上罢,明天把枕套被毯都拿出去洗一洗。你就睡在我的床上,我到虹口大旅社去开房间去了。"
"你到外面去宿恐累她不安,我想我们就胡乱住它一夜吧,再不然我睡地铺亦可。"大家正在计议时,晚饭送来了,我忙叫他再端回去,点了几碗莱,加一客饭,做好了一齐送来。不料包饭尚未送到,杰抱着保儿先回来了,说是他起先见了来往不绝的汽车很快活,后来不知怎样又睡着了。于是我忙给她们理了床,让保儿先睡。吃了饭,大家闲谈一会,声音很低,保儿不时转身,三番四次把我的话头打断。夜里,那孩子不时哭醒,一会几撒尿,一会儿吃牛奶,电灯全夜未灭,我与贤睡在一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我很奇怪旧诗中的美人怎么这样不爱独宿,在我的经验,觉得一个人伸脚伸手的躺在床上,较两人裹在一条被里连放屁都要顾忌的总要舒服得多了。这夜直到五更光景我始朦胧入睡,但外面一些声音都听得见,我似乎听见保儿在天将明时还撒过屎。
到了六点半,保儿的哭声又把我惊醒,贤也转了一个身,没有开口;我知道他昨夜确也没有睡得好,而今天九时后又有事要做,心中十分焦急。于是忙一骨碌翻身下来,杰已在替保儿穿衣,一面在他嘴里不知塞些什么东西,不哭了;我披上了衣服,忙喊二房东家娘姨去开面水,说毕回房时,一脚踏在一堆湿东西上,仔细看时,天哪,床下都是屎,想是昨夜保儿撒的,杰也看见了,忙解释此乃她自己把痰盂的位置放得不好,并非保儿之过;说着,问我要了几张草纸,自己把地板拭净。洗了面,我告诉她牛奶须在八时左右可送到,她若肚子饿了,我们可到附近面馆去吃些虾仁面;她也同意了,于是我们赶快离了房中,让贤得安睡片刻。在面馆里,保儿又打碎了一只大碗,由我赔偿一角大洋了事。吃完面还只七时一刻,我想贤恐怕还未起来,故提议到(kun)山花园去玩玩,杰欣然同意。途中保儿似乎十分快活,我觉得他比昨夜美了许多。
到了园内,游人已不少,有中国保姆领着的白种小孩,有日本女人一面看着孩子们在土堆上玩得高兴,一面却自很快的织着绒线衫,也有在亭子里独自看书的日本男子。这许多孩子中我最爱一个印度婴孩,大概还只四个月光景,黑黑的小脸儿,大而有光的眼睛,抱在一个奶妈怀里,我不禁前去拉拉他的小手。"这种亡国奴理他则甚?"杰很不以我为然,自己却找了一个金发女孩玩,但那孩子似乎不大理会她;忽然,保儿把那女孩的头发扯了一把,拍的一声,保儿脸上早着了一掌,大哭起来;杰也动了怒,骂她不该动手打人,那保姆忙来劝住:"算了吧,这女孩就是住在花园这旁红洋房里的,她爹是外国人,胖得像猪一般,凶得紧,一不高兴就提起脚来踢人……"这时园内的人多围拢来瞧热闹,我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杰也站身不住,就抱起保儿一面骂了出去,在路上还愤愤的说外国小孩都是野蛮种。大来怕不要做强盗婆。
回到家中,贤已自出去;保儿仍是吃零食,撒尿,吵到外面去的闹上大半天,好容易挨到下午三时半光景,就雇了两辆黄包车送她们下轮船去;上了新宁绍,杰就喊茶房说要定一间独人住的房舱。"今天客人很多,没有独人住的房间;你要是不高兴同人家在一起,趁大菜间去好了。"那茶房半讥笑地答。
"我们偏不住在大菜间,要一间空的房舱。"杰气得涨红了面孔。我深恐那茶房再讲出不中听的话来,忙上前解释:"因为我们有孩子,恐怕夜里吵起来累得别个客人睡不着,故希望最好能自占一间;既是今天不得空,那就随便请你们排一间较空的便了。"
于是,茶房把我们引进卅七号房间,已有一个摩登少妇先在,鬓旁缀着朵软纱制的小花。"妈,花……花……"保儿一伸手就去扯她的头发,急得她躲避不迭。杰也不向她道歉,只问她是不是一向住在上海的,这次到宁波去还是到镇海去,……最后,请求她可不可把这朵花取下来让保儿玩一会。我从旁瞥见那妇人很有些为难的样子,于是忙拦住道:"这舱里闷得慌,我们到船边去走走吧;孩子也是喜欢瞧热闹的。"那保儿听见到外面去,也就不要花了;我们三人在一张统舱的空铺上坐下,瞧着外面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卖水果糖饼的小贩不断地在我们身穷挤过,当然保儿又买了不少吃的。
"啊,我托你一件事,"杰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我说:"秋叫我到上海后就写封信给他,好让他放心,我尽管忙着保儿也忘记了,今晚你回去替我代写一封吧。"
"这个容易……"我下面还有许多想说,可是不知如何开口好;我觉得我须尽朋友的责任对杰下个忠告,告诉她不能如此来养儿童:一个女人把她全部青年时代的精力用在孩子身上,而结果只有把孩子弄得更坏,真是太无聊了。可是仔细一想,像自己这样弃了孩子不顾,表面上过着有闲生活,而内心却无时不在彷徨矛盾之中的,还不是比她更无聊吗?我自己该走的道路尚未决定,而她却死心塌地的把灵魂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正如我家朱妈一般,在"上帝保佑我们"之中消去了一切烦恼,她们能在小天使的鼻涕尿屎里及似通非通的汉译赞美诗中找到无上的快慰,这真使我羡慕而无法仿效;我还对她说这是不对的吗?还是索性不说呢?——正踌躇间,忽听得一个统舱茶房嚷起来道:"怎么?你们的孩子撒了尿,把我放在这铺下的什物都弄湿了!"我低头看时,真的蒲包纸包上都湿了大半,地上也有水,但杰却在否认:"我家孩子从来不会乱撒尿,也许是别的水吧?"可是那茶房却也不甘认错,就扯起保儿的紫红袍子让她自己瞧个明白:"你看,裤上不是也湿了吗?"我情知这是事实,只得对茶房表示歉意:"孩子的事真没办法!——你这包里的东西还不要紧吗?最好解开看一下……"那茶房咕哝着去了,杰还在独自分辩说保儿在南京时从来没有乱撒过尿,我觉得听着怪不舒服的,就立起身来告辞。
"开船不是还早吗?——我预备在镇海住上几月再回南京,那时当再来看你们。保儿那时也许会跑了,再不必老叫人抱得臂酸。你的女儿几时断奶?我希望下次能看见这个小天使。"
"小天使!"我不禁轻轻嘘了一口气,独处离开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