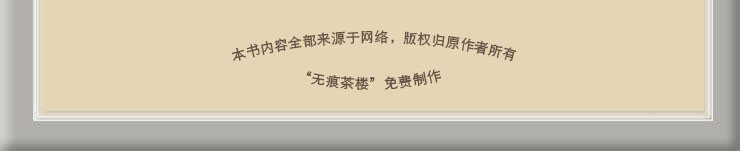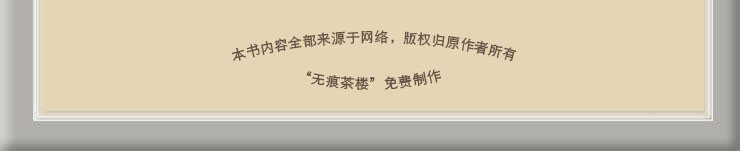|
乘滑轮车远去
|
|
在风行滑轮车的年月里,十八岁的猫头一直是街上少年所崇拜的英雄,猫头是制作滑轮车的大师。那时候在我们街上吱扭扭横冲直撞的滑轮车有二十余辆之多,它们几乎都出自十八岁的猫头之手。
猫头个子很高,腿与手臂很长。猫头的眼睛像他母亲一样的乌黑发亮,猫头的鼻子像他父亲一样的挺拔威武。就这么回事。猫头实际上是一个小美男子。我的两个姐姐都这么说。说他以后肯定能找一个上海姑娘结婚的。
所以我不相信那天看见猫头干的下流事是真的。
那天是九月一日。少年们秋季入学的头一天。我在铁匠弄里的红旗中学上高一了。早晨的时候我决定把黄书包收起来,采用另外一种上学姿势:把所有的课本笔记本夹在腋下,这是我们街上高中生和初中生小学生的区别。你必须遵守这种街规,你要是在我们街上长大,会懂得这种街规比学校的校规重要得多。
我一出门就看见我弟弟在化工厂的大门外偷玩我的滑轮车,我冲他喊了一声,"停住!"他就慌了,我看着他笨头笨脑慌慌张张地放开了笼头。滑轮车驮着他的半爿屁股撞到铁质语录牌上,当。我就知道滑轮车要完蛋了。我把腋下的书本全甩到水门汀上冲过去,朝我弟弟的屁服踹了一脚,但已经来不及啦,滑轮车的四只轮子滑出了木轴,在地上乱滚一气。那时已经快上课了,中学生们走过化工厂门口汇向铁匠弄,而我和弟弟满头大汗地修理滑轮车,怎么也弄不好,你要知道我弟弟是个废物,一点也帮不上忙。后来他哭哭啼啼地说,"去找猫头吧。"
就去找猫头。猫头天天在家里。猫头不想到乡下去插队,猫头才有工夫给我们做那么多的滑轮车。我们扛着可怜的破车来到猫头家。那扇暗红色的门反锁着,四只手一齐敲门,无人答应。我弟弟说,"猫头去上学了吧?"我说,"放屁!人家早毕业了。"我想猫头早晨是不出门的,他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说不定他是躲在家里研究新式的滑轮车。我闯进隔壁木木家,我知道从木木家窗子跳过去就是猫头家的天井,而猫头的房间窗户又对着天井,可以看看他在干什么,就这样我钻到了猫头的窗前。窗开着,却垂着窗帘,里面悄无声息。我轻轻掀开窗帘一角朝里张望,看见猫头站在地板上,红裤头褪到膝盖处。猫头在玩他自己的鸡鸡。是真的,一点不骗你。
猫头怎么会干这种事?我怪叫了一声就逃开了,翻回木木家窗子。我想不到猫头除了做滑轮车还做这种事。我弟弟见我出来就问,"猫头呢?"我嘻嘻嘻笑。他摸不着头脑,又问,"猫头在干嘛?"我涨红脸憋了半天说,"猫头是个臭流氓。"
说完我把破车子朝弟弟肩上一搁就朝铁匠弄跑了。
那天是九月一日,秋季开学的头一天,但是头一天我就迟到了。
我要说的其实不单是猫头的故事。
我要说的是九月一日那一整天的事,那天的事情发生得莫名奇妙稀奇古怪,但对于我来说显得意义深远,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晰。
我气喘吁吁跑到教室门前喊报告。
教室里的混帐东西都幸灾乐祸地龇牙咧嘴地对我微笑。世界上迟到的事是天天发生的,我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要笑我。政治教师齐大胖朝我点点头说,"你还行。你还记得教室的门。进来吧。"我刚跨进教室推开半掩的门,一把扫帚一只畚箕就掉到我头上肩上。我听见教室里一片哄笑,这全是混帐教师齐大胖唆使同学干的。齐大胖一贯如此混帐。你要知道他是根本不配教马列主义政治的。
我忍气吞声地找到座位,发现邻座是女的,而且是李冬英。我的气就更不打一处来。凭什么让我跟班上最脏最丑的女孩坐?上课的时候我不断地用胳膊和腿把李冬英往外面拱,李冬英就木呆呆地往外面移,最后她差不多是坐在过道里了,我才罢休。我听见齐大胖突然抽查起毛主席诗词来了,他把张矮叫起来啦,他提问:"春风杨柳多少条?"张矮说,"万千条。春风杨柳万千条。"齐大胖又问:"六亿神州怎么摇?"张矮摸了摸脑袋,回答:"六亿神州尽舜尧。"我很怕抽查到自己头上,我的脑袋乱得一塌糊涂,眼前尽是猫头干的下流勾当。那辆滑轮车还找不找他修呢?
"哇!"木头人丑八怪李冬英忽然张大嘴巴哭嚷起来,大家都惊讶地望着她。"你怎么啦?"齐大胖走下讲台,他看看李冬英又看看我。"是不是你把她惹哭的?"我说,"我没惹她,她自己爱哭有什么办法?"齐大胖就去拉李冬英坐到原来的位置上,李冬英却僵硬地仰着头,夹紧了双腿依然大声哭嚎,有人突然惊叫,"哎呀,她流血了!"低头看她坐的椅子,果然有血,紧接着我的头被齐大胖敲了一记,"又是你干的好事,给我滚出去。"齐大胖一边怒骂一边把我揪出来朝门外推。我让李冬英搞迷糊了,愣头愣脑地出了教室。站在窗前听着李冬英哭了一会儿又戛然而止。
我想今天碰到的事情都出鬼啦。但是不让我上课也没什么可伤心的。我沿着学校的围墙走。九月的阳光在头顶上噼噼噗噗地奔驰而过。有一只小白色从围墙的窟窿里钻进来,在草丛里蹦蹦跳跳的。那只兔子的眼睛像红宝石一样闪闪发亮。我撒开腿去追兔子,兔子就惊慌地逃了。我也不知道追兔子有什么好玩的。问题是你不迫兔子又有什么好玩的呢?
最后兔子被我撵到围墙尽头,那是个死角,一边是学校废弃的旧仓库。那只兔子就呆呆地蹲在墙角,神态活像该死的李冬英。我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了兔子,我看见兔子闭了下眼睛,随后发出了一种很奇怪的轻微叫声。它在我的手里一动不动,显得老实而驯顺。我试着松了松手看它跑不跑,它依然不跑。我觉得那只兔子真是像透了木头人李冬英。九月的阳光在头顶上噼噼噗噗地奔驰而过,兔子的皮毛摸上去温暖舒服。我从兔子身上狠狠地拔下一把兔毛,放开了它。
问题还是出在兔子身上。那只该死的兔子有钻窟窿的癖好,我看见它逃走后又从旧仓库的大门窟窿里钻了进去,紧接着我听见旧仓库里发出一个女人的惊叫,紧接着是破桌椅乒乒乓乓地倒在地上,我跑过去扒住大门,跪在地上,低下脑袋从窟窿里张望,我先是看见了纠缠在一起的四条腿,然后我又看见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我们学校的江书记,女的是教过我们唱歌的音乐老师。
这又是怎么啦?
我的手里抓着一撮兔毛。在阳光下兔毛温暖而柔软,发出雪白的光泽,我举起那撮兔毛仔细地看了看,一边走一边鼓起腮帮把兔毛一根根吹走。我的脸憋得又烫又红。
放学时我是和张矮一起走的,张矮比我矮半个头,但我知道他是已经发育好了的。张矮跟你一起走路时就要勾肩搭背,但是只有他搭你的份,绝对没有你搭他的份。那天张矮就这样搭着我的肩出了校门。我要往东走回家,他却用劲推着我肩膀朝西走。
张矮说,"跟我去石灰场看热闹。"
我说,"去石灰场干什么?"
张矮说,"有人约定在那儿单甩(一对一打架)。"
我说,"我的滑轮车坏了,我得回家修去。"
张矮吸紧鼻子嘘了我一下,他说,"玩滑轮车算什么东西?我明天替你砸了烧炉子。还是跟我去石灰场吧,"
"谁跟谁?"我问。
"猪头三跟癫八,"
我嘀嘀咕咕地跟着张矮朝石灰场走,石灰场是以前建筑队烧石灰的地方,现在窑已倒塌,成了一片空地,是街道开群众大会和少年们决斗的好地方,我们走到石灰场时看见里面已经聚了好多人,有认识的,也有陌生的,你一见他们就知道个个是狠客。我靠在一堵断墙边不走了。
"不是单甩。"我说,"你他妈骗我。"
"单甩不单甩的都一码事。反正要放血。"张矮笑了笑,推我,"进去呀!"
"我先在这儿看看。等会儿再说。"
"好吧,等会儿再说。"张矮又勾住了我的肩膀。
原来是群架,我分不清那一大群人谁是猪头三的人谁是癞八的人。猛听见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怪叫,紧接着那些人影就急剧地波动开了,他们跳跃着碰撞着怒骂不绝,相互殴打,在正午的太阳下仿佛奔马嘶鸣,蔚为壮观。
"恐怕猪头三打不过癫八,他眼睛开花了。"我说。
"你懂个屁。猪头三后发制人,"张矮说。
石灰场里的形势正如我判断的,猪头三快顶不住了,我看见他的人马有几个偷偷溜了出去,这时候张矮开始紧张地喘气,他的手臂勾住我的脖子快把它勒断了。我对他说:"你快松松手。"张矮盯着猪头三根本没听见。张矮眼睛绿了一下,突然推了我一把,"上,我们上!"
"我们上?我们帮谁?"
"当然是猪头三,他是我师傅。"
"我不想上。"我抓住了一棵树枝,抛开张矮的手说,"我要回去修滑轮车了。"
"你敢不上?"张矮瞪着鬼眼睛,"你今天不帮我忙明天我踩你肋骨。"张矮说完大吼一声跳过断墙朝癞八扑过去了。
我这才明白张矮是带我来打架的。张矮已经悄悄地加入了猪头三的队伍我事先一点不知道,我看见瘸八不屑地微笑着躲掉了张矮的扑击,然后抬起那条著名的弹簧腿朝张矮的下巴踢了一脚。张矮的脸一下子就变形了,他的下巴脱臼了,张矮站在人堆里捧住下巴,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神绝望而愤怒。我忽地打了个冷颤,转身朝铁匠弄跑去。我想这不能怪我,张矮的下巴是癞八踢掉的不关我什么事。
我在铁匠弄拼命奔跑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那只兔子被迫逐着拼命奔跑。
按照时间顺序,下面该讲到九月一日的下午了。
九月一日的下午我没去学校,我一直在家里鼓捣修理滑轮车。我父母都在家。母亲找出一捆红绒线,让父亲伸出胳膊把线绷紧了,她就开始团线。他们夫妻两个配合默契,母亲像幼儿园的阿姨,父亲像幼儿园的好孩子。
从下午开始隔壁的疯女人一直在哭嚎,时断时续。疯女人的哭嚎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一家已经习惯。每当隔壁鸡犬不宁时,母亲就要批判疯女人的男人,"谁让他色迷心窍。要找漂亮的漂亮的,不漂亮的不要。好,总算找到了漂亮的。漂亮的又是疯的。"这番话包含着某些哲理。但我觉得有些颠倒是非,好像发疯的不是那女人而是她的男人小孟了。
疯女人在漫长的哭嚎过后总要从孟家后门冲向河滩,这也是习惯。据说疯女人都是喜欢溺水的。然后小孟就追出来抱住疯女人杨柳般的腰肢,把她拖回家。以往都是这样,但九月一日下午有所不同。我看见疯女人半裸着上身,举起双臂朝水里走,肮脏发黑的河水已经没到了她的腰肢上。小孟却还不出来救她。我尖叫起来:
"她要淹死啦!"
母亲边缠线边说,"小孟怎么还不出来?"
父亲回答说,"小盂恐怕起杀心了。"
我看见疯女人越走越深,现在她丰满洁白的乳房像睡莲一样飘浮在水面上。她举起双臂就像吴清华被缚在椰子树上。我浑身的血突然一热,"我去救她!"我这样喊了一声就飞步冲向了河滩。我跳进河水里向疯女人游去。要知道在水里救人是很讲究技巧的,你不能去抓溺水者的手,而要抓她的头发,你要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把他拎到岸上,否则大家一起完蛋。我抓住了疯女人的头发就往回游,没想到她一下子抱住了我,贴在我的身上。"放开,别抱我。"我吓白了脸,但疯女人是不管你的技巧和安全的,她光滑的身体像条鱼一样啄着我,充满了危险的热量。很快地我也成了溺水者,如果不是我父亲及时赶到,我就随疯女人一起到东海龙王那儿厮混了。
我和父亲浑身精湿地把疯女人推到小盂家后门。我要说那个疯女人确实美丽绝伦,在岸上我不敢再看她半裸的身体了,我父亲对我说:"背过脸去。"我就背过了脸,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了。
小孟的脸在后门黑黝黝地一闪,把疯女人往里一拽,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他连"谢谢"都没说,这实在不懂礼貌。我和父亲救了他老婆,他却砰地把我们关在门外了。依我看小孟根本不配活在这世界上。
我在房里换衣服的时候,听见有人走进了我家,听声音是猫头他妈。她急速地跟母亲说着猫头怎么猫头怎么的。我就隔着一道门板问:"猫头怎么啦?"
"正要问你呢:"母亲说,"猫头不见了。"
"猫头怎么不见了?"我说,"他不见了关我什么事?"
"猫头跟他妹妹说,他要找你算帐,"猫头他妈敲了敲门板,"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猫头上哪儿了吗?"
"算帐?算什么帐?"我很惊奇,突然想起早晨的事。也许猫头知道我看见了他干的下流事?我考虑了一下就大声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他干的事!"
我很恼怒,早晨的事难道能怪我吗?猫头凭什么找我算帐?我还有点害怕。猎头毕竟是猫头,他既然要找我算帐就早一点吧,他怎么又找不见人影了呢?
夜里街上大乱,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像拉起了警报。我跑出门外,看见街上到处是人。一辆三轮车慢慢地经过人群,骑车的是猫头他爸,猫头他妈坐在车上掩面大哭。我看见猫头满身血污躺在三轮车上。原来是猫头死了,我头皮一麻,目瞪口呆。
"猫头怎么死了?"
"让汽车撞了。"
"猫头玩滑轮车,钻到汽车肚子里去了。"
我追着那辆三轮车。我看见猫头的脸被一块手帕蒙住了。他被汽车辗过的长臂长腿松弛地摊在车板上,我看不见猫头的脸,但我看见了猫头自己的滑轮车堆在他的身边。昔日街上最漂亮的滑轮车现在己成为一堆废铁残木。我想不通的是猫头驾驶滑轮车的技术无人匹敌,他怎么会让汽车撞了呢?
我最终想说的就是九月一日的夜里。那是我学生时代睡觉最晚的一夜。夜里我发烧了,我知道自己烧得很厉害但我不想对父母说。我裹紧了一条旧毯子躺在小床上,听见外面的街道寂静无比,蟋蟀在墙角吟唱,夜雾渐渐弥漫了城市,钻进你的窗子,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如果那真的是思想的话,你用一千把剪子也剪不断那团乱麻。我不知道我是否睡着了,只记得脑子里连续不断地做梦,其中一个梦我羞于启齿。梦中,我的滑轮车正在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路上充满激情地呼啸远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