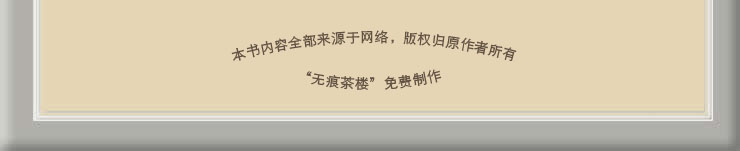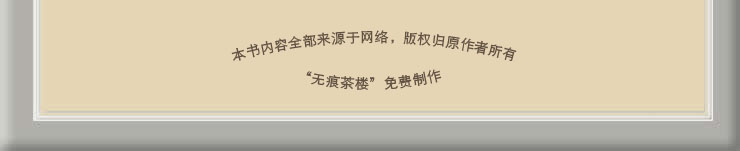|
我为什么不会写杂文(代序)
|
|
非小说文字中。我最喜欢阅读的是一些伟大的作家写出的伟大的杂文。记得以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那个著名的一口痰和一群人的片段时,一种被震惊的快感使我咧嘴大笑,自此我的心目中便有了这种文体的典范和标准。
世界在作家们眼里是一具庞大的沉重的躯体,小说家们围着这具躯体奔跑,为的是捕捉这巨人的眼神、描述它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甚至对巨人的梦境也孜孜不倦地作出各自的揣度和叙述,小说家们把世界神化了,而一些伟大的杂文作家的出现打乱了世界与文字的关系,这些破除了迷信的人把眼前的世界当做一个病人,他们是真正勇敢而大胆的人,他们皱着眉头用自制的听诊器在这里听一下,那里听一下,听出了这巨人体内的病灶在溃烂、细菌在繁衍,他们就将一些标志着疾病的旗帜准确地插在它的躯体上。自此,我们就读到了一种与传统文学观念相背离的文字,反优美、反感伤、反叹息、反小题大作、反晴蜒点水、反隔靴搔痒,我们在此领教了文字的战斗的品格,一种犀利的要拿世界开刀的文字精神。
作家如我,多年来睁大眼晴观察着世界这个巨人,观察它的眼神,但有时候它睡着了,没有眼神,我坐在它的口腔附近,能闻见它的鼻息和一些隐隐的口臭。作家如我,有时候企图为世界诊病,也准备了一把手术刀,一些标识疲病的旗帜,在这巨人的身边忙碌,但我发现我无法翻动它的巨大的沉重的躯体,我无从下手,当我的手试探从巨人的腋下通过时,我感受到巨人真正的力和重量,感受到它的体温像高炉溶液使你有灼痛的感觉,我感到恐惧,我发出了胆怯的被伤害了的惊叫。作家如我,在世界这个巨人身边扶指叹息,一筹莫展,而手中精心准备的那些五颜六色的旗帜受不了主人的犹豫和无能,旗帜作出背叛的决定,它们一改初衷,改换做了节日彩旗,发出一种类似欢迎的嗜杂声,使我的处境更加荒诞,使我的恐惧更加恐惧。作家如我,最后用一种不确定的声音指出世界患了牙周炎。听者说,我早就知道了,几乎人人都有牙周炎。我觉得额面扫地,我俯身倾听世界的内脏的声音,我听到了一些罗音,我知道世界的肺部也许受到了感染,我想把这个发现告诉别人,但听众也背叛了我,他们不告而别,而我终于发现我是白忙一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管是谁有点罗音都没什么,就医学常识来说有点罗音不碍大事,我想我在忙些什么屁事,世界睡觉我为什么不睡,于是我怀着虚无的激情躺在这巨人的脑袋边,一起睡上一觉。
人要是睡着了除了做梦,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我的梦的产量很高,所以一直没写出鲁迅那样的杂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