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身陷文字与影像的碎片
作者:于田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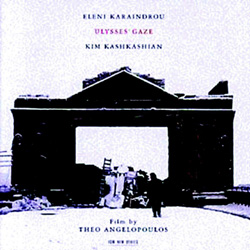
也许诗人的一生都注定陷落在一种困顿里,那是诗性与人性的困顿,是在永垂不朽和稍纵即逝之间的摇摆与彷徨。
《永恒和一天》里,希腊文豪亚历山大在妻子安娜死后,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去续写一首十九世纪未完成的诗;《尤利西斯的注视》里,导演“尤利西斯”为了上个世纪初的未完成的三卷胶片,开始了间关万里的追寻。
这是亚历山大在人间的最后一天,他身患沉疴,二十四小时以后就会走进医院——大概永远都不会再用人的目光凝视那灰蓝的海洋;
这是“尤利西斯”在经历二十八年十一部作品的导演生涯后的一段旅程,到达了终点以后他会向世人讲述他营造的第十二个故事——关于这次寻找本身的故事。
亚历山大在1998年的一天准备向人世告别,他一次次回想起1966年9月20日安娜给他的一封信,一次次重复着那一天的海岛之旅;
“尤利西斯”为多年前的女人们所诱惑,她们被扣留在电影胶片里,安静地在织机前忙碌,也许她们在传播着农庄里的谣言吧——一切无从知晓,影像里她们只是一群渺小的哑巴。
安娜在信里深情地嗔怪亚历山大,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1966年的9月20日,女儿刚刚降临人世,他守在她们的身边,却并没有在和她们一起生活——至少她是这么感觉的;那段旅程里,“尤利西斯”和三个女人的恋情,几乎概括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爱情故事:幻想用肉体之爱去催发灵魂之爱——却以失败告终;屈从于巫术般的胁迫,着魔似的被暗流卷走——醒来春梦无痕;为天使般的女孩心动,小心翼翼浅尝禁果,却是爱而不得——在冰天雪地里绝望嚎啕。身边,爱人的尸体逐渐冰冷。
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意蕴深长。
在修辞学上,它们是互文关系,可以互相成为对方的注释;作为影像,它们是一对兄弟,从相同的基因里继承着相似的血液。

同样哀悼了失落的希腊文明——不仅是那残破的庙宇殿堂呀,更是那种业已消散的豪情万丈的精神;同样是一群群的阿尔巴尼亚难民,男或是女、老或者少,铁蹄践踏、山河破碎过后,残留着相同的卑微眼神,还有麻木的面孔。十九世纪末的诗人在河边徘徊,亚历山大听到他在呼唤:“在这世纪之交希腊人应该起来战斗!”;送“尤利西斯”去阿尔巴尼亚的出租车司机对着雪野呐喊:“希腊正在死亡——希腊呀,你要死就死得快一些吧!”
毫不留情的记忆在流动,有时和缓有时奔突,注定了让亚历山大和“尤利西斯”一次次遭遇到自己的母亲和恋人。回到过去时空的他们,无一例外的,保持着现实里衰老的或正在衰老的身形。亚历山大在疗养院里对着老年痴呆的母亲:“为什么,妈妈,没有任何事情是如人所愿的呢?为什么我要过着流亡的生活,在讲自己语言的地方却找不到信心?告诉我,妈妈,为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爱?”;“尤利西斯”的列车靠站了,年轻的母亲不由分说地拉着疲惫的儿子,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新年,去完成一个一年一度的规矩:照一张“全家福”。这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大家族最后的尊严。镜头内外的“尤利西斯”眼神忧郁疑惑,他想要问母亲什么呢——不就是亚历山大的那三个问题么?
亚历山大从警察和人贩子手里,解救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小难民,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像一切人和人的关系:你进我退,你强我弱,接着突然变成了“你弱我强,你退我进”,然后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午时,亚历山大把三明治举得高高的,让饥饿的小难民回到自己身边。他反复告诉小难民他第二天要去旅行,“别缠着我”是他的潜台词;到了晚上,对着小难民离去的背影,亚历山大失声大喊:“留下来陪我!”,他顺势蹲在了地上,和小难民开始了水平的对视:“你的船还有两个小时才离开,而我只有一个晚上,请留下来!”
1966年的9月20日,亚历山大抛下妻子,独自一人爬上断崖,他寻找到1933年夏天自己在石头上刻的字迹,他高举着双臂,用希腊土风舞的手形向悬崖下汪洋中行驶的轮船打招呼,尽情享受着那无与伦比的孤独的自由;1998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和小难民同乘公共汽车,车窗外的海面上是三十年前驶过的轮船。而那艘轮船上站着的,也许就是“尤利西斯”吧,他流着眼泪告别了执著的爱人,对她说:“我哭泣,是因为我无法爱上你。”与“尤里西斯”同行的,是巨大的列宁塑像——冰冷的石头永远沉寂着,原本屹立不动,而今颓然倒下,是另一种情爱的失落。

也许,世界真的并不存在,只存在我们对它无穷尽的表述;往事真的并不存在,只存在我们对它无休止的追忆。
——仿佛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永久地停留在一种状态、一种情绪里。
那些淹没在时空尘埃里的文字和影像的碎片啊,诗人徒劳地追寻着你们:亚历山大没有续完那首长诗——尽管他竭力捕捉着空气中漂浮的一切话语,甚至向小难民收买词汇;“尤利西斯”丢失了胶片的灵魂——尽管他找到了那些泛黄破损的断章。为了那些迷人的碎片,诗人无一例外地没有珍惜爱情的欢愉——他们是否应该为了诗和梦想放弃深爱他们的血肉之躯?
在亚历山大之后,会有人继续写那首未完成的诗——所有意识创造都可以被当做一首正在完成的诗;在“尤利西斯”之后,会有人继续拍那些未完成的影片——一切艺术创作都可以被看成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诗人永远会把精神创造视为通向天国的路径,而忽略了最亲近他们的人的渴求。
临别时,亚历山大问小难民:“告诉我,明天会有多久?”小难民回答了一句阿尔巴尼亚语——也是卖给他最后一个词汇:“阿拉维尼。”阿拉维尼,就像我们一生中稍纵即逝没有结果的恋情,就像那些飘散在风中的眼神和话语。阿拉维尼,它的意思是“太晚了”。
亚历山大最后来到海边的旧居——女婿已经准备用推土机把它铲平,就在明天,古老的房子将和亚历山大一样成为历史。幻想里,亚历山大问安娜:“明天会有多远?”
安娜笑着跳开一步,回答丈夫:“永远或一天!”
——或许,我们向往飞翔,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翅膀。也许,矛盾的产生只是选择的不同,无关善恶。
附录:
《永远和一天》(希腊)(汉译名:《一生何求》),导演:提奥·安哲罗普洛斯,199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尤利西斯的注视》(希腊)(汉译名:《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导演:提奥·安哲罗普洛斯,1995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