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昆德拉与我们的“神经”
作者:仵从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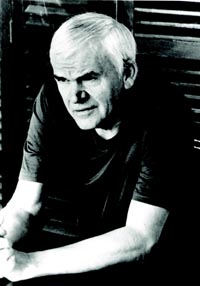
昆德拉自1985年为中国读者知晓、1987年后为广大的中国读者阅读,转眼已近20年。这20年间可谓是昆德拉热读热说热卖。此热迄今余温犹在之时,因上海译文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首批7种)”2003年4月的发行,使昆德拉与读者又一次见面,致“昆德热”甫息又起。“热”本已有趣,“热”后而又“热”就更加有趣。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昆德拉,你触动了我们那根“神经”?
路德维克,你也有中国兄弟!
始于1962年、成于1965年、出版于1967年的小说《玩笑》是昆德拉最早的长篇,也应该是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长篇之一。《玩笑》在涂抹上“内部发行”与“作家参考丛书”的保护色后于1991年进入了气氛肃然的中国。这本书的主人公路德维克与小说的标题有关——身属大学生的他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上玩笑式地写下了如下的话:“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健康思想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然后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60年代斯大林主义背景下的东欧国家捷克。这是一个充满杀机而决不可“玩笑”的时代。一个人在不可玩笑的时代不得体地开了时代一个玩笑,趾高气扬的时代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于是,路德维克的命运便因这一小小的举动铸定:被批判、被开除、被发放矿区惩戒营劳教——他的一生毁掉了。一句玩笑的代价便是悲剧的一生。无独有偶,《玩笑》也有“中国版”,路德维克,你也有中国兄弟:在190期《新闻周刊》上,编者用一个版面的规模讲述了一个比路德维克年令更小、遭遇更惨的中国少年的故事:“一个80年代的高中生,仅仅因为在一张刊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随手写了几字戏言,便被有关部门认为他对时势不满,故意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以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2000年7月,他才得以平反”(引文见2000年9月14日《南方周末》第15版蒋少虞文:《小鬼的舞蹈》)。我想,当这位蒙冤17年的中国少年读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当读过《玩笑》的《新闻周刊》的编辑接到关于这位中国少年的稿件、当我们读过《玩笑》之后读到如上的报导,我们最大可能的反应是被强烈地“触动”了——昆德拉用他的笔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此处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思考。我知道,我也相信,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象路德维克式的“中国少年”遍布各地,他们的故事也小异大同。大家面对的是共同的处境、类似的体制、相仿的意识形态,因此也便有了一支同时代开“玩笑”而被时代“玩笑”的队伍。
自然,路德维克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玩笑》内容的全部,但它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冷峻也智慧的昆德拉装进了历史的记录、习俗的画卷、政治的反思、命运的哂笑、阴郁的怀疑主义和他思想的透明晶体。对我们,它有太多的亲切与酸辛、太多的提示与质询。尽管昆德拉说这只是一本“爱情小说”,是“一本讲述强奸的书,一本自身也时常遭到强奸的书”,一再申明“请不要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来难为我了”,但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把小说的时间设置在那动荡、紧张的20世纪60年代?谁让你把人物的故事与命运设定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东欧?而且你原捷共党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苏军占领捷克后的被迫流亡者的身份又何一无“政治性”?昆德拉先生,这实在由不得你了。何况,我们——中国读者——又是具有自己的经历与体验、也正在回首历史的困惑与思考中的“主体”,因此我们也只好委屈你的确真诚的一再表白了。
雅罗米尔:布拉格街头的“红卫兵”
我发表于1996年的长篇论文《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中,有一条关于雅罗米尔的注释:“这也许是解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角度。”当写下这个句子时,雅罗米尔、中国的“红卫兵”或自以为是的青年“革命者”在我心中是三位一体的。

雅罗米尔是昆德拉另一名作《生活在别处》中的“一号人物”。他在母亲无限的温情与浪漫主义的诗歌浸泡中长大。他正在充满热情、想象也天真单纯的青春时代。他年轻的肉体与心灵都极为敏感。他相信“生活在别处”。他寻求“在别处(的)生活”。他极欲得到世界与人的“承认”。他渴望富于意义的“行动”。但非“青春时代”的昆德拉知道:青春时代的雅罗米尔是了无经验的。当无经验的青春进入人群、政治、时代和历史时,便潜在了一种可能的悲剧或危险。雅罗米尔踏上并持续着自己的旅程。为了得到“男人”的证书,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求“性”;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与意志,他对离经叛道的艺术表示尊崇;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他揭发了情人的弟弟的“叛逃”阴谋,充满自豪感地走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大楼。他果然受到了政治的嘉许,接受了检举“文人”中的“捣乱分子”的责任。阴鸷的历史张开了狡黠的巨网,一条带着崇高感与责任感的“鱼”兴冲冲地游了进来。他骄傲地想到:“这不是由外部的权力强加的,而是人们为自己创造、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类的勇敢和尊严。”这是个昆德拉以为(我们想必也同意)的可怕的时刻:虚妄的激情、无经验的青春与这二者可以酣畅表现的理想场所——“革命”——遭遇了。其可怕在于:他(们)在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中生成着“罪恶”。坦率地说:在阅读《生活在别处》时,作为过来人的笔者眼前不时晃动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关于“红卫兵”,“青春无悔”之说自然是依然的浑噩,而指令其“忏悔”,实在又是见木不见林的朴素的浅薄。十几岁的他们(当然是作整体观)当年不正如雅罗米尔满怀真诚且神圣的激情投身于时代的“革命”嚒?他们由衷热爱伟大的领袖和领袖的“学说”,他们可以与至亲之父母划清界限、可以与至近之同学亲友势不两立、可以身负行囊重走“万里长征路”、可以以青春之躯战天斗地不畏艰辛。他们中有不少的人甚至在(武斗中)死去时仍口诵“革命经文”。他们与雅罗米尔同样或雅罗米尔与他们同样:为历史所欺、为青春所骗、为激情所毁。雅罗米尔们在疯狂中伤害了他人,但同时更深重地伤害了自己。他们是邪恶历史手中的工具。然而,昆德拉的思考更深:“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换言之,每个人都有与青春或激情年代相伴的“恶”。它在潜态中蜷伏着,如魔瓶等待着被时代或“偶然之手”打开——布拉格街头的雅罗米尔与北京街头的红卫兵,他们都共同遭遇了“革命”或“偶然之手”。智慧的昆德拉以他年轻的雅罗米尔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存在”的秘密:青春是无经验的;但无经验的青春却是有激情的;有激情的青春在心理上最具可能的维度是渴望绝对(想一想雅罗米尔对“此处”的拒绝与红卫兵的“横扫一切”);当无经验的青春和渴望绝对的激情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革命年代”)邂逅时,“恶”或“灾难”便要发生了。
用这样的思路去想历史上激进的“革命”、激进的“革命青年”、破坏欲与破坏性极强的“革命组织”以及我们既亲切又痛切的“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有门开一隙之感?
搭车女郎:我们共同的“秘密”
“性爱”,是昆德拉小说的一大话题。扯远一点说,也是人与文学的一大话题。是人便会有性爱。有文学便会有性爱——除非有强暴的外力(如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与中国“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文学不能有性爱的表现。往日我们习惯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其实是把性爱文饰之后的表达,因为当我们谈到“爱情”时,一般的理解当然是指发生在异性之间的爱悦,也就是说,“性爱”乃是以物质性作为基础或先决条件的,性之爱乃是其本质性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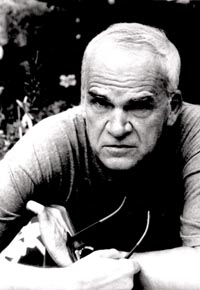
虽然性爱是文学共同也恒久的话题,但中外文学中关于这一话题的“说法”却大有差异。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自然、优美的诗性故事;但在《十日谈》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关于性爱直露、狎玩的喜剧性场景;到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类作家笔下,性爱的主人公和他们的故事又显得庄重高贵,几近于圣洁;至于小仲马之类浪漫派作家,性爱则充满热烈、伤感、绚丽的色彩;而独立特行的劳伦斯另树一帜,他在那里全无遮掩地写性爱、性事甚至性器,却满篇充盈崇敬而赞美的诗意。从中国小说看,也是类型各异:远有《金屏梅》之类的肉感、《红楼梦》之类的优雅;近有《废都》之类的放纵、《黄金时代》(王小波)之类的自然等等。差异归差异,上述小说的含义却或是写性爱的美好、或是写人性的复杂、或是写命运的不测、或是写社会之黑暗。回到我们的话题:昆德拉写“性爱”与他们不同。昆德拉要探讨我们生存深处的又一个“秘密”:“性爱”的“处境”或“性爱”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他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1963)是一个极形象的诠释:
一对外出度假的情侣在开始旅行后,无意间进入了一场游戏——互不相识的搭车女郎与司机之间彼此调情逗趣。这位少女对于游戏过于“投入”,渐渐地,她竟由一位平时显得羞怯、腼腆的率真少女变成了一位言语放浪、举止轻狂的卖笑妇。深有意味的是,在这一渐变的过程中,她体味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快感。这快感既是心理上的,更是生理上的。而“司机”虽则不时仍依“男友”的身份观察她并觉得恶心,但姑娘的淫言浪语仍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与快感。于是,两个完全自由、放荡的肉体在施与受的快乐中达到了交合的完美。“两个陌生的躯体在床上合作得天衣无缝。这正是姑娘梦寐以求的境界……她沾沾自喜,心里甜滋滋的。在这遥远的疆域,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用弗洛依德的“词”来说:以现实原则行事的自我隐退了,以快乐原则行事的原我出现了。这是寻隙而出的自由情欲的辉煌时刻。然而戏剧性的结局是:云癫雨狂之后回到现实,回到自我的身份,喜剧转变为悲剧——小伙子不能再接受他曾经爱过但已见过她“放荡”一面的恋人;少女为自己的作为充满莫名的愧悔与悲哀。他们既不能在精神上相爱如初,也不能在肉体上交欢如昨。
昆德拉在这这个当然是虚构也当然是真实的故事中向我们揭示的“性爱”的“秘密”是:性爱(情欲)的本性是自由的;它在人生存的现实处境中受到了“理性”力量的压抑,被迫进入了潜在状态,但它存在着;被压抑的性爱(情欲)是不自由的,不自由便有痛苦,因此,它要在或它会在某个适当的时机(或时刻)破门而出(我们的“过失”或“罪孽”常与之相关);但矛盾的是,自由的性爱实现之时(如在游戏中的男女主人公)却又恰是其“现实关系(秩序)”破坏之时,而“破坏”又必招致痛苦(如小说的结尾所表现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在“自由的性爱”与“压抑的性爱”二者之间我们两难。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境遇”。
怀疑主义的昆德拉的结论是悲观的。孔夫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之叹也未见乐观到哪里去。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结论,问题在于:我们理想中的“性爱”之路,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