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昆德拉——十分失望
作者:雅克-皮埃尔.阿梅特

小说:一个流亡者能否回到自己的故乡?米兰·昆德拉用《不知》(L'ignorance)来回答。一部重要作品。
1975年,米兰·昆德拉和妻子维拉(Vera)来到法国。他们出现在伽里玛出版社的客厅时,他穿着羊毛套衫和牛仔裤,她头戴高帽、鬈发拳曲,仿佛来自一部捷克黑白电影,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十分惊讶……《玩笑》的作者和维拉显出腼腆和好奇的样子,感到不知所措,活像两个逃学的中学生。他们的肩上留有布拉格之春的花粉。这作品迷人的米兰,高个子但又灵活,有一张雕像般优美的大脸,犹如年轻的拳击手,看到他,大家都在心里提出疑问。他写了《玩笑》,辛辣地讽刺共产主义的空想,书中有一个女人的形象,如同出自福楼拜的手笔。他们夫妻俩来到出版社,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搭车旅行的年轻人,手拿旅行包,对这样隆重的接待感到意外。他们来自铁幕后的野蛮世界,包里带着一本杰作……大家都在想,这对夫妻是否只在巴黎逗留几天,巴黎是否只是去美国之前短暂停留的地方。
现在,昆德拉及其妻子已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八年。他们之间说的是捷克语,他们说狄德罗在我们的作家中声誉最高。仔细阅读过昆德拉小说的人都知道,来到法国是他作品的关键时刻。
一生的界限就在这里,什么是流亡?一种痛苦。在流亡中,世界变成“动荡的黑暗”,这是另一位流亡者雨果的话。
1989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想,这位作家是否会回到他那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故乡。他想必每天起身时都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用《不知》来作出回答。
这本书使我们感到意外
这本书说的全是痛苦和流亡,共有58章,都十分简短,直言不讳,给人印象强烈。书的主题简单:流亡者的回归。昆德拉塑造了两个人物: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年的伊雷娜(Irena)和生活在丹麦的约瑟夫(Josef)。两人在书中走的是平行的路。他们将相遇在书的末尾一个嘻嘻哈哈的暗淡场景之中。前面几章有出人意外之处。其中谈到希腊神话(奥德修斯和伊塔卡)、语史学(retour(回归)这个词在欧洲语言中的词根)以及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这像历史散文?像杂志社论?像讲座?像个人沉思默想?像私人日记?像杂乱无章之作?
一页页看下去,你会发现,昆德拉把他的人物和感想置于赋格曲式庞大音乐结构之中,要知道他父亲是钢琴家和乐队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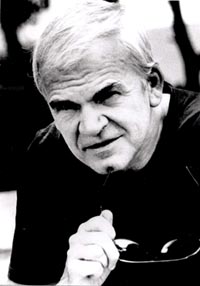
没有叙述的任何愿望。他的故事波澜起伏,活像一出闹剧。你注视着伊雷娜和约瑟夫所走的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例如,约瑟夫住进一个旅馆,是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几年里。那是黄昏时分。他观赏着他二十年前熟知的地方。他到了那些地方,一点也认不出了。“当他不在时,一把无形的扫帚在他年轻时代的景色上扫过,扫掉了他熟悉的所有东西”;这把扫帚,是这部小说的通奏低音,是它的痛苦和毒药……你想象一下,奥德修斯踏上自己的岛屿伊塔卡时,发现岛上建起了高速公路、汽车停车场和商业中心,而他在离开时,那里只有凉爽的树荫和放牧的羊群,他会多么忧伤……约瑟夫的感觉基本上也是如此。
我们的时代飞速发展,使城市和农村大大改观。在1944年的地毯式轰炸之后,混凝土建筑物面积扩大。近年来,欧洲到处是建筑工地,以适应有车居民的需要。书中有许多场景,如果单独分开,显得十分美妙。伊雷娜想要有语言实践的机会,希望说法语能脱口而出。有个场景引人发笑,那是在波希米亚的一座公墓里,一家人在墓穴里重逢,仿佛在九泉之下,死人也要像活人那样感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痛苦。同自己讨厌的一个亲戚的尸骨,一起待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我也很喜欢读那高中生的私人日记。他成年之后,想不到自己曾是傻头傻脑的青年,也无法想象,他房间里有过性交用品,他同把雪当作裹尸布的热情女中学生的自杀有关。
因此,使一个人眩晕的各种事情,同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了起来。所有的事都相互呼应:遇到一个兄弟和寻找一座公墓,重新得到一幅古画和对自己衰老身体的剥夺。
读者仿佛听到了回到故乡时伊奥利亚的优雅歌声,那是对他们的补偿。人们发现,他对过去只有一种巨大的痛苦,对故乡的迅速变化只是感到十分惊讶,而留在祖国的人们和离开祖国的人们之间,只有令人难受的误会。
希望的这种巨大破灭,包含着某种十分可怕、令人心碎的成分。这同福楼拜非常相像,福楼拜触及了住在令人厌倦的诺曼底市镇—永镇的包法利夫人的思想深处。在流亡中长期反复思考,走着奇特的路,但通往的并非是失去的天堂,而是路面上一个个大坑大洼。
这本书使我们感到不快
这本书具有某种风格,故意写得十分平淡:像洗手池那样白净。昆德拉致力于确切、有条理和几何图形般的美妙结构。他玩弄的是事件发展的迅速、它们之间的相互呼应以及对别人的伤害和受到的伤害。很少有书给人以结构如此规则的印象。

人的内心深处完全被裸露出来。这种毫不宽容的态度,如同帕斯卡在描写不信神的人的痛苦时最为阴郁的“思想”。在《不知》中,你会跌入恶劣存在的泥潭之中。这尖刻的散文,使我们看到荒谬的场景,例如你躺在床上,老年人的性欲会因粗话而唤起,而粗话最终带来的则是在下流的粗俗中找到的母语的安慰。昆德拉的这本书有粗俗之处,可以说是一种洗劫、一种狂怒。用穆西尔(Musil)的话来说,伊雷娜和约瑟夫漂浮在“反常的空虚”之中。就像被子能御寒一样,抵御即将来自坟墓的寒冷,用的是合在一起称之为一本书的那些纸张。
极好的忠告!对记忆的思考主宰着《不知》,最终构成它的中心——空虚的中心。弗洛伊德向我们揭示我们行为的动机,使我们受到恋己癖的创伤,米兰·昆德拉使我们承受的是同样痛苦的真实。
我们这些不幸的读者,裹着普鲁斯特的漂亮披肩,以为记忆会向我们展示非常美丽的乔木,却从高处掉落下来。
过去,是真正的圣诞小树,照亮我们老年的岁月,可昆德拉却用斧头将它修剪。这忧心忡忡的笑声无法忍受……作者低声对我们说,我们的往事有局限性,数量又少,十分乏味,就像留在门厅五斗橱上的一张即时成像的照片,平淡无奇,任何人都拍得出来。这也是极好的忠告……
昆德拉从不隐瞒他属于中欧极其失望者之列:卡夫卡、穆西尔、布罗赫(Broch)。特别是非常伟大的[视野广阔的]布罗赫。这些作家感到,奥地利帝国在颤抖,欧洲的价值在崩溃。有趣的是,这些作家被纳粹德国驱逐或排挤,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如昆德拉的结论痛苦。我们得要思考。
昆德拉是极少数作家之一(也许跟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一样),在分析当今这监狱般的悲惨世界中的眩晕。就是使人苦恼的弗洛伊德所说的“令人不安的奇特”。
这本书使我们感到苦恼
相比之下,法国作家像在孩子房间里打弹子。他们喋喋不休,在销售情感的可爱圈子之中!
法国有部分文学批评,对他以前的故事里那种论证性的、干巴巴的、令人沮丧的自然主义感到困惑,现在仍觉得不知所措、犹豫不决。有些记者墨守常规,对这种“悲伤的知识”新颖的无调性感到愤慨。但是,现代忧郁的历史,应该将此书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