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痛,故我在
作者:张 秋

《切肤》(In My Skin)的极度嗜血,让我马上想到了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is)编导的《日烦夜烦》(Trouble Every Day)——只不过一个是吃别人,一个是吃自己。自编自导自演该片的法国才女玛莉娜·德·凡(Marina de Van),是名导弗朗索瓦·奥宗(Francois Ozon)的《八美图》(8 Women)和《沙之下》(Under the Sand)的编剧之一,她的两颗大门牙间黑漆漆的裂缝,和《日烦夜烦》的女主演、“巴黎野玫瑰” 帕特里斯·黛尔(Beatrice Dalle)竟也是如此的不约而同,很适合吸血和撕咬。
在《沉默的羔羊》续集《汉尼拔》(Hannibal)里,联邦特工被打开了天灵盖,安静地端坐在餐桌旁,“食人博士”安东尼·霍普金斯,优雅地从里面取出一小块大脑,然后煎炸三分熟,再送进他自己的嘴里。博士就是这样不容挣脱地控制着你的肉体和思想,他吃你已经是小菜一碟,他还能让你吃自己,吃完还说味道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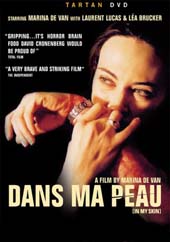
《切肤》里艾瑟的自食,却是未经任何医学处理的自觉行为,是对身体的一场“自我探险”。探险的起源,始于一次意外摔跤造成的伤口,它虽然已经愈合,但那一截腿却失去了痛感,好象不属于自己了。这一切同时也是玛莉娜·德·凡自己的亲身体验,于是她开始追问:我是通过我的身体存在于世,并和外界发生联系,但如果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的,那我是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愿望:想看看身体到底是什么,以及我是否还在里面。”
慢慢慢,且慢,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老家挨着沪宁铁路,上学时我经常沿着铁轨中间的一级级枕木快乐地行走,就像电影里一样,可惜有一次眼前一花,一脚踏空摔断了左臂,在接骨的民间庸医手上受了点折磨之后才去了医院,石膏在手臂上绑了很久,拆开那天,医生让我试着用左手端起他桌上的茶杯,我颤颤巍巍,手好象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和自己肢体的这种陌生感、分离感,如今竟被影片激醒,且对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恐慌起来。我甚至想到了《拯救大兵瑞恩》开头诺曼底登陆战中,在海滩上捡起自己断臂的那个士兵,想到了陈果的《香港有个好莱坞》中被错认错接的两只断臂,造成一个人有两只左臂,另一个人有两只右臂……

艾瑟离开医院后发生了奇特的变异,从一开始的自残,不让伤口愈合,发展到对身体其余部分惊心动魄的自食。人的本能是回避、害怕疼痛,而新鲜的痛感此时对艾瑟却是宝贵的。假如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感觉,我还算活着吗?我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吗?这比残废更可怕。不痛,才是艾瑟“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
我们只知道艾瑟有个关心她的男朋友,她自己是个白领,对中东有研究,原来为媒体撰写评论,一切看上去很美。可后来她转行搞起了珠宝销售,虽然做的是中东市场的调研,却毕竟风马牛不相及。在餐桌上听客户高谈阔论的时候,她心不在焉地在桌子底下偷偷开始了自残。她对自己的身体没感觉,对自己的职业、感情、生活,显然也统统没感觉。她很认真、很疯狂地破坏、撕咬着自己的肉体,贪婪地吸着自己的鲜血,甚至还从牙缝里取出自己手臂上的皮肉,看个究竟之后再放回嘴里咀嚼,镜头长时间静止地自然主义地拍摄,起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结尾(当然,如果你不犯血晕,能坚持到这会的话)是开放式的:她满脸满身是血,蜷在地上,两眼像狼一样惊恐地盯着你……女主人公“探险”的代价不小,结果却不妙。

我痛,故我在。从痛中体会和发掘快感,寻找存在的证明,以及生命的意义,《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导演:大卫·芬奇)和《冲撞》(Crash,1996年第49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导演:大卫·柯南伯格)里的“撞车俱乐部”,便是这样典型的“民间极端组织”。这两个俱乐部的成员都不是社会底层的贫民,而他们却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迷失,当人被物质异化得失去感觉和方向时,痛,转而成了人们的精神追求。
在《冲撞》中,死里逃生的经历,不但没有引起驾车人对汽车的恐惧,反倒唤醒了他们的情欲和性高潮。痛,以及生死的边缘,让人感觉到了生,孤独、压抑、疯狂……在刹那间粲然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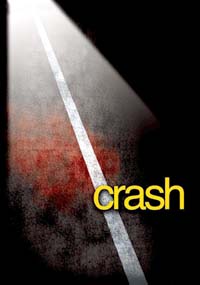
撕心裂肺的冲撞,就这样拉开了一道口子,里面流淌出的竟然是莫名的兴奋,于是伤口就像一朵异样的花,一直被刻意地培植浇灌,血淋淋地开放,永不闭合。
撞车俱乐部成员以疤为美,视残骸为艺术,以模拟撞车为娱乐,疯狂,变态,但也很high。人有时候就这样被迫回到原始,就像《29棵棕榈树》(29 Palms)中的那一对男女,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沙漠中,关于人的所有事情都还原归结到原始本能的性,和暴力。繁华喧闹的都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电影中那片叫人抓狂的沙漠。

《搏击俱乐部》里,顽固的失眠症象征着“我”的人生状态。“我”一开始出没于各个癌症团体,从毫无希望的人那里寻找希望,寻找痛苦的认同和安慰,直到后来在飞机上结识了泰勒——“我”分裂出去的另外一个人格,就开始了“斗阵”这样的残酷游戏,没有任何防护,一对一的互殴,“打过之后犹如得到了救赎”,第二天再鼻青脸肿地去写字楼上班,张着“血盆大口”和同事做鬼脸,把嘴里掉落的牙齿像垃圾一样扔进下水管道。泰勒在用自制的腐蚀性粉末烧“我”的手背时,对嗷嗷叫的“我”说:感受一下这种痛,这是你一生最棒的时刻。他传授给“我”的名言是:“No fear,No distraction。”
失眠只是一个表象,“我”真正的病症,是“想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原来的自己:老板手下的好好先生,住公寓楼,努力工作,然后受广告的诱惑,去买那些不需要的东西,一切都追求完美。泰勒开始对“我”进行颠覆和改造:“你要忘记自己所认识的人生。”他的三堂经典课程充满“人生哲理”:第一堂课是布置给全体会员的作业,让我们找一个陌生人打架,实验结果是“很不容易”,因为正常人总是避免打架;第二堂课是用枪抵住一个便利店店主的后脑勺,逼他说出自己想做什么,在得到“想当一名兽医”的答案之后,又给他六周时间去完成,否则将受到生命威胁。泰勒得意地说:“明天一定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第三堂课是在雨夜驾车快速反道行驶,然后问惊慌失色的“我”死前想做的事,“如果现在死去,对自己的一生有何评价”,在说完他的又一句名言“要放手,别想控制”之后,就开足马力朝对面的车子撞去——和《冲撞》里一样玩命的撞车,然后再松开安全带,惨笑着从翻转的残骸里爬出来……

泰勒大笑着挨打:“我还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呢”,笑到打他的人怕,他的笑比他的拳头更有杀伤力,在俱乐部里可谓“以痛服人”,俱乐部队伍也日渐壮大,最后发展到《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 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里那样的反秩序反社会,一种在交响乐“伴奏”下的破坏的狂欢。他们对于肉体之痛的挑战、蔑视和超越,揭示了潜伏于社会这一庞大肌体中更大的痛。
真正的经典电影,是一定要反复看的,每看一遍,都会撩起一点新鲜的人生感受,像《搏击俱乐部》、《猜火车》、《发条橙》这样的叛逆和异类,到我三十不立、四十而惑的当口,才仿佛忽然看出点真谛。

我并不羡慕嗜痂嗜痛之癖,也没有勇气去撞车和“斗阵”,但我羡慕《黑客帝国》里尼奥那样的分身,我就可以分一个自己出去到处穿梭,再撒点野,“母体”则留在办公室里老老实实打卡上班,看稿子,挣工资,还房贷,至于拯救世界,那不是我的事——这充满战争和破坏的人类世界需要被拯救吗?沃卓斯基兄弟最后是有一点疑问和悲观的。而在虚拟和现实越来越相互交叉的时候,肉身的感觉便越来越重要。有人在虚拟中分辨和寻找现实,而撞车俱乐部是在现实环境里执着地创造着虚拟,他们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刺激的生存空间,用自己的方式——机械的冲撞和肉体的冲撞,来进行相互间的交流;搏击俱乐部也是一个真实的虚拟,他们同样“活得不耐烦”,用大白话讲甚至可以说“找抽”、“欠揍”,竟然以鲜血、生命为代价“作践”自己的身体,但变态、极端背后的挣脱和反叛,或许正是我们这些“很不容易打架”的所谓正常人所缺乏的。回到开头《切肤》的问题:我还在我的身体里吗?我的身体是否已经或正在沦为皮囊和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