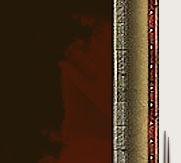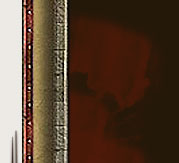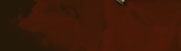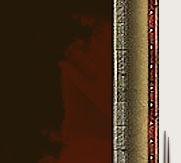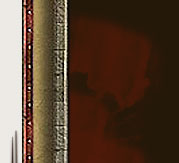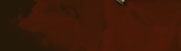| |
|
 |
|
一个黑点出现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广岛上空没有一片云彩,飞机孤零零地向前飞着。它愈飞愈近,其不寻常的外表引起了居民的惊讶。根据学者们的请求,飞机被漆成象征希望的绿色,机翼下面画上了白色的鸽子。一丝风也没有,城市在日本温和的夏日里安睡着。
洛斯阿拉莫斯的重要物理学家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卢士奇声称他需要所有的助手。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只有一个操纵杆,压一下就会自动引起一连串的作用,但是他感到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力拒绝朋友们分享最后的光荣。大家都热切地希望看到最后的胜利,这是多年超人的努力的最好报酬。只有爱因斯坦没有来,他的高龄和身体不允许他作高空飞行。他通过一部无线电话同飞机保持联系。
“让他们自行其事好了,”总统对军事指挥官们说,“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学者的事,我们懂的不多。我们感兴趣的是结果。”
机组人员被要求按卢士奇的指示行事,不管是些什么指示。因此,当卢士奇命令驾驶员降到广岛上空几百米,围着城市绕几圈,并摇动机翼以让白鸽在阳光下闪烁的时候,驾驶员并未表示反对。他服从了,只是说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然而卢士奇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他心里知道防空大炮不会采取行动。
他的本能没有欺骗他。日本人没有开火。看到这架孤零零的绿色飞机,上面画着奇怪的鸟儿,他们还以为是什么幽灵出现了呢,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飞机已经转了好几个圈子,罗莎看见了那挤满人群的街道,他们并未显露任何恐惧的迹象。
“你看,昂里科,”她说,“他们猜到了,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果然如此,似乎由于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飞机上的人把他们的兴奋和热情传给了下面的广岛人民,居民们瞪大眼睛望着天空,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看吧,都看看!睁大了你们的眼睛看看,”卢士奇叫道,他紧张到了极点,好像地上的人群能够听见他的话似的。
不过他立刻平静下来,他必须保持镇定,才能领导一系列复杂的操作。他命令驾驶员把飞机升到四千米,飞机庄严地打着旋儿飞向高空。
“时间临近了。”阿尔玛依声音颤抖地说。
卢士奇抑制住心跳,把聚能器放了出去,聚能器坠在一个小气球下面,立刻在空中飘浮起来。飞机围着它绕着大圈子。
斯波尔抓起他们与爱因斯坦联系的电话,低声地喘着气说:
“到时候了,老师。”
爱因斯坦的声音在麦克风中震响,异乎寻常的冷静,这与弟子们的激动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毫无担心之感,实验只能证实一个正确的理论。”
卢士奇这时用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对他的妻子说:
“罗莎,多亏了你,我才能顺利进行这些研究。对于即将“发生的伟大奇迹,你的贡献和我的一样大。由你来压下操纵杆吧。”
“不,昂里科,一切光荣都属于你,尤其是这个。”
“可是,你没看见我不能压吗,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吗?”卢士奇几乎是在哀求了。
他倒在一张椅子里,一动不能动。学者们个个脸色发青,瘫在那儿,和他一样地激动得要命。他们用尽全身力气说出这么几个字:
“你来,罗莎!”
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有些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更为坚强。罗莎果断的压下操纵杆。立刻,一个扩音器开始一秒一秒地数着:
“十、九、八、七……”
卢士奇终于用手做了个绝望的动作。驾驶员明白了,把发动机关上。飞机开始静静地滑翔,约翰·阿尔玛依极瘦的脸愈发显得瘦削,斯波尔也形容大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六、五、四……”扩音器响着。
卢士奇紧紧抓住罗莎的肩膀,强迫她把头靠在舷窗上,挨着他的头。
“三、二、一……零!”
往昔,当原始原子突然爆炸的时候,天上一定是高奏喇叭致敬,庄严地表示宇宙初开;于是,扩音器也庄严地宣布了人类才智开创的新时代的零时间。然而,这人类的创造却没有任何声响伴随。恰恰相反,静谧无声,一种比最骇人的喧嚣还要给人印象深刻的静谧充满了广岛晴朗的上空。
飞机继续静静地滑翔着,空气凝滞不动。机舱里无声无息。在新时代的最初几分钟里,自然的沉默和冷淡显得如此固执和咄咄逼人,驾驶员们竟认为他们遭到了失败。而科学家们却非常清楚,那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在静默中完成的。
几乎所有的学者一同发出了胜利的叫喊,他们的目光狂热地搜索着空间,发现聚能器下面有一道光辉一闪即逝。太阳的光线被……被一种东西,一件物体,一种物质反射出来……一种刚才还不存在的物质。又有一个不寻常的反光。飞机靠过去,他们看清楚了。
比一片刨花还薄,比一片摇落的玫瑰花瓣还轻,却又像玫瑰花瓣一样在空中旋转,又像一片水晶在阳光下光芒四射,一小片铀在广岛耀眼的天空中缓缓地飘着,它是宇宙间分散能量的合成,它是人类的智慧、耐力、才能和爱情的象征。
那被制造出来的薄片在城市上空高高地飞着,犹如一片落叶,它的出现吸引着学者,他们还盯着它看着。然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性格作出反应。
约翰·阿尔玛依扑到卢士奇和罗莎的脖子上,紧紧地和他们抱在一起,哭着。斯塔里诺疯狂地跳起了快步舞,使飞机危险地颠簸着。然而,伟大的斯波尔的表现使机组人员更为担心。他在地上打滚,头撞着舱壁,无法控制自己歇斯底里的笑,扭弯了巨人般的身体,激烈地抖动着。
很久,他们之中没人能说出一句话来。他们的激动最后用一个惟一的公式表达了出来。
“E=me”,阿尔玛依在两声哽咽之间喘了一口气。
“E=mc2,”卢士奇重复道,紧紧地抓住罗莎的手。
“E=mc2,”罗莎结结巴巴地说。
“E=mc2,”斯帕里诺叫道,摇着胳膊,像风车的翅膀。
“E=mc2,E=mc2!”斯波尔教授吼道,他的笑声使座舱里充满了不断的轰鸣。
可以理解地疯了一阵之后,卢士奇跑向电话,费了好大劲才使朋友们稍许安静下来,他勉强用激动的声音向爱因斯坦宣布他们的成功。
“E=mc2,老师!聚合的能出现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物质,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出现在广岛的上空。您对了,我们对了!”
“我对此从未怀疑过,”爱因斯坦只是简单地答道,““谢谢!”
那薄薄的铀片还在广岛上空慢慢地飘落着。在这欢乐和忘乎所以的几分钟内,它只下降了很短的距离。纯金属在阳光下的闪光使人们能时时刻刻看到它的行踪。
学者们的神经由于老师的安之若素而松弛下来,他们观察着行动的下一步。驾驶员重新打开一个发动机,使飞机能够保持在薄片的高度上。
“创造不能、不应该就此停止,”卢士奇说,“现在应该开始连锁反应了,就像曾经发生在原子水平上那样……是不是我的眼睛模糊了?……那儿,那儿!”
他已经看见了,在被如同火炬一样的物质薄片照亮的空间,两件相同的物体闪闪发光。铀的薄片又有了一个孪生姐妹,和第一个一样地纯洁无瑕,由同样纯粹的物质组成,然而比第一个更为神奇,它们相互为伴旋转在广岛上空,优美地上下飘动。
这一次,学者们静静地看着,只有斯波尔爆发出一声欢呼:“四个!”
现在,四个薄片盘旋在城市之上。但是,挪威学者的话音刚落,八个白点便在阳光中闪现出来。连锁反应的奇迹又出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每一次新的奇异的增生。
“八个,”斯帕里诺喊道。
“十六个,”卢士奇欢叫道。
“三十二个,六十四个!”斯波尔高呼。
奇迹接连不断地产生着,他们很快就目不暇接了,那真像钻石和珍珠组成的波浪,一浪接着一浪从虚无中涌出,彷彿产生于一个隐蔽的天才大脑的跳动之中。一群透明的“蝴蝶”宛如白云飘浮在广岛蔚蓝澄澈的天空,并且不断地扩展着。
飞机绕着圈子,有几个薄片贴近了座舱。
“可是——”斯帕里诺大声说,“这是花呀!”
斯波尔教授笑声又起。他现在一扫歇斯底里的样子,而带有某些狡黠的色彩。
“铀花,”他说,“当爱因斯坦回忆他所受到的热情接待时,一个微妙的思想出现在他的脑际。这个思想,我们成功地使之成为现实。既然创造的原则已被发现,便能按照我们的愿望成形,把金属物质制成花的形状,这并非难事。这样,我们既可以满足日本人的理性,又可以满足他们的艺术感。”
大家都热烈地欢呼,并对挪威学者的富于创造性表示祝贺。
“你们看,”罗莎指着地面说,“他们懂了,他们在向我们欢呼。他们谁也不会忘记的。”
的确如此。日本人理解了神奇的白云的意义,于是全体居民都跑到街上来,人们最初的直觉,对奇迹的预感,逐渐变为科学的肯定,而并未失去其宗教色彩。全体居民都心醉神迷,既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又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广岛人民生活在一种其他任何地方的居民所从未体验过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满足的时刻里,他们沉醉于慢慢向他们头上聚拢的辐射着光辉的降落物之中,内心里充满公式E=mc2的光辉,城里的贤哲们齐声吟诵着这个公式,犹如一曲赞歌。他们的胳膊都在一阵感激、期望和爱的冲动中伸向天空。老人们跪下来,感谢上苍的恩赐。他们强迫孩子们也像他们一样匍匐在地,并让他们无限崇拜地合起双手。
在这光荣和充满快乐的数分钟内,其中的每一秒钟都似乎凝聚着一种难以逾越的幸福,对广岛居民来说,还有更为光辉灿烂的顶点和更为销魂荡魄的时刻。
首先,不断增长的白云愈来愈大,终于像一个巨大的蘑菇伸展在城市和附近农村的上空。这时,广岛的整个天空直至边缘都被那无数的小花盖满,它们比春天的樱花更为娇艳,并且是那样地多,竟使阳光分解为无数奇异的火花和美妙的彩虹。
然后是动人心弦的时刻,人们惊醒的感官第一次在宁静中听到这天雨的音乐。缭绕于他们耳际的声音之和谐,是人间任何音乐所无法比拟的。那些神经过度兴奋的艺术家们也只能在梦中似有似无地听到与这和声类似的轻轻的回响,而一旦醒来便无法追寻了。这是一种伴奏的音响。持续不断,柔和得像最清澈的泉水潺潺流动,像六翼天神并排飞向空间的无底深渊时翅膀轻拍,而在这比难以捉摸的波动更为细微的颤动之上,断断续续地产生着无比纯粹的声音,令人想起薄水晶的震颤,那是无暇的铀的薄片在缓缓下落时相撞所发出的音乐。
最后是天上的学者和地上的居民都热切盼望的时刻,是人造的物质的第一批薄片落到广岛的时刻,它们像神奇的雪,像蝴蝶那样经过长久的翻飞。轻轻地、优雅地落下。这时,人们真是心荡神驰了,难以想像灵魂和肉体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种快感。
如果说广岛的健康人焦急地、久久地希望看上帝的馈赠的话,那么,城里那些不幸的人,病人,残废人,受伤的人,他们更想得到它,他们的热情千倍的强烈,近于狂热,他们都拖着身子来到街上,或让人抬到街上。一种预感把他们从痛苦的病榻上解放出来,那最初的闪光便是他们的希望。
看哪!那聚集在一起的居民们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个波冲击到地上,当这些不幸的人感觉到那初生的物质的气息和它温暖的抚摩的时候,新的奇迹接连发生,彷彿应答着人们在空中所制造的纷至沓来的奇迹一样。一个不幸的人,一个下肢瘫痪的高个子伤兵甩掉了拐杖,把双手伸向天空,跳起胜利的舞蹈。
别的人仿照他的榜样,随着天上的铀愈落愈密,他们也愈聚愈多。那些瞎了眼睛的人,他们从事件发生的开始就把惊呆了的面孔转向天空,现在,当那有魔力的薄片在他们没有生命的瞳孔前擦过的时候,他们的面部松弛了,表情活跃了,眼睛在光的抚摩下震颤了。他们齐声感谢上苍福播人间,这给天空中的音乐又增添了激动的音响。赞颂之声从广岛升起。
看哪,瘫子走动了,瞎子看见了,聋子听到了,伤口愈合了,丧失能力的感官复原了。在这光荣的新纪元之初,上帝并未袖手旁观,他不愿违背人的良好愿望。他不像通常那样把自己的介入限制在几个人身上,而是使奇迹无止境地增加,使所有的痛苦一时都得到平抚,他终于表示了他的仁慈,这仁慈本来是对那些恳求仁慈的人的努力和那些对他坚信不疑的人的信仰的酬劳。
在这种景象面前,广岛的热情迸发了。很快,城市就像过节一样焕然一新。竖起彩竿,挂起标语,插上旗帜,成千上万的小旗上都用斗大的字写着公式E=mc2。奇花异葩似宝石一般把地面盖满。孩子们拣起来,又让它们在手中散落。小姑娘们把它们插在头上,当作价值连城的珠宝。这时,学者们为了使这美景锦上添花,又把一束束五颜六色的焰火射到光辉灿烂的空中,焰火辉映着奇幻的闪光,使它们如同极光一样燃烧在上帝降福的城市上空。
为什么广岛的试验不能在光荣的顶峰结束?为什么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它不仅反映不出原始意图的纯洁,而且甚至还同启发这些事业的崇高原则背道而驰?为什么这样多的爱引起了这样多的混乱?……事情发生之后很久,留下许多信件的约翰·阿尔玛依回忆起这一悲剧时痛苦地引用了弥尔顿的诗,他把这些诗句想像为出自某个恶魔之口:
如果那时上帝试图从罪恶中获得美德,
我们的工作一定是阻止这样的结果,
而从美德中进一步发现罪恶的手段,
那常常获得胜利的罪恶……
然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评论,绝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解说。前面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历史应该满足于忠实地记录事实……
一小时之后,卢士奇发现铀雨无休无止、愈落愈多,连锁反应没有任何缓慢下来的迹象,他首先表示出不安。
“是停止试验的时候了。”阿尔玛依喃喃地说。
卢士奇向他指着操纵杆,他已经把它放到零的位置上了。他指挥不了试验了。一种创造的热情鼓舞着被唤醒的自然,它似乎无法得到满足。
每一秒钟都成为能转化为物质的目击者,并且这种转化在两秒钟之间成倍地增长,宇宙的源泉,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飞机早就不得不提到很高的高度,以便从眼看愈来越厚的制造物中摆脱出来,而学者们只能借助最先进的仪器才能看见广岛上空发生的一切。
在广岛上空,铀雨愈来愈密,愈来愈暗,其光辉渐渐地消失了。铀花的数目按照在棋盘的每一个格子里都放上比前一格子多一倍的麦粒,用同样的定律增加着,难以遏止。数学指挥着一切,而数学不容动摇的严格反映在它每一个感性的表现中。任何光线现在都不能透过这云层的结构,那耀眼的白色和五彩缤纷的光芒都融进了一片灰蒙之中。这是一种质地致密,暗淡无光和沉重的物质,连续不断地落到城市上,使大地为之抖动,那低沉连绵的轰鸣声如巨炮长久而永不停歇地回响。
街上的铀已经埋没了居民的腰部,进而埋没了他们的脖子。学者们借助仪器尚能看见某些被父母举在头上的孩子,不久,这些孩子也被埋没了,合成物质很快地吞噬了那些最高的房屋。
广岛就这样消失了。
当城市被淹没之后,当自然的创造热情枯竭之后,当天空渐渐明朗,最后一批花朵飞落在广袤无垠,不见一个岛屿踪影的金属海洋上之后,当学者们看到广岛一无所存之后,他们都陷入了长久的默想之中,然后卢士奇叹了一口气:“谁能预见这个呢?”
“没人能够,昂里科,”罗莎说。
“可是,”卢士奇犹豫着,“我似乎应当承担一部分间接责任。”
“是我按的电钮,”从扩音器里传出爱因斯坦悲哀的声音,斯波尔已经通知了他。
但是大家都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千方百计地安慰他。斯波尔毫无困难地向老师证明,无论是他,还是卢士奇,或是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不应受到任何谴责。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良心,”他最后说,“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愿望是纯洁的,我们的理想是创造。”
“确实如此,”卢士奇说,他最后望了一眼大地,“有上帝作证,我原不希望这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