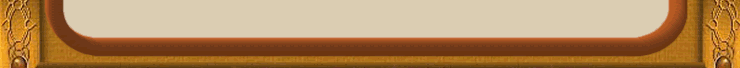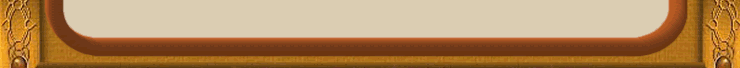|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秉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儆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闻,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旱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写的所谓“五六年之内,四时天气寒冷变化异常,五谷耕作少成,不是经常阴雨连绵,就是经常干旱不断;荆、襄、岳、常等郡县,连年暴发洪水;吴、楚、蜀、粤等地区,到处可见旱涝灾害”等语,是什么道理?当今皇上即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得时,五谷丰登,人民乐业,各省之内,即使有少数州县,有点旱涝不均,朝廷立即给以赈济,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人民生活获得安定。而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关、楚、蜀、粤到处有旱涝灾害,有什么证据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我看有你这样反叛朝廷、狂背逆乱之人隐藏其间,心里常常怀着不满,阴谋违法作乱,致使天常被扰乱,人理被灭弃,而导致阴阳失调,四时易序,所以才有江水泛涨之类的灾害发生。这是天常人理在警告你这种人。这些灾祸的出现,完全是因为你一人所致,你知罪么,你有何辨解?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住在偏辟的山谷野村,好像青蛙坐井观天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偶尔见一处旱涝就说成是旱涝经常可见,而不知道到处是时序调和,五谷丰登,百姓乐业的情况。这都是因为小民不通事理,看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缘故。况且当时确实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深院,也能体恤民情,一遇偶尔的旱涝灾害,便立即动用府库的钱粮,对灾区给以救济,并及时减免赋税劳役的真实情况。弥天重犯今天才知道皇恩浩荡,虽尧舜再世也不过如此。小民的愚顽无知之罪实在不小。一个小民狂妄背叛朝廷,足以导致当地的灾害发生,这个道理若不是精通天人感应的玄奥之人,是不会理解的,弥天重犯今日才豁然开朗,如大梦初醒,虽然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是万分幸运的。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屡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屡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所谓“抚育我的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的就是我的仇敌”等话是何道理?当今皇上即位以来,勤于治理,常常是夜不能寐,批阅奏章,每每是呕心沥血,爱养百姓之心,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些年来,四海百姓无不承受圣上的恩德惠泽。对于过去欠纳的钱粮,减免几乎一千万两银子,仅江浙等处浮粮,就每年减免六十余万两。至于赈济抚恤,减少取消,以及豁免之处,更是不计其数。浚筑河堤,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缉盗除奸,一切政务之事,都实心实意,一天到晚繁忙不停。皇上对天下百姓的抚慰、保护是备至的,所以普天之下,无不颂扬为父母,爱戴称为天子。今你不以抚慰为恩德,反而认为是虐。不以皇上为父母,反而认为是仇人。这是何种心肺,何样肝肠?你认为朝廷虐民,都有何事可作凭据,你把你的所见如实说出来。
曾静供:皇上的恩德、仁义,遍及海内外,他对天下百姓的体恤之意,可以说自古以来少有。弥天重犯住在偏辟的远方,不晓事理,不知天高地厚之恩,只是片面地看到远方之民,贫富悬殊,富者田多,贫者无田,而皇上历年来普降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不动就是几百万,抚养爱恤百姓,真是备至周详,然而只有那些有田产的人家,饱受其惠,而没有田产的人家,多感到雨露不均。直到去年到省城,今年来京城后,才得知皇上有这么多爱养善政,这么多抚慰计划,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但对天下百姓的事却关怀得无微不至,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真是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以来,圣帝贤君恩泽于民,百姓把他们称为天子,颂扬为父母,记在史册之上,载在经典之中。拿今日同过去相比,实在是非常少见,今日四海之内,就已经可以看到百姓爱戴皇上,已经颂扬的真命天子。就说以弥天重犯我这样狂妄地诋毁、冒犯,还受到皇上这样宽大对待,真是非常惭愧和后悔,总感到皇上的恩德比天大,比地厚。其实,四海九州,天下生灵,没有一民一物不时刻在皇上的恩德涵育之中,这是不用说的。弥天重犯我过去之所以不以为抚,反以为虐,主要是听信了谣传,没有看见皇上的恩德,所以恩将仇报。现在想来,这真是王道如天一样,高深莫测,蒙受它的感化而自己却不知道罢了。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原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粜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粜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允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粜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译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的供词中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言语。这卖米事情,是外省督抚上奏皇上时向皇上建议:江浙一带人多米贵,请求动用国库里的银钱,向产米的省分购进之后,再运到江浙,平价卖给百姓,以解决其吃饭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办法,况且,又减价卖给百姓,朝廷还亏着本哩,你为什么说贩卖米石争夺小民之利了呢?至于水银之事,是因为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在任时,因各种原因,落得府库亏空,不能完满交接,所以新任巡抚石礼哈向皇上报告了此事:建议让金世扬原来动用府库的银两收贮的水银,可以再变卖后充公平账。皇上允许他的请求,令他在广东发卖,这不但解决了问题,而且也保全了金世扬的身家性命,这是特别宽大的恩惠。你为什么说这是与民争利呢?不过,这两件事既然流传,必有原因,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你要供出传说之人。
曾静供:弥天重犯对于这此事,当时都不知道这是皇上的经纬谋划和恩赦安排。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这件事,产生的那些谣言,是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的;广东发卖水银的话,是因为那些行走广东的人路过永兴县时说的。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然居住这地离县一百多里,但是乡里常有人在县城来往,所以听得此说,不是直接听远方人说的。那里知道这是移此就彼、酌盈济虚的办法,况且平粜与减价一模一样。变卖水银完公,确实又是体恤臣下,这是皇上办法得当,气量宽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妄加指责。弥天重犯当时确实不知圣虑高远,错误地相信人言,以为朝廷与民争利,今日才知道完全相反,而是利民益民的大事,诬蔑皇上之罪,真是难以逃脱。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此数日之内,成谳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里承认说过“极好杀人,整个京城都感到寒气逼人”的话。我皇上像天地一样,有好生之德,自元年以来,怜悯体恤民命的案件,不可枚举。就说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后,督抚及刑部已经拟定的现有案件,如云南的黑夜杀人的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的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的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山西的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安庆的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的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等等。凡有一线可生的希望,皇上都是又令九卿大臣详细再议,从宽减罪。又有逃纵的窃盗赵玉等人一案,私自造钱的张仙等人一案。有的因其愚鲁,不知道国家规定的条例,有的是因情节稍轻,一律从宽处理。至于共同殴打庶母的曹一案,因他的情节尚轻,不忍处以极刑,命臣下查定确实之后最后议定。根据廷臣所讨论决定的,例如规定捕役治罪之条例,利用符咒诈骗的处罪条例,都因为过去未曾向天下讲明,让有关部门另行详议。这几天以内,现成的文案材料具在,可以逐件给你详看。难道说你曾静没有到来之前,皇上预知你来,故意作假给你看的吗?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到底有哪个人被枉杀?何年、何月、何日滥杀过一人?传说杀了什么人?你必须一一据实说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今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慌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加功拟绞。盖妇人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民命太多。
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
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开始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传,发狂作乱,使自身陷入罪大恶极之境地。自从小民的案发到长沙至今大半年之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美好,才知道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没有一点过错,久为普天之下所敬仰。自从到京城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感到痛悔,不但觉得无脸见人,而且也感到无地自容。加上皇上一次又一次宽大处理,更觉得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圣明天子,不但抚慰万方,而且对一个禽兽不如的重罪之人,这样恩赦有加。现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曾仰承旨意,恭捧皇上亲手批示的九卿所奏民间的那些重要案件及国家条例,典章制度,让弥天重犯跪伏阶前,直接目睹敬阅,真是万分感服,惶恐汗背。虽说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但是皇上的体天好生之德,操劳爱民之念,明明白白地见于御批之下,真是令人感慨,激动得让人流泪。
就说云南所奏的黑夜杀人一案,把主谋定为八十二岁的老妇判以死刑,又把她的儿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也当作同谋判以绞刑。其原因是妇人的丈夫已死,按三纲五常之义,老妇应当听从儿子的,这样何汪为什么不谏阻他的母亲,而轻率地顺从他的八十余岁老母去杀人,而且当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清楚的供词,好像难以再拉扯另人抵罪,然而黑夜抱草烧尸,尤其不可能是八十余岁老妇所干得了的。这个案件把何氏判以死刑,又把她的三个儿子处以绞刑,好像的确伤民命太多。又有广东的殴伤服叔一案,因为祭田引起争执,县衙已经断了银田,两未交清,但是谢日习也不该手持棍棒至谢伯逵门前大骂,这与平时那种越分无礼,恃强凌弱殴打长辈致死人命的情况不同。
又有江西的不知情奸妇一案,通奸之事发生在前,谋杀之事发生在后,两者没有牵扯。况奸妇与其夫离居已有多年,刘氏夫妻的情义未绝,而且还有八岁的孩子,哪肯背弃丈夫而去从奸杀人。法律中有关于“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的条文,这正按通奸来看,不因为刘氏别居多年,此时不可能萌发奸意。这三个案子,皇上考虑的真是细致,明察秋毫,着意关照民间的隐情,所以不肯依照原来的判决,而令九卿再行复议,尽量处理得当。
【原文】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窍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饬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译文】又有江西的误伤兄命一案,因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处很好,本来平时没有一点隔阂,只因为催要丁钱小事,发生了怨恨。开始是因郭国宾拿酒壶砸郭国正,没有打中,而郭国正拾起对方砸过来的酒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最初并不是故意杀害其兄,一时上前反击致死,所以改为应斩监候。又如曹道生的妻子汪氏不循妇道一案,丈夫要茶喝,她不给端,丈夫责怪她,她不但不接受改正,反而用石头还击,并且用头撞她丈夫。曹道生气愤之下,用柴片连连殴打汪氏,以致殒命。这是汪氏自己有失三从四德,而导致的命案,并不是本来道生有意杀害,按法律判的是绞刑。皇上让从宽枷责结案,不但使天下夫妇义正,各循其道而且体察抚恤民情的恩德,真是太大了。
又有查声闻的盗窃一案,他虽为盗首,其实并不是有意去行劫,因误听了一个叫李瞎子的话,目的在于烧毁之文契证券,以图复占。这种情况是愚民无知所致,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他的父亲代为自首,皇上关怀百姓疾苦如圣心真是殷切,准许从宽处理,免去死刑。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百姓的案件中,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皇上都不忍心对其置之死地。
又如一些案件如赵玉、田群、刘五因犯盗窃罪而被监禁后又逃跑,按理当加倍治罪,圣上考虑他们是无知愚民,未必知道监禁后逃跑还要罪上加罪,所以仅仅按盗窃罪维护原判。并且把犯罪监禁后逃跑要加罪的条例明文颁发给天下衙门,公开张贴在监牢门口,使那些犯罪的囚徒,入监的时候就使他们知道这些规定。又有私铸钱文,律斩立决一案,张仙等人私铸钱币,由于他以前以造卖铜器为业,因公家禁止用黄铜器皿,所以就把他所存下的铜私自铸成了钱币,其罪与公家造钱部门私铸有些区别,所以也改为死缓,等到秋后处决。这不仅说明圣上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而且对小民犯罪与公家犯罪也区别得这样细致,这真如茧丝同牛毛混在一起,也能辨别出来一样,竟是细致入微到这样程度。
【原文】
又如曹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殴狄氏之时,曹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
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到,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舂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与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难以数计矣。
【译文】
又如曹同殴庶母一案,按照法律处以凌迟,也没有什么说的。皇上的批示中根据情况分析了孙氏挑唆曹霍柽,共同殴打狄氏之时,而曹起先并不在旁边,是孙氏指使使女小春去把曹叫过来的。曹听从父母之命,帮助欧打狄氏,致使狄氏伤势严重,到第九日就死了,此案中曹虽行殴打,但原本没有要把狄氏致死之心。因此把曹改为死缓。秋后处决。这个案呈中只因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一句,就引起了皇上的高度重视,马上推究原由,恰当定案,改判从轻。以此看来,我皇真是神明照烛,无微不到,用心良苦也只有这样了。
又如周元伯一案,周元伯与周见南是邻居,两家房屋紧邻,因为舂米争碓,两人互相谩骂起来,后又打起来,周见南遂被周元伯打伤。刑部议案判为应斩立决,而皇上下旨又让九卿再议,不忍因一次打架致伤而判为死刑。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粹是以道德教化,并没有一点用法的迹象。大概“道”这个理十分玄妙、深奥。没有一定的形体,混然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地变化无常,不是大圣贤、大智慧之人是掌握不了,也不能运用灵活的。法律虽然依据道来制定,但是一落到具体法规,就有些死板,局限,不再灵活了。
所以先儒已经讲过,三代以道治世,而后来则以法把持天下了。如后世贤君要算是汉文帝、汉景帝,然而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所以说黄老清静,但法无惨刻。他们也没有把道用活,没有真正领会其精神,如果碰到犯死罪之人,依现成的法让他抵命,并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都是按现成的死板条文、死板条例去断,就可以清静、无为、省事。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仁心恳切,全副精神、全副精力都用在百姓身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凡事斟酌权衡,处处体谅下情,真是与古代圣君尧舜、禹汤没有两样。
再比如说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事先没有告诉百姓的条文,百姓犯了这方面的罪,也给以宽宥,不予治罪,等颁布了条文规定,公布给百姓之后,再有犯者,才加以严惩,才不使百姓怨枉,决不忍心于不教而杀,不教而惩。看到这里,直觉得皇上那种爱护百姓之情。此文王对待百姓的心情更切更笃。唯恐百姓无知,而犯了法度遭受苦痛,这就是个天了。大概皇上的宫殿,如天体一样,大自然的元气周流四时,无所不包,即使当秋天处于肃杀寒冷季节时,也无不包含着、孕育着春天的生机,所以许多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善政善教,使许多人改恶从善,如果是万一犯了刑科,也仍然根据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查根追由,有的得到体恤,有的得到原谅,有的得到从轻发落。这真是仁至义尽了。就说近期从四月一日以来,短短几天,略举几例,没有一件不体现皇上的仁德,何况这以前呢,更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有那些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有几千几万。由此看来,皇上的好生之德,普及四海的仁政,确实是难以用数字来表示的。
【原文】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
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赉”字的“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
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译文】
皇上不但勤于民事,而且敬天之念也没有一时一刻懈怠,没有一时一事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都是一个字不准确,一个意思不确切,都不随便接受。而且都不肯有大臣的颂扬之词而忽略不问。如皇上在圣谕里批道“朕的事奉上天,就如臣下事君那样,臣把君看作九重之尊,而人君看待上天,也同样看作九重之尊。假如各级官员称颂他的上司,说成是‘上所崇奉’,或者称成是‘福与君齐’,那么那个上司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不感到害怕吗?今在奏章中把皇上赞扬为‘效灵齐天’其不是违背理义、轻慢神灵‘陷朕于不义吗?’细细地体会这些话,真是非常实际而且也十分透彻,可以说是自古圣君贤后所达不到的见地,自然应该永远当作后世的法规程式。皇上敬仰道德到了极点,心细也到了极点,臣下呈上来的奏章,即使出现一字之误,也能发现并及时地指出来,例如李凤翥的贺本之内,误把“赉”写作“赍”字;总督高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银有在二三两”的句子,句子落掉“两”字,这已经经过了多少衙门校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也没有发现,结果皇上一看就指了出来。
自古以来,作帝王的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大多是听听内阁大臣的现成意见和结论,即使阅览一些臣下的奏章,也只是仅仅看看贴黄,有的时候恐怕连贴黄也顾及不到,哪有时间去细看案呈文件。况且案呈文件已经有许多官员层层把关都发现不了问题,一般情况下皇上怎么能够知道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皇上留心国政,太周密太细致入微了。关心天下苍生,真是劳累,真是辛苦,同时也可以看到皇上的学问渊博精深,敬业负责。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马虎,一点轻视,都是聚精会神地处理问题,没有一件不尽到心思,没有一件不做得周详。所以帝尧称圣人是以钦佩德政为先,孔圣人修养自身是以坚持敬天为根本。而《中庸》一书的主旨也是笃恭而天下平”。今天我皇上处理政务如此地细致和周密,真可以说是先圣后圣,同揆合符”了,同过去的圣君没有两样了。
【原文】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之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谟,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目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
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译文】
弥天重犯是山野之间的庸俗卑鄙之辈,没有一点知识,怎么能仰测天地之大呢!但是今日既蒙旨下问,根据自己的一点所见就心悦诚服,其实皇上有经纬策略,远大规划,弥天重犯算什么人,怎么能够了解呢?况且从前僻处深山好像未曾见到天日一样,就是有点意见,也不过是像蝼蚁那样,揣度广大的天地,怎么能够知道他的高深呢?所以一听到谣传,就信以为真。
就比如说近来的一件事,承蒙大人捧出本章,上面讲到马廷锡讹传消息说:皇上因听信管天文的官员钦天监启奏,说紫微星落在东南福建那个地方,会有帝王出现,危及本朝,所以特派大人赴福建一带,把凡是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童,全部处死。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以为证。这个事,若让弥天重犯当时听到,一定以为是真事,并且写到书里去的。小民无知,大概都是差不多一样,况且弥天重犯尤其处于深山穷谷之中,可以说是无知小民中最无知的。不到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一路上所见所闻,而且亲身受到皇帝的如此恩惠宽宥,并亲眼看到皇上对百姓这样悉心爱护,对政务这样操劳。才实实在在地信服皇上德同天地一样广大,同日月一样光明。从前在长沙时候,蒙三位大人多次对小民宣传皇上圣德,虽说也信服,但是还总有些疑惑,并不全信。到今天为止,才真正是拨开云雾见了青天,心里才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是这样地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但遗憾的是,自己陷入法网,不能回到老家,去宣传皇上如天地一样的恩德,像古代圣君那样的明哲,人的父母一样慈爱百姓,以便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之地,共庆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同时使山角海边,都痛恨和反对那些造谣诽谤的奸人,恨不得吃其肉,剥其皮。虽死难瞑目,即使如此,也痛感不能报答皇上恩德的万分之一啊。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赡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廪给以赡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时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宫人,厚赐赡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之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话,这是从何说起?当时密亲王的妃子,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的宫人,因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无力养活那么多人,同时与密亲王关系密切的也感到不得其所,所以特降谕旨,让理郡王的生母,将这些宫人分别做出安排。并且皇上传旨对每个人逐个进行询问,若有人旧想仍留在宫中,那就按圣祖皇帝的老妃可以居住宁寿宫为例子办。这时候有人愿意仍居住宫中,所以皇上就让她另住别宫,并且给丰厚的待遇。这件事是皇上对密亲王宫人的恩德,凡是宫中之人和朝臣都是知道的。今你这话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你又把密亲王叫做三爷,消息虽为误传,但必定有乱说之人,你可据实供出来。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的五六月间,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罪的官员,是他这样说的。弥天重犯听到此话后,没有仔细分析,辨明真伪,意为既是从犯罪的官员口里说出,一定是实事。到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传说谣言的是个什么人,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犯官,但只要朝廷上查一查那年那月,有什么犯官从衡州过就清楚了。直到去年到长沙,听到正道舆论,才知道皇主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不是完完全全地合乎天理,而没有一点人欲的圣君,哪能这样精明为国,哪会如此焦劳为民!后又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毫无瑕疵,并且又使小民伏读圣谕,真是表里无憾,完全与在长沙听得的正道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更加相信,从前那些谣传全然是假。况且皇上加恩于宫人,对她们给以优厚待遇,是圣主的仁慈善政,而谣言却传为是皇上把那些妃嫔纳为己有,岂不是使人痛感遗憾!这十多份的供词,不是弥天重犯怕死贪生故意这样讲,实是因为朝廷把小民缉拿出深山穷谷后,见闻渐渐地开阔,认识渐渐地提高,实实在在地看到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兴奋,自愧自悔为什么不做一个盛世良民,所以痛心遗憾到这种程度。其实自己所供出和谈吐的很多地方,都是理屈词穷,语言无序,不成词句。而且山野愚夫,从来不知道上奏陈词的规矩,言词文体的格式不免有许多错误。加上自从到京城以来,惭愧后悔的心情很重,感慨涕泣消耗了精神,四肢疲惫难以抬起,惶恐战栗,手指也打颤震动,一点一画不像个字,千万叩首,仰请圣上明鉴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