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回 稽首莲台万缘独立 相逢萍水一诺千金
|
话说宝钗听珍珠说一窗花影反不如半榻松风话,颇有理解,正欲答应,见周贵家的来回林之孝伺候。王夫人吩咐着他进来,周贵家的答应出去,同林之孝来见,给太太请安,又给三位奶奶、姑娘问安。王夫人道:“自老爷去世,我悲哀成病,不能下炕已及二年。今日心中安慰,一旦病痊。且有几件要事与你商酌,不是一半句言语可以完结。”吩咐丫头端张炕桌摆在一边,地下铺个小垫子,命林之孝坐下,“赏杯酒你吃,我有
话说。”林之孝赶忙回道:“太太赏酒,奴才站饮,断不敢坐。”
王夫人道:“你是我家三代老家人,比不得别的家人小子。你且坐下,我慢慢对你说话。”林之孝道:“奴才伺候着,太太只管吩咐。”王夫人道:“你不妨坐下,等我想着说话。”林之孝不敢再辞,只得磕头谢太太赏坐,在那垫子上偏着身子坐下。丫头们摆上杯箸,赶忙斟酒。王夫人将桌上果碟撤几样给他。
此时,高照地光全已点上,周贵家的、张瑞家的领着丫头们慢慢上菜。王夫人饮了几巡酒,用过两回菜,这才将宝二奶奶们入梦之事大概说了一遍。宝钗、珍珠又一层一层细说一番。
林之孝十分惊叹。王夫人命将宝钗、珍珠的衣服、护肩给林之孝观看。林之孝接着,站起来定睛细看,甚为惊异。王夫人道:“我患病二年,百药无效。若不是宝玉的灵丹,如何就能脱体?”
林之孝道:“奴才心里也想着,太太病的日久,怎么今日比前几年不病时精神还好?谁知是宝哥儿进了太太的灵药。本来宝哥儿生下时,原是怪异,人人都知道是有来历的人。如今果然成了仙得了道。俗语说的好,一人得道,九世升天。以后太太可不用十分惦记他了。”王夫人道:“从此以后,我这心倒可以放下。”林之孝道:“刚才说老爷提起什么房子,奴才还没有听真。”宝钗同珍珠又将老爷吩咐的话再说一遍,并说:“太太回南之事,都托在你一人身上。说是住咱们这宅子的人,祝亲家知道。”王夫人笑道:“不知这祝亲家、桂亲家是谁?”
林之孝连声答应道:“奴才受这府里三代深恩,不敢不诚心报效,竭尽犬马。今日老爷成了神,还将这些重事委付奴才,奴才敢不耽承报效吗?”宝钗点头道:“老爷谆谆吩咐,知道你老成忠正,不负所托。太太回南事繁任重,大非容易。我同四姑娘敬你一杯酒,以慰老爷托付之心。”命丫头们执了壶,同珍珠把盏。林之孝望空磕头,谢过老爷、太太,跪饮三杯。王夫人欢喜之至,说道:“家门冷落多年,必须回南整顿,重兴故业,庶不负祖宗功绩。只可惜荣公世爵,子孙不能世守,深以为愧。”宝钗道:“太太回南后,培植子孙,书香有继,这就是不负祖宗功业,何必以世爵为念!”李纨道:“我只愁这座宅子如何去得掉,连着这大观园,谁也买不起,就是房牙子知道要卖,谁敢进宅来瞧?这件事有些难办。”林之孝道:“咱们家要卖宅子,最是一件难事。但是老爷说住宅子的人祝亲家知道,又说桂亲家短少盘费,咱们就着回赎金陵祖屋。奴才想,住这宅子的人,自必来找咱们,不用托人张罗。倒是金陵的宅子,原典给兵部郎中桂三老爷,他同咱们家是同寅相好,怎么老爷称他是亲家?自然还有个什么缘故。”珍珠道:“这些事自有一定的机会,一时亦难以揣度,倒是太太先将金佛一事赶办,以解冤孽要紧。”王夫人点头,命宝钗将锭赤金递与林之孝道:“你与我赶着造尊佛像,我明日亲送去铁槛寺中,给尤二姐解冤释恨。虽是宝玉众人将他两个冤恨解开,到底腹中那块金子终非了结,不能无恨。我如今替他造尊金佛,供在铁槛寺中,朝夕谶经,可以消他几世的怨气。你去找个高手匠人,赶紧打造,我明日亲自送去供奉。”林之孝答应,双手接着,连声叹息道:“不是奴才大胆说,这都是凤二奶奶过于残忍。活着的时候,尤二奶奶奈何他不得,如今凤二奶奶在阴司里,那里有当时的威势?尤二奶奶这一腔怨气,自然是要报的。幸亏宝哥儿同众姑娘的情面,才将这一件冤帐了结。不然是不知道要报几世的仇恨呢!”王夫人们不胜点头叹息。林之孝道:“明日断来不及,奴才命他们赶紧去办,请太太后日到寺拈香罢。”王夫人点头道:“很好,就是后日。只要办的妥当。”
林之孝答应,谢过太太赏酒,退了出去。
平儿道:“我要回去给来旺家的烧了纸锞,再来吃饭。”
王夫人道:“我常远不到你那院里,等吃过饭,我也同去逛逛。
今日又是大好月色,到你家去喝茶说话。”珍珠们连声答应,又饮了一会,伺候太太用饭已毕,同到平儿院里闲话不提。
且说贾琏带着小子三儿,主仆两个骑马出城,见路旁两边俱是高柳垂阴,野花含笑。村庄上那些孩子们挎着筐子满地上争拾马粪。行过一座板桥,只见一望不尽的麦浪黄云,被风摆着层层叠翠。贾琏正看得怡心悦目,忽然道旁麦地里飞起几只白鹭,雪光闪闪,刚欲飞入浪中,又惊起一阵乌鸦,跟着那白鹭冉冉飞去。主仆两个顺着柳堤信马走去,见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上,口里唱着山歌,随着那个牛慢慢过来。听他唱的山歌道:送郎送到黄土坡,手拉手儿泪如梭。郎与姐儿一件衣衫作纪念,姐送情郎一个大窝窝。郎说我吃着窝窝想着你,你别将我的衣衫丢下河。姐说情郎忒心多,我不丢你你丢我。你丢我去采花草,采了这窠又那窠。可怜我似檐前水,点点滴滴不离窝。郎说姐儿不用多心罢,我也想你你想我。
贾琏叹道:“咱们骑着骏马,倒不如他坐在牛背上的有趣。”
行走多时,来到一座土地庙前,两旁那大槐树下坐着好些挑担的买卖人,俱在树阴下歇脚。贾琏道:“咱们也歇会子,再去将牲口拉去饮水。”三儿答应,取下马褥铺在一边树下。贾琏靠着树根,甚觉凉爽。
只见那担夫中有一个后生,起身走过这边,对着贾琏道:“二爷,怎么今日得闲出城逛逛?”贾琏向他细看,认得是常在府里送炭的老张,因答道:“我要往铁槛寺去,牲口上乏的慌,在这里歇个腿儿。”老张道:“铁槛寺的这条道儿过不去。”
贾琏急问:“为什么过不去?”老张道:“那座石桥去年被大水冲断,有好几村的人要进城去都绕着道儿,多走八九里、七八里、十来里的都有。这座桥原先原是那些庄户人家共发善心,不拘男女大小随缘乐助凑攒了几年,好容易才将这桥建造成功,以此就取名万缘桥。如今,村庄上这些人家穷的多了,家家自顾不暇,那里能够做好事?就有一二处有钱的人家,别样上面倒肯花钱,若提起做好事,比剥他的皮还要心痛呢!”
贾琏道:“这桥要多少银子可以修造?”老张道:“这工程大着呢,总得几千两的足平足色,少了不能。”贾琏道:“比如这会儿有人发心造桥,托谁去办呢?”老张笑道:“我的爷,这会儿那里有这样的大善人?要他有钱,又肯发心,还怕没有人给他去办吗?这也不过是咱们爷儿们白说话。若是有这样的大财主大善人发心去建这桥,只用托东庄上的刘长者,交给他办,又省钱又结实。二爷不知道,这刘长者就住在咱们东庄上,他家几代都是工部的石匠头儿。他家世代忠厚,人人都叫他家是长者。这老刘长者是前年不在的,这会儿是小刘长者,也有五十多岁,有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一家子过的很和气。
他家原很过得,因那年修皇陵,管工的官要使费,想他给的不够分儿,诸事挑持。说他的石头大也不好,小也不好;厚的叫他铲的精薄,薄的又要叫他换厚。闹得他左赔右赔,将一分家私赔光还不饶他。后来我听见说,幸喜咱们老爷正在工部里做员外,对那些管工的官儿们说了情,好容易才将这件工程完结。那刘家的父子,将咱们老爷就感激了个使不得。这会儿提起老爷来,他们还是念不绝口。他们父子为人正直,从不欺心骗人。以此这些各庄的大大小小,都同他很相好,谁不相信他呢?”
老张正说未了,三儿带马过来。贾琏起身,小子搭上马褥,问老张:“咱们到铁槛寺,往那条路去?”老张道:“打这儿向南去,过了赵公爷的坟,向西一拐,转过柏树林,拣直向东去,走到土神庙戏台后身,再向西去,过一座长板桥,向着南去就瞧见铁槛寺的那一带树林了。”贾琏命三儿记着。主仆上马依着他的话,扬鞭而去。果然转向东西,过了长板桥,一直来到铁槛寺山门下马。有个沙弥瞧见,赶忙入寺通报老和尚。
贾琏往里进去,见老僧法本出来迎接,上前施礼说道:“长远不见二爷,今日是什么风儿刮到这儿来呢?”贾琏笑道:“特来照顾你的买卖,找你商量。”二人来到方丈,与法本见过礼,彼此坐下,侍者们送茶伺侯。法本问:“太太、奶奶安好?”贾琏答应:“都好。”法本道:“我本来惦记着,要进城去瞧瞧太太同爷们,因为这赶车的有病告假回去了,一会儿找不着个妥当赶车的,因此这一程子出门就很不便。像前几天珠子王家、元宝张家都套了车来接我,一进城去,二爷想,还由我做主吗?一住就是几天,还有好些太太、奶奶们都等着我去做经事。做了这个太太的,不做那个太太又使不得。咱们本寺这几个和尚如何去得?我只得外请了几位南僧去做经事。这家那家的一连闹了一个多月,把这些和尚一个个多闹的垂头丧气,倒像害了一场大玻我也乏了个使不得,养了这一程子,这两天才扎挣得祝”贾琏笑道:“怨不得我刚才瞧见你软瘪郎当的,没有点儿阳气,谁知是经事做坏的。”法本笑道:“好,二爷该罚个什么,自己说罢。”贾琏道:“这是你说的话,罚我个什么劲儿!”法本笑道:“罚你五十斤香油,点佛前的灯罢。”贾琏道:“罢呀,你拣直的说厨房里香油快吃完了,又何必拉扯在佛爷身上去!”两人正在说笑,侍者来问晚饭,贾琏道:“且等一会,我今日来没有别的缘故,是要给凤二奶奶同尤二奶奶做几天道场功德。明日就要起经,先是太太给他拜三天水忏,再接我的经忏。”说着,向怀里取出白银三十两,递与法本道:“你且收着,做完经事,咱们再算。”法本道:“算不算再说,只是如何来的及?要到四方八路去请人,明日料理妥当,后日一早起经罢。若说是给凤二奶奶念经,连这几两银子都不该收才是。想着凤二奶奶生前,每年佛爷跟前不知花多少钱!就像那年蓉大奶奶出殡,凤二奶奶那样的张罗,那一件事不要经他老人家的心坎儿上打个照面调停的妥妥当当?谁不赞他!后来收下来的那些素供饽饽,桌子陈设的那些东西,拢共拢儿都给了咱们寺里;又把那些剩下的米煤柴炭也给了寺里,叫咱们这些和尚直吃了一年。后来听见凤二奶奶升了天,谁不伤心流泪哭的要死。至今这些和尚,睡里梦里都想着凤二奶奶呢!”贾琏听了,止不住哈哈大笑道:“罢呀,都是被你们这些和尚想他,将他想的下了地狱,你们还要想他呢!”法本也觉好笑道:“我说话拙,二爷别挑眼儿。”贾琏笑道:“结了,咱们说别的罢。”又在怀里掏出一包儿来,说道:“这是凤二奶奶的一支头发,你放在磬里也使得,木鱼里也使得,另请一位有德行的戒僧对着头发念七昼夜金刚经。”法本道:“这又是什么讲究?”贾琏道:“你别管他,只管依着我办。”法本点头,收了头发。贾琏吩咐侍者:“命三儿将我的衣包带进来,交你师父收着。”和尚们摆设晚斋,贾琏一面吃饭,问道:“有个刘长者,不知你可认得?”法本笑道:“他是石匠头儿,就住在咱们这东庄上,成天在寺里说闲话。才不多一会儿回去了。”贾琏道:“你着个人去叫他来,我要问他说话。”法本点头,吩咐着人去找老刘,刘贾府琏二爷找他说话,请他就来。侍者答应。贾琏用斋已毕,取水漱口,小沙弥伺候洗脸净手。不一会,有个侍者领老刘进来。法本瞧见,起身笑道:“老刘,琏二爷要找你说话。”贾琏抬头看那人,有五十多岁,花白髭须,长方脸儿,一团和气,走进来望着贾琏就要行礼。贾琏赶忙拉住,说道:“久仰,你家几代长者令人可敬,今我有话相商,奉请过来,别要拘礼,请坐下,我有
话说。”老刘道:“爷在这儿,匠人怎敢坐?况且老爷又是匠人一家恩主,匠人更不敢乱坐。”贾琏道:“你这样拘礼,我就不好同你说话了。”法本道:“罢呀,老刘你别谦让,咱们这二爷不比别的爷们,让你坐,你告个罪儿,只管坐着罢。”老刘听说,只得告罪,歪着身子坐下。
贾琏道:“请你过来没有别的,要同你商量万缘桥之事,不知要多少银子才能修造成功?”老刘笑道:“这个功德是二爷独办呢,还是别人托办?吩咐明白,匠人再说。”贾琏道:“是我打谅要办。”老刘笑道:“若是别人办这件功德,非离了五千两不能;若是二爷要办,只须二千五百银,也就办得起来。”贾琏道:“怎么我办就少这些?”老刘道:“有个缘故。那年匠人同父亲承办皇陵,因管工的官儿除了例规外,另要使费。匠人的父亲因这件工程并无出息,不肯另给使费。谁知工上的官儿们怀了恨,格外挑持,驳掉好些石头,不准报销,因此将一分家财赔个干净。后来工程告竣,将那照例的工价又要核减去十分之四,匠人父子急的要寻死上吊。这天在工部衙门口正遇着咱们老爷,匠人父子就拦着车诉说苦情。蒙老爷恩典,向着那些大人们力争,才将照例的工价准销。老爷不但救匠人父子性命,连匠人一家子性命都是老爷恩赐的。后来驳下这些石块,至今堆在庄上。去年原打谅要修造这桥,除石头不算外,将那些应用的石灰、桐油、白矾、麻筋、木桩、铁绊以及匠人们的工价、运石的脚费细细估计,必得二千五百银子才能完工。匠人无力,将这条心也就歇了。而今二爷发这个大善心,做这件大功德。除那石头是匠人报老爷的恩典不算外,二爷竟交给匠人二千五百银,匠人给二爷出个力,办成这件大功德,比什么好事还要功德浩大。匠人也沾二爷的光,得些好处,这便一举两得。若是别人要办,还得算二千五百两的石价。”
贾琏道:“既如此,事很凑巧,就将这事奉托,送你二千五百两银子,成功后再谢。”老刘道:“既是这样,我连立碑、刻字、建碑亭,一箍脑儿都给二爷包办。”贾琏甚喜,说:“后日在此念经,就是这日开工罢。必须赶办。”老刘道:“既开了工,自然赶紧去办。”贾琏点头吩咐老和尚:“殿上佛爷前点上香烛,我要磕头祝赞。”法本亲自去点香烛。
贾琏带着这老刘同来大殿,虔诚拈香,跪在佛前,将凤姐心事并现在修造万缘桥之事默祷一遍。拜毕,命老刘也过来拜佛,随在手上取下一只赤金手镯,递与老刘道:“以此为定,即以奉托。”老刘道:“二爷已在佛爷前拈香立愿,等着后日开经破土,就动起工来。不拘几时,匠人到府里来领银子,又何必给定?”贾琏道:“这不过是点诚心,等着完工之后,我再谢罢。”老刘不好再推,只得双手接着戴在手上,说道:“天气尚早,二爷骑个牲口到河边去闲逛逛,就便瞧瞧桥的形势。”贾琏道:“很好。”吩咐三儿赶忙去备牲口。老刘向老和尚借了一匹马,不一会儿都拉在庙门伺候。
贾琏辞了法本,同老刘骑上牲口,一同三人在柳林之下迎着夕阳西去。真是村庄如画。约莫走了三五里来路,望见一道长河,清波荡漾,回环曲折,不知有多少远近。正在遥望,早已来到河边。老刘用手指道:“二爷瞧,这不是旧桥的基址!”
说着都下了牲口,命三儿牵着。老刘在河边指与二爷看这桥身的宽窄。贾琏看那水面约有五丈多宽,遇有发水时,竟有十余丈宽。又看那旧桥基址,原不甚宽大。那些被水冲塌断折的石头,俱倒在水中,将水激的喷银飞雪一样。
老刘同贾琏沿河一面走着,将造桥的道理说与他听。不觉走有二里多路。见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个后生,看去不过十六七岁年纪,生得十分清秀,不像是庄家小子,坐在石上钓鱼,旁边放着个半大鱼篮。老刘瞧见叫道:“柳大爷,今日钓着大的没有?”柳郎见是老刘,同个三十来岁的人,生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红,带一脸慈善之气,身上衣服亦颇华丽,头上带着青纱软翅巾,脚下穿着皂靴,像个贵公子的打扮。柳郎看毕,口中答道:“不曾钓着大鱼。”把脸掉转去依旧钓鱼。老刘见他看贾琏几眼,并不起身招呼,恐贾琏脸上磨不开,因用手指道:“这位大爷是礼部主事柳老爷的公子,因柳老爷去世,太太领着这公子娘儿两个在馒头庵守灵。柳老爷是个念书方古人,家中素来清淡。做官的时候,不过使唤一两个仆人,自从柳老爷去世后,他们也都散去。这会儿太太身边只剩个丫头,同这位大爷住在庵里。去年还当卖着度日,今年当卖一空,娘儿两个手头很窄。二爷,瞧不得他这么年轻,他极孝顺这位寡母,成天在这河里钓鱼,拣大的留着给太太吃,将小的拿去卖钱买米。可怜他娘儿两个就这样苦度。”贾琏听他是位公子,又孝行可敬,倒赶忙走至河边,躬身拱手道:“柳公请了!”柳郎听见,回过头来,看见那人拱手躬身站在河边,连忙放下钓竿站起身来,将那件破衫子抖了一抖,过来与贾琏施礼,问道:“先生尊姓?”贾琏未及回答,老刘忙说道:“这是宁国府贾大老爷的二公子,原任工部郎中贾二老爷的侄儿,当今元妃娘娘的兄弟。”柳郎道:“原来是位贵戚公子,失敬之至!”贾琏亦赶忙谦让,因问道:“尊大人仙逝之后,京中岂无亲友同年,虽无指囤举舟,哀王孙而割爱者,亦当集腋成裘,伴灵归去。何以尊兄奉太夫人羁旅松门,对清流而独钓?琏虽不敏,愿闻其说。”柳郎道:“先君落落寡交,素常清介,公余之暇,惟有闭户读书,不通庆吊。虽有一二往还者,俱是同寅,泛泛并无关切之人。至于年谊,早已落落晨星,毫无询问。先君在日,已复尔尔,及至见背之后,嫠妇孤儿,一棺相对。弟虽不肖,亦不敢堕父之志,摇尾朱门。故守此钓丝,以图甘旨。今蒙下问,用敢缕陈。”贾琏见他器宇轩昂,语言清朗,又细看光景面貌,很像当年蓉大奶奶兄弟秦钟的模样,心中十分欢喜。
拉着手道:“萍水相逢,三生之幸。琏有一语奉读,未知肯容纳否?”柳郎道:“庸才碌碌,毫无知识,今蒙谦抑,愿领教言。”贾琏道:“三生之幸,得接光仪,一见丰姿,令我钦仰。
欲与贤兄订石上之盟,约为昆季,伏乞允从,幸无见弃。”柳郎未及回言,老刘笑道:“倒很好,两位都是公子,一见面儿就说得来,这才叫三生有幸。不用说,琏二爷年长是哥哥。柳大爷,就在这块大石头上面,两个磕个头儿就完了。”柳郎笑道:“我怎好仰攀!”老刘道:“罢呀,大爷不用过谦,哥儿们见个礼罢。”柳郎道:“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两人在石上拜为昆季。贾琏要往庵里去见太太,老刘道:“这是要去的,我给柳大爷拿着钓竿鱼筐,也不用骑马,两箭来路,哥儿俩慢慢说个话儿,几步儿就到了。”贾琏道:“这倒很好。”
弟兄在前,老刘同三儿在后,一同向着馒头庵慢慢走去。贾琏问道:“尊大人科名乡贯以及兄弟年岁名字?”柳郎道:“先君讳遇春,字香雪,系甲戌进士。祖籍广东廉州府人。家本贫寒,别无田产,有祖屋十余间,家眷进京时,已典为路费。弟名柳绪,字幼张,今年十七,有一胞姐系前母所生,早已出嫁,旋即去世。弟母汪氏,今年四十,只生弟一人。先君旅榇现厝寺后。请问二哥年岁名字?”贾琏道:“我名琏,字小商,行二,今年二十八岁,祖籍金陵人氏。”正说话,不觉已到庵门。
有个小尼姑妙静走上前来,说道:“二爷怎么这会儿才出城来?到这儿干什么?我在这里瞧着你们来,射着太阳的红光看不出是谁,再也想不到是二爷。家里的太太、奶奶们都好啊?”贾琏道:“好,你们老师父怎么一程子不进城去?”妙静道:“二爷不要提起咱们老师父,自从去年送那倭瓜到太太那儿去,他回来的时候,出了垂花门,遇着凤二奶奶对他说:‘那件事等着你去审呢。’他唬了一跳,赶忙回来就发烧害玻只一点上灯,就见神见鬼,直闹了好两月,好容易求神许愿的,这才好些。谁知前日黑间,又大嚷起来,直哼哼了一夜,说是瞧见个青嘴獠牙的鬼,拿着个大铁钩子,在他脊梁上扎了一下。昨日早上,咱们瞧瞧那脊背上肿的像个大碗似的,赶忙去请那有名的外科温大夫来瞧,他说是个阴发背,恐怕好不了,给他上些药,又开了一个帖儿。他说你们再请别的高手来瞧罢。今日是老师父的那个外外宋钟,荐一个大夫叫做什么史德成,来给老师父瞧,他说不相干,是点儿火毒,包在他身上,几天就医好,要三百银,少了不依。老师父先给他一百银去配药,他就给老师父先上些药面子。赶他去不多会,老师父就昏昏的睡去。直到这会儿也没有醒。这史德成真个是个好大夫。”贾琏听说点头叹息,心中早已明白,只不便说出。
老刘道:“二爷同柳大爷多坐会子,我还有事,不能够在这里陪二爷,我可要先走了。”说着,就将钓竿鱼筐交给妙静,说道:“你给二爷送进去。”妙静道:“仔吗,刘大爷到这儿来,连水儿也不喝口儿就去吗?”老刘道:“罢呀,天也不早,我还有事去呢。”贾琏道:“既是如此,就烦捎个信儿给老和尚,说我在柳大爷这里有一会子呢,横竖今日是大月亮,叫他等着咱们罢。”老刘答应,辞了贾琏、柳绪,上马而去。
柳绪向妙静手内接过钓竿鱼筐,说道:“二哥请少待,等我进去禀知母亲再来奏请。”贾琏对妙静道:“你同柳大爷进去回声柳太太,说我请安,要来拜见,还有说话。”妙静答应,跟着柳绪进去。贾琏慢慢走进庵来,庵中姑子俱知道琏二爷来了,这个赶来请安,那个也来问好。正在你一言我一语,柳绪急忙来请,说道:“奉母亲之命,请二哥相见。”贾琏听说,忙将衣冠整顿,跟着柳绪往柳太太这边来。未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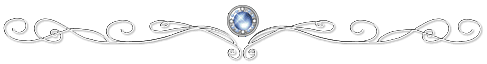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