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哭向金陵
|
荣国、宁国二府被罪之后,因那府第原是先皇敕造,园子又是贵人省亲特建的,均不抄没,馀者产业皆已入官,只家中日常所用什物及眷口衣饰等细琐陈设、粗笨家具,留下以维其生计。靠卖这仅存之物度日过活,家下人散的散,遣的遣,各寻门路去了。唯有三户老仆夫妇,为人朴厚忠诚,不肯背弃旧情的,还在府里共患难同甘苦。这时荣宁二府案情稍缓,身无大过者皆可在军功上效力自赎。贾政贾珍等派往军粮转运处和马匹供养补送等事务上去,贾赦判了监候之刑,唯有贾琏仍在京东皇庄一带管理收存采集等事,故不时仍可回来料理些家务私事。
此时王夫人早已惊痛病倒,不能理事。凤姐事发后,素日仇者一齐唾骂毁谤,原先借在王夫人处理家之任是无人肯服了,邢夫人乘势收回到东院里去,这边只得由李纨求借平儿留下协理。
凤姐自回到邢夫人手下后,全家对她并无一个怜惜疼顾之人,从邢夫人起,任意寻隙施以挫辱。这时邢夫人还剩下一个旧日身边人,便是曾赏与贾琏收房的秋桐。这秋桐当日来到凤姐房,原是新插来的眼中钉,只因那时尤二姐比她更要紧,凤姐便忍下,反使她去作践二姐,以致二姐难以忍受,吞金自尽。二姐死后,那秋桐自恃是大老爷先收房的人,比凤姐还要位高,不把凤姐放在眼里,时常生事,凤姐哪里肯让她,二人早已日渐水火相敌了。如今恰好又都回到了邢夫人手下,凤姐又已失势无权,于是秋桐便肆意刁难凤姐,每日更加恶言丑语,指桑骂槐,羞辱凤姐。凤姐此时,恰如早先的尤二姐受她的暗气明倾,一般无二,且又过之。
那凤姐本是个脂粉英豪,又是威权娇贵惯承宠奉的,到这地步,如何受得过?为时不久便病上加气,卧床不起。
平儿明知此情,但也无挽转之策,只是时常打发人来送食送药,空时亲自来看。二人见了,有秋桐等明监暗伺,也不敢多叙衷肠,唯有对哭一场。
平儿说道:“奶奶还须往开里想,保重身子,咱家的事总会否极泰来的。”凤姐说道:“我自知道,你我二人亲如姊妹,别人总不知我心的了。我心里明白我这病是不能久捱了,你不忘我,把巧姐这孩子多照管些,别叫坏人们算计了,我死也瞑目,这就是不枉你我姊妹一场了。”
凤姐语不成声,平儿已哭倒在炕上。
且说贾府诸人官司里,唯有贾琏虽是掌家之男人,却独他身上实无多大劣迹可寻,怎么罗织也构不成真正的罪款,只是对妻室约束不严,纵她犯过伤人,贪财图利,这却是个不能“齐家”的罪名,妻子的事是要分责的。这么一来,贾琏本人倒也十分恼恚:一是凤姐瞒了他做出这些不好的勾当,二是自问确也缺少了丈夫的气概,素日只知畏惧顺从……,心中倒是自愧。因此对凤姐又恨又怜,知她目下处境已是十分狼狈,故不忍再加埋怨责斥,增她的难堪。无奈邢夫人却不肯发一点仁慈之心,一意要在凤姐失势失宠的末路中向她报复泄其往常的嫉恨,天天逼责贾琏,说:“你还想要这败家惹祸的恶妇?也没个男子汉的样子!你趁早休了她,叫她回王家去,别给咱贾门丢丑!你不肯,我就要替你办了。”
邢夫人一面亲向儿子进逼,一面又唆使秋桐。那秋桐本是她房里大丫头,赏了贾琏后,只凤姐为除尤二姐,一时用着了她,不曾多管,二姐一死,她就以为凤姐是个好对付的,便又转向凤姐生事挑衅,不把奶奶放在眼里,竟欲凌驾。凤姐岂是容得这种无知愚妄人的,于是二人早成了对头,积怨已深。谁想凤姐竟到了这一地步,她更乘势反向贾琏诉说当日尤二姐受凤姐之害的苦情,她原比别人知悉那些细节,再施编造渲染,添枝加叶,说凤姐如何怀恨贾琏,“她原已定计,要害爷与新奶奶!”用这些浸润之言激怒贾琏。贾琏先时于二姐一死,原对凤姐不满,如今再被一挑一激,果然这些年所受凤姐欺蒙骄诈诸事,一齐涌向心头,也觉邢夫人的话有些道理了。然而又终是不忍。如此反反复复思量难以委决。
谁知这日贾琏进房,偏凤姐病中之人,一腔悲切,向他倾诉,不免夹带了埋怨他只顾别的不管她病苦等语,贾琏才在外面诸事心烦意恼,进屋便又听这些怨词,不禁心头火起,变了脸,说即刻写休书,“送你回王家去!”
正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凤姐从此被遣,离开了贾府。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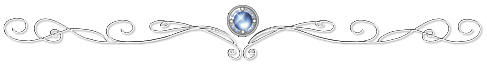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