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
|
我在一些文稿中已然指出过,黛玉之逝,照雪芹所写,应当是:一、受赵姨娘的诬构,说她与宝玉有了“不才之事”,病体之人加上坏人陷害,蒙受了不能忍受的罪名和骂名,实在无法支撑活下去了;二、她决意自投于水,以了残生;三、其自尽的时间是中秋之月夜,地点即头一年与湘云中秋联句的那一处皓皞清波,寒塘冷月之地。
持不同意见的研论者,大致提出两点:一是黛玉乃是偿还“泪债”、泪尽而亡的,不是自沉而死;二是死在春末,而非中秋。
对前一点,我从来也不认为那是一种“矛盾”。既泪尽,也自尽,——因泪枯,遂自尽。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势不两立’的事由。她的死因可能比大家意中想的要更复杂,而不是“是此即非彼”的简单化思想方法所设计的那种样子。
对后一点,我看论辩者的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绝对准确之说。
主张黛玉逝于春末的,所举最被认为是坚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葬花吟》和《桃花行》。这是黛玉自作,而其言曰: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如此明白易晓的话,怎么不是死在春尽,却硬说是死在中秋呢?
我想提醒持此见解的同志们一句:要抠字面,要讲真的明白易晓,黛玉的葬花名句也不能作那样的理解。请问,什么叫“红颜老”?难道少女病亡,能叫“老死”吗?须知所叹的春残花落。乃是节候时运的荣落盛衰的事情,不是狭义的、一时一己的遭遇和变故。脂批说《葬花吟》乃是“大观园诸艳归源之小引”,就已说明了葬花之吟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个很窄隘的意义了。此点最为要紧。以上讲“字面”。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对于雪芹的“春”“秋”如何理解的问题。
在雪芹笔下,春和秋构成全书的“两大扇”,也就是盛衰聚散的两大扇的另一表现形式[注一]。所以雪芹早就点破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这不单指甄士隐一家一人之事,也是笼罩全书的总纲领。雪芹以上元节作为“春”的标志,而以中秋节作为“秋”的标志。全书开卷第一回就写了中秋、上元二节。秦可卿在梦中警觉凤姐所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是这个意思的另一表现法:三春一过,便是衰秋。因此脂砚也说:“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 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参互详玩,就不致于把雪芹的苦心匠意化为一种简单的意思,以为既言“三春去后诸芳尽”是说春三月一过,书中诸女子全部死净亡光了。比方唐代杜牧之有一首名作,题目就叫作《惜春》,其句有云:“春半年已除,其馀强为有;即此醉残花,便同尝腊酒;怅望送春杯,殷勤扫花帚……”说的就是雪芹所寓怀的同一种道理了[注二]。
上引一小段脂批,极关重要,允宜细加参详,或可略窥真意。要讲一讲的,实在很多。如今姑且拉杂浅陈拙见如下。
第一,有人把“三春”只解为迎、探、惜三位姊妹。这虽不是完全不对,但至少忘却了另外一层要旨。从上引脂砚之言已不难得知,所得而与“三春”作对仗的“三秋”若不能解释成是指三个人名字,则“三春”也不应单解作是指三个人名字(兼寓双关则或者有之)。假如有人说“三秋”也是三个女子之名,那只好举出秋纹、秋桐、(傅)秋芳来——不过那将何等不伦不类乎!因此可以证知:按芹原意,全书所写,有三次春的(上元节的)大关目和三次秋的(中秋节的)大关目,前后对称、映照的“两大扇”,构成整个大布局的一种独特的结构风格。这风格,是典型的中华民族式的。西洋艺术理论家是否承认和理解,我不得而知,我们中国人却是完全理解的。
我们点检一下,全书前八十回中,“两大扇”的大致情形如下:
(1)元妃省亲——春,第一个上元节,第十七、十八回;(2)荣府元宵夜宴、太君破除旧套——春,第二个上元节,第五十三、五十四回;(3)某变故情节——春,第三个上元节,第八十一回(推想,假定)。[海棠社、菊花诗、两宴大观园——秋,八月下旬之事,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回,但未写中秋节,故不在数内。]
(1)夜宴异兆、品笛凄凉、联诗寂寞——秋,第一个中秋节,第七十五、七十六回;(2)某变故情节——秋,第二个中秋节,第?回;(3)某变故情节——秋,第三个中秋节,第?回。
我们现在已无眼福读到的原书,恰恰要包含着第三个元宵和第二、第三个中秋——这关系着“三春”“三秋’,都是绝大关目可知!
我也说过,迎春嫁后归宁,已是腊月年底,书正是八十回将尽之处,那么第八十一(或连八十二)回,就正该写到第三个元宵(三春)的节目了!必有大事发生。(是否仍与元妃之事有关,尚难判断。)
那么,这第二个第三个中秋——三秋的大关键,当然是该当另一种大事故大变化发生了。——这又是什么呢?凡是真正关切雪芹真书原意的,岂能不在这一点上牵动自己的心思和感情?
从整体布局看来,下一年的中秋节(依拙著《红楼纪历》,应为第十六年之中秋),黛玉之死就是那一关目中变故之一。
关于这个日子发生黛玉亡逝之变的证据,我已举了一些。当然最显著最主要的力证,仍然是“本年”(第七十六回所写,为第十五年)中秋夜黛玉联句自己说出的诗谶:“冷月葬花魂”。
妙玉听到此句,再也忍不住,出来拦住了。说是“果然——太悲凉了!”这个力证实在连反驳者也驳不出什么别的道理来,只能承认这不是无故的随便措词。其实,全书中例证还多。脂批点明“伏黛玉之死”的那一处,是在贾元春点戏,四出中所伏事故为:《豪宴》伏贾家之败,《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之死。所谓“离魂”,即《牡丹亭》中的第二十出《闹殇》者是。杜丽娘在此一折中病死,其时间是中秋雨夕。试阅其词句:——
“伤春病到深秋”;
“今夕中秋佳节,风雨萧条,小姐病态沉吟”;“从来雨打中秋月,更值风摇长命灯”;
“凭谁窃药把嫦娥奉”;
“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奴命不中孤月照,残生今夜雨中休。”
“恨西风一霎,无端碎绿摧红”;
“恨苍穹,妒花风雨,偏在月明中”;
“鼓三冬,愁万重,冷雨出窗灯不红”;
“恨匆匆,萍踪浪影,风剪了玉芙蓉”!
这词句里,隐隐约约地透露了雪芹安排黛玉中秋自沉“冷月葬花魂”的文情思致的真正渊源联系。这会是巧合偶然吗?
再如,在海棠社中,湘云后至,独补二首,一首自咏,一首即咏黛玉,其词有云: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
玉烛滴干,正指黛玉泪尽;而晶帘隔月,又正是《桃花行》中“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的同一内容。这月痕,乃是八月中秋的冷月,而绝不是泛指(一年四季,月月有月亮……)。大家皆知,诗词中凡涉晶帘,自系秋景,此乃通例,可以互参者也。
末后,要想考察钗、黛、湘三人的收缘结果,恰恰在中秋联句诗中已经都说到了,你看——
渐闻语笑寂,空剩雪霜痕;
阶露团朝菌,庭烟敛夕棔;
秋湍泻石髓,风叶聚云根。
宝婺情孤洁,银蟾气吐吞;
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
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
虚盈轮莫定,晦朔魄空存;
壶漏声将涸,窗灯焰已昏;
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我旧日在拙著中所说:凡星月孤洁,嫦娥奔月等,皆关系宝钗之事,今日看来不但太简单化,也没有细究灵兔那一句要紧的话。这需要重新讨论才行,——当然也不能说是初次不确、这次就对了,我只是说这里面有许多内容,过去一直未曾认真思考、未能懂得透彻。
第一点须要清楚的是,联句乃是黛湘二人为主角,后来加上妙玉。里面没有宝钗的任何位置(她回家去了)。这个布置本身就说明月亮的事与她无关,中秋这日子也与她无关。婺,星名,又叫女媭星,婺字的本义是“不随从,不随和”。情孤洁,应即“花因喜洁难寻偶”同一语意。这与其说是映射“宝姐姐”(女媭乃“姊”也),不如说是映射黛玉,因为性情不随和的不是宝钗而是黛玉,又即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那么,接着说的“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应是黛玉的致死之另一层因由,即:她的死与“误吞灵药”有关。
说到此处。这就要看官们再次回到全书开头,黛玉初来的那一段情景,众人一见了黛玉,就问她药的事:——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在此,脂砚便批道:
“为后菖,菱伏脉。”
我在《新证》第881页指出:
“贾菖、贾菱有与配药有关的事情,详情难以想象。或者竟与黛玉之死大有关系?”
如今结合“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二句而看,我当日的疑心是大大增加了。还要看到第二十八回有一大段文章专写配药的事,那可注意之点,就在于王夫人一见黛玉,就问她吃药好些否,黛玉答后,宝玉开口说,吃两剂煎药,“还是吃丸药的好”。这才引起天王补心丹,王夫人便说“明儿就叫人买些来吃”。这时宝玉却说:
“这些药都不中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林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这然后并又引出宝钗、凤姐的话,并且提到了薛蟠也配此药等一大段非常奇特的文章。内中奥妙不少,均待深究。此刻我所注目的当然仍是黛玉——她又一次和“配药”的问题联在一起。这就绝非偶然了。
结合“药经灵兔捣”而看,黛玉之死,除了患病、受诬、悲伤等原因之外,应是误服了丸药,所谓“误吞灵药”,始如嫦娥之奔向月宫——即在中秋自沉而命尽,做了“水中月”的湘娥。
所谓误服,有二可能,一是自己吃错了,二是别人给错了。第二个可能之中又有两个可能:一是无心之错给,二是有意之谋害。揆其情理,贾菖、贾菱在贾府所分派管的事,是专司配药,配药是最严密慎重的事,外人是不许插手的。在这个事情上使了坏的,多半仍是贾环有份儿。这误服之药,自然不会是什么毒剂,可以致人于死亡,而是大热燥烈之味,使得黛玉的病骤然恶化。黛玉不宜多服热药,如附于肉桂一类,宝钗早巳点破,那就是在“秋窗风雨夕”一回书中。正面提及黛玉的药,是在“风雨夕”秋窗之下,与秋直接相关,也不是无谓的笔墨。
等到雪芹正面写及第三个中秋节时,那已是宝湘二人因“白首双星”之绾合而重会的另一个大关目了。那时,还该又有中秋赋诗的情景。这恐怕就是脂砚所说的“中秋诗起、中秋诗收”的意义了吧?
综上而观,可知拘于“春尽”字面而认为黛逝于春末之说,是不符合雪芹艺术构思的大全局的。黛之泪尽而逝,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多层内外原因,于中秋月夜,自投于寒塘,因而命尽,正所谓“一代倾城逐浪花”——黛玉题咏西施之句也。
其实,晴雯的死,也是如此(在池中自尽,并非病死),容另为小文说之,此不及枝蔓了。
癸亥八月初草
~~~~~~~~~~
[注一]一部书文而分为春秋两大扇,先例已有《西厢记》。在此剧中,张崔相会在春,离散在秋,故此元明时人俗称《西厢》为“崔氏春秋”——以至简化为《春秋》二字之名目,事见李开先所著《词谑》。我意雪芹著书,多受《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之影响,《石头记》以春秋为两大半之布局法,亦其例之一端。
[注二]小杜此诗,用于《红楼梦》,十分恰切,盖第二十七回写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大观园众女儿举行饯花盛会,黛玉葬花,正是“饯春”“扫花”二事之合写,四月二十六日原为宝玉生辰[当另文专论],故“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麝月掣签,亦有“在席各饮三杯送春”的“仪式”。饯春有杯,扫花有帚。凡此皆为特笔,文心奇妙绝伦。
[附记]
这篇拙文本亦为纪念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而作,故所论皆是就雪芹原书本旨而考察分疏,不涉程高伪续一字,不唯不涉,且正以雪芹之本真而显程高之伪妄。此种文字,殆可归之于真正的“红学”范围,而不属于一般小说研究论文的性质体裁。
记得也是在本学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论“什么是红学”的问题。据耳目所及,也曾引起一些红研者的关注。有人赞同,也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此事不无关系,觉得应该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些,庶几于红学有益而无损。要点如下:第一,我所以把“红学”和“一般小说学”分开来讲,并无摒某些论文于“红界”之外的用意。恰好相反,我写那篇文字,正是由于有的评论者发表宏文,对“红学”颇加嘲讽,认为它不是正路的学术,因为它“不去研究作品本身”,尽是搞一些别的,云云。所以“红学”连是否应该存在,似乎也成了问题。我对此不敢苟同。拙文之意,无非指出,“红学”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或是某几个“好事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弄出来的离奇花样。不是的,红学的产生,完全决定于《红楼梦》这部具体作品的具体特点,正因为《红楼梦》不尽同于别的一般小说,才有了红学这门特殊的学问,“红学”也才不同于一般小说学。说清了这一点,正是为了在“四面楚歌”声中为“红学”争取一点儿合法存在权利,如此而已。焉有反过来要摒别的研红文章于“红界”之外的用意敢存于私意之间。这是不必误会的。
“红学”,——本不是一个十分光彩尊敬的称号。在我年青时,大家还只把它当玩笑话,常常带有轻蔑语味。如今的人未必尽明了,反而担心“被摒于红学”之外了!这倒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由此可证:红学的意义、价值、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人们不是担心当红学家的不光彩了,而是争它的名份了。
第二,我的一些话,本不是针对那些已然把“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即“对作品本身”的小说学研究)的各自的定义范围和其间相互关系都已弄得很清楚并运用得相当好的研者而说的。因此,并无“排斥”什么的用意。相反,我在另外场合说过的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可以丰富补充,不能偏废——但不应混同,或以为可以相互代替。它们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但“分”则济美,“混”则两伤,正因此故,才有些人只要“研究红楼梦作品本身”,而不愿去想一想,所谓“红楼梦本身”,毕竟何指?是程刻百廿回本?还是脂评八十回本?连这都不问,便去研究“本身”——并且“思想和艺术”的重大问题呢,而且还认为“红学”中的版本学是繁琐讨厌的东西……。那么,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第三,有文章在批驳拙见时,说了一段话:“由于作者曹雪芹把他的家世生平作为生活的素材,概括到他的艺术创造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关系,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艺术的真实建立在生活真实之上,……”好了,文章承认这一点,是极其要紧的。但是,我不禁要请问一声:同志,您这个论断是怎么样得出的呢?难道不是先有“红学”中的“曹学”做了工作,才使得您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的吗?难道这不正可以证明:红学曹学是“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之研究的先决的或关键的事情吗?您分明是从曹学中汲取了它的成果而后才能够出此论断的。那么,当有人(海外学者以及海内红研家)撰文指责我把红学弄成了曹学的时候,对曹学颇有不然之意的时候,却未见您替我的曹学也说几句公道话,则是否新近才对曹学的意义和作用又有了更多的理解呢?
现在有不少研者,从红学中获得了必要的前提知识,并且分明是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了,却反过来对红学工作者为他的劳动争取一点公平评价而颇有意见,这倒是令人感到费解的。
至于有的又说我把红学分成几大支,分得太细了,也太死了,这也不利于红学的提高和发展云云。其实,红学的内容是不断在扩充的,现在世界上多种外语译本《红楼梦》和《石头记》的出现,就产生了新的“翻译红学”。分类只是就目前状况为了明晰方便而立成名目的。科学总是分支愈来意细的,没听说是有相反的趋势。分工细了,专业专了,一点儿也不意味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位科学家必须是一位多门类科学家,这是“不碍”其成为真正专家的。至于提高和发展,那正是分工与协作的辩证法的天经地义。红学研究必须集聚众多的专家——清代历史、社会、哲学、文艺、民俗、宗教、伦理、……等等专门学者,共同努力,才可望逐步窥见《红楼梦》这一座弘伟奇丽的艺术建筑的堂室之美,岂但区区“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等所能胜任哉。总之,为了《西游记》,完全可以也应该建立“吴学”,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无法说成“吴学”与“西游”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曹学”与“红楼”之间的关系。余可类推。既然如此,红学的一切,显然有它的很大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的问题,用研究其他小说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才产生了红学。红学可以丰富我们中国的小说学,世界的小说学,但它如果与一般普通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它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是混则两伤。我的拙意不过如此,没有别的。有的同志过于担心了吧。
1983年在上海开红学大会,我为《文汇报》撰文,曾说:
像红学这样一门独特而又复杂的学问,真好像神州国土上的长江大河,包孕丰富,奔腾东下,气象万千。我们最好也以 那样雄伟广阔的心境与目光去看待它,创造有利于学术民主的条件,促使各种流派和见解的繁荣发展,从多种多样的角度和方式去研究探索,必如是,才可望对这部异乎寻常的伟大巨丽的作品有越来越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这正是百家争鸣的胜业,而不是“定于一尊”的短见。……(1982.10.24)
这段话,像我的一切拙文一样,措语用词,都做不到尽善尽美,假使能蒙高明不弃,不哂其辞拙,而肯领其意诚,那真是莫大之幸了。
周汝昌 再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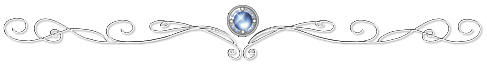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