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情榜证源
|
《红楼梦》的原本,卷末标有“情榜”。此事由脂砚斋批语而得知,今已人人尽晓,但一直未见有人认真加以研索。此榜虽然是雪芹的独创,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无源之水,须知脉络根由,自有所在。
第一应知,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末尾多有一个“总名单”,包列全书人物,名之曰“榜”。榜原是评品高下,昭示名次先后的一种形式,所以《封神演义》末尾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的名单,是为“封神榜”。《水浒传》末尾列有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的“忠义榜”。《儒林外史》末有“幽榜”,尽管考据者认为并非原作者之真笔,但也正好说明当时的这一通行的体例,非同生制硬造。至于《镜花缘》,写了一百个女子应试科考,更是列有一张大榜,就无待详言了。
由此可知,雪芹作书,末附一榜,列出全部重要人物的名次,自然就“顺理成章”,不劳专家们去考证此榜究竟有无,争论列榜是否“蛇足”了。
然而,有榜属实,无可惊异,也还罢了;至于为什么非是“情榜”不可?难道说这也有“来历”、“出处”不成?答案又将如何呢?
我说,雪芹之所以名其榜曰“情榜”,也并非偶然“心血来潮”、忽发“奇想”,确实也有来历、也有出处。若问来历如何?我将答曰:这个“典”就“出”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所编的一部书里。
这部书,名叫《情史》,这听起来真是十分俗气;因此虽然久闻其名,知它在清代也在禁书之列,却不想到图书馆去寻它,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坏书”。做点学问,总免不了有成见偏见,自划自限。所以我很晚才得一见《情史》之面。及至一见之下,便大吃一惊,我说:果然找到了雪芹“情榜”的根源来历!原来,冯梦龙将他所见的古今之情事,无拘小说正史、经籍杂书,一一摘采出来,加以分类,编成一书,是曰“情史”。他将辑得的八九百篇故事,分编为二十四类,亦即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他是第一次“整理”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情”的记载,并且作了“系统的研究”。这真是一位奇人的创举,无怪乎他这一部奇书惊动了雪芹的灵台智府。
《情史》一名《情天宝鉴》。雪芹曾把他自己的小说取名叫做《风月宝鉴》,已经说明了他是从冯梦龙那里取得的启示。
《情史》的二十四个品类,本身就构成了一张“情榜”:试看那细目,便十分有趣——
1.情贞;2.情缘;3.情私;4.情侠;5.情豪;6.情爱;7.情痴;8.情感;9.情幻;10.情灵;11.情化;12.情憾;13.情仇;14.情媒;15.情芽;16.情报;17.情累;18.情疑;19.情鬼;20.情妖;21.情通;22.情迹,23.情外;24.情秽。这就是冯梦龙按他自己的理解和感想。对古今一切情事作出了首创的分类法。(在这里,或许马上就又有高明人士出来议论了:冯某的分类法“很不科学”,不值得介绍!)
这个大分类,自是前无古人,堪称独绝。但是,“后无来者”呢?就不尽然了——就是该改“后有来者”,来了一位曹雪芹,受了施耐庵先生和冯梦龙先生的启发,写了一部小说,为一百零八位女子传神写照,正与一百单八条英雄成为“对仗”,即“绿林好汉”对“红粉佳人”。而他又对每一位女子作出了“评定”、“考语”,其方式正是如同冯氏的办法,都用“情”字领头。我们已经知 道的,黛玉是“情情”,金钏是“情烈”。
如果不妨揣断,那么鸳鸯可能是“情绝”,晴雯可能是“情屈”。至于宝玉是“情不情”,薛蟠是“情滥”,雪芹或脂砚也有明文点出。由此可知,“情榜”虽以一百零八位女子为主,可又“附录”了“男榜”,大约柳湘莲是“情冷”,冯紫英是“情侠”,一时当然不能尽知其详,有待研求,但此事实,已无疑义。冯氏是将若干人一“群”分为若干类,雪芹则是以个人为“单位”而分订品评,这是他对前人又继承又翻新的一贯精神。由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生发”出一百零八位红粉佳人,也正是同一种精神的表现。
雪芹的一部分艺术构思,来自《水浒》,很是明显。例如,施公写绿林好汉之降生,是由于被石碣镇压在地底的“黑气”冲向外方,而成为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的。雪芹则因此而创思,写出“正邪两赋”而来的一百零八个脂粉英豪,闺帏奇秀。施公在一百单八之中,又分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雪芹则写宝玉神游之时,在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看见许多大橱,储藏簿册,注明了那些女子的不幸命运。宝玉只打开了三个大橱,看了正钗、副钗、又副钗的册子。每橱十二钗,所以他看了三十六人的“判词”,正符“天罡”之数。他没有来得及全看的, 还有七十二人之册,那相当于“地煞”之数,痕迹宛然可按。
由脂砚透露,全书写了正、副、又副、三副、四副……。这就表明:情榜分为九层,每层皆是十二之数,十二乘九,正是一百零八位。
雪芹全书回目分为一百零八,榜上题名的诸钗(也可称为群芳,代表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总数也是一百零八。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艺术结构。但二百几十年来,无人正解,所以必应为之大书特书,以见原书真面。谈论雪芹的整体思想,倘若连这一结构法则也不能明了,更何从而谈起呢?
我写的这篇小文,十分简略,许多层次和关系,皆不能深入探究叙述。但其 目的,是为了加深对雪芹著书的正解(不是俗解),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义。比如我此处为讲情榜,引了冯梦龙的《情史》;那么,冯氏所谓之情,毕竟涵义如何呢?这就也须弄个基本清爽才行。因为这将大大有助于理解雪芹的意念。
如今我引《情史》自序的一段话,略作拈举:
“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辗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当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 喜如来’,有人称赞名号,信心奉持,即有无数喜神前后拥护,虽遇仇敌冤家,悉变欢喜,无有嗔恶、妒嫉、种种恶念。又当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
请看,他之所谓情,绝不是儿女之相恋一义;其性情,其胸襟,其思想,其志向,皆不与俗常之人同,而分明近似于宝玉。他开头就提出“情痴”这个名目,他的“怪”脾气,也就是不为世人理解的宝玉的那种“痴痴傻傻”。我多年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时时疾呼:《红楼梦》的真主题并不是什么“爱情悲剧”,而是 人与人的高级的关系的问题。即最博大、最崇高的情。到此或许能博得部分人士的首肯,承认冯梦龙为我们作了旁证。
宝玉之为人,总结一句话:是为(去声)人的,而不是为己的。冯氏至以为情能治国理民,情能改变薄俗浇风,情堪奉为“宗教”。这宗教也绝不是“虚无”“色空”的,恰恰相反,但世俗之人,不解此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项绝大的题目,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枢纽。冯氏不过搜辑旧文,雪芹则伟词自铸——这伟词,真是何其伟哉!然而也只有弄清了上述一切,才能真正体认这种伟大的真实斤两,真实意义。
1988年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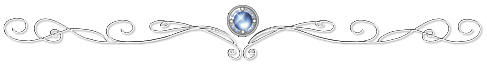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