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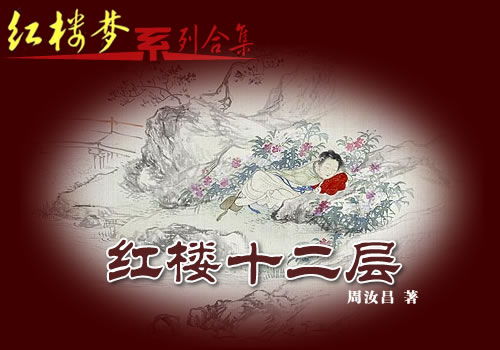
|
|
第四层 《红楼》灵秀(1)
|
研究者、评论家常常以曹雪芹与英国的“剧圣”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比并举。如此,则雪芹可称为“稗圣”(稗指说的别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八个剧本,他的众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将近40处的;而我们的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几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贵贱等,却是集中在一部书里,而且是有机地“集中”“聚会”,而非互不相干。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史上惟一创例,无与伦比!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处,生死休戚,息息相关,是一个大整体,而不是依次上场,戏完了没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换一个“登场者”的那种零碎凑缀的章法。此为一大奇迹,一大绝作。
诗曰:
著书全为女儿心,亦有高年妪可钦。
浊物也须一言及,无违大旨义堪寻。
风流人物在英才
一提起《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大题目,便有如剥春蚕千头万绪须缫,如寄音书千言万语难尽之感。在此文中,我只想就其一端,粗明鄙意,我要从东坡名作《念奴娇》说起。
东坡这首词的头一句是什么?他道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知东坡心中意中关切追慕的,不是其它,乃是华夏从古以来为人传颂的风流人物。谁当得起这样四个字的一种称号呢?东坡写得清楚,那便是三国周郎,凡我中华之人,谁个不晓,公瑾英年将略,顾曲名家,真可谓风流绝代,才艺超群。这样的人才,这种的风流人物,似乎以前未闻(至少未显),比如先秦诸子,两汉名流,大智鸿儒,高风亮节,全是另一种风范。到得三国之时,这才由周郎树立起了头一个仪型。东坡乃许以“风流”二字。但是,仍有一桩遗憾,就是周郎不曾留下翰藻文词,人家都知道他是位高级的将才和艺术家,却不能承认他是文学作家。真是风流未足。且再看同时代又出现了何等人物?
三国之中,东吴、西蜀,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但一色是帝王将相之资,却少见诗人情种之质。惟独地处河南的魏,却产生了那种与帝王将相全不相同的人物——即我所说的“诗人情种”型的人物。魏武曹瞒,雄才大略,且置另论,出名的三曹父子中,以曹植子建特为佼佼。以我管窥蠡测之人观史,窃以为自从有了曹子建,我们的文化史,实实打开了崭新的一章,论人论文,皆与以前不侔。这真是里程之碑,纪元之表。大书特书,犹恐不足以表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意义,作用影响!
那么,对这一崭新类型的风流人物,是否又有崭新的词语来表白他呢?完全有的。有四个字,在《红楼梦》里雪芹也曾用过的,最为恰切,最为高明……
哪四个字?——哪四个字?
你且打开《红楼梦》,翻到第十八回,看众姊妹奉元妃之命题咏新园时,那李纨题的匾额是什么?她道是:
文采风流
这还不算,她的诗又说: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
我说,凡属学人,要识得,这“风流文采”四字,方是曹子建这种类型的文曲巨星人物的题品和写照,方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条最为璀璨夺目的脉络与光辉。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雪芹病逝,好友敦诚,作诗痛挽,其句云: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衰草寒烟对落曛。
那第五句“邺下才人”是指谁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来比拟雪芹。
我们中华文化史,论人论文,特别讲究这个“才”字,这是文化学术界要注意探讨的一个巨大的课题,如今只说“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这一点,是自古同然,从无争议的。因为从南朝的大天才诗人起,便许他独占了“八斗才”之美誉。我们第一流惊才绝艳的诗人李义山说“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也是独以“才”字评于子建。以后,“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说戏本里的“标准语言”。这只要不拿“陈言套语”的眼光去看待,就会深体其间的重要涵义了。曹子建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地),于西园与诸诗人聚会,其时有应玚、徐幹、刘桢、阮瑀、王粲等,号称邺中七子——即是敦诚所说“邺下才人”之义。这实际上乃是后世吟盟诗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赋》,应玚作《正情赋》,他们把汉代的“类书”式铺叙性的大赋变为抒情诗性的短赋,连同五言诗,为文学史开辟了一条重要无比的发展道路。中华的诗史,虽说要以《诗经》《楚辞》为始,但那实在都与风流文采一路有别。可以说,曹子建等“西园才子”,才是中华诗史的源头、正脉。这条脉,纵贯了数千年之久,不曾中断,关系之钜,略可见矣!
敦诚挽吊雪芹,用了“邺下才人”一词,他虽然是以同姓同宗相为比拟之旨,但无意中却道着了我们文化史上的这一条脉络:若论文采风流这个类型的天才文学人物,正以子建为先驱,而以雪芹为集大成,为立顶峰,为标结穴!
《红楼梦》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内涵,但它的文采风流的这一文化特征,识者道者极少。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认识这一重要特征及其脉络源流,便不免令人欲兴宝山空入——至少也是买椟还珠之叹了。
我们文化史上,论文论人论事,都讲才、学、识、德,兼者为难,而才则居首。才之与材,有同有异,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举一个有趣的例:“诗才”与“诗材”,绝不容混)。对于《红楼梦》来说,雪芹明白地记下了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为“是德”),这意思极为明显,就是那时候人,正统观念,是把“才”与“德”看作“对立物”的!才,本来是极可宝贵的质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贬词。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实,子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诬蔑为“有文无行”者,才之“过”也!
然而,在《红楼梦》中,李纨是自幼奉守“女子无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妇,但是题出“文采风流”的,却正是她。这件事,雪芹或许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这些,便绝不是文学史的小范围所能解说的,所以要讲清《红楼梦》,非从文化史与国民性的大角度大层次去深入检讨不可。
要说的难以尽表。真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种怅憾之怀,大凡执笔为文者,定都会有同感罢。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