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八章 鼓音笛韵(上)
|
第五十四回除夕的家庭乐趣,有“击鼓传花”一段好文字。雪芹写了鼓艺的特色,这与他写中秋闻笛,可谓“一对”。雪芹的手笔之高与艺境之妙,也正与鼓、笛之韵大有相通之处。
且听雪芹如何写鼓——(凤姐)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戏完乐罢。……便命响鼓。那女先儿们皆是惯的——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惊马之〔蹄而〕乱驰,或如疾电之光而忽暗。……
你听,这雪芹一支笔,竟传出了中国鼓艺的绝活妙境。这种令鼓,不是单皮鼓,不是手鼓、腰鼓,是长筒落地鼓,鼓面黑漆乌润,鼓边铜钉金亮,而鼓腔上绘着彩纹,那鼓音渊渊然,富有馀韵。击起来,令人耳悦神怡。雪芹写的那鼓艺,是妙手,是灵音,不是那种使满劲擂得喧天震地式的“村里近鼓”;六个“或”字的排句比喻,写尽了中国鼓艺的高境界。“腊鼓催年”“钟鼓乐之”,“箫鼓元宵”……,无鼓不成欢,中国的鼓,有各种“鼓段子”的不同击法,也有独特的乐谱,不是现今洋式“电子琴”里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重复“打拍子”。雪芹在这个体会上是深的,这是艺术节奏的妙用,也是两个手腕(双鼓箭子或鼓槌儿)的绝技。在行文的艺术节奏中,正合了那“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的章法变幻。
但此际讲鼓以比文,我之用意却更侧重在节奏之外的鼓音的轻重亮暗的艺术。这是击法与击处的双重艺术。击法有单点,有联珠,有正应,有侧取,有实填,有空音(闪板),而击处则还有鼓心与鼓边之别,——鼓边还分几个距心远近度,甚至也击鼓帮一二下的配音法。
这儿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鼓心之音最响最正,为何放着那中心点不击,却去击侧击边?难道俗话“敲边鼓”倒是好的不成?
让我提醒一下,在雪芹令祖曹寅的先辈文友周亮工所编的《尺犊新钞》中,引过他友人信柬中的几句话,大意是说作文如同敲鼓,大部分是敲鼓边——而中心也少不得要敲它几下!
就我所见,以鼓喻文之例,莫妙于此。这听起来太觉奇特,说那话者究为何义呢?盖画家可以“墨分五色”,鼓师却也正是“手有五音”,一张鼓面上,他能敲出多样音韵来。只拿京戏来说,几槌轻鼓,配上两三下“仓”然冷然的轻锣——更鼓三敲了,立时让人觉得那真是夜带更深,万籁俱寂之境。忽一阵紧点子突然震响,便使人真感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杀气”声势,耸然神动,便知局面大变。但一支鼓曲,若槌槌打中心,便不成艺——有句极不雅的民间歇后语:“××打鼓——一个点儿”,正谓此也!思之可令人大发一噱。那么可知,鼓不能总是敲中心,文也不可只会用“正笔”。
以鼓喻文,除了节奏的疾徐轻重、繁简断连之外,最要紧的是这个“鼓心”、“鼓边”的问题。而我讲《红楼》艺术,把这一点作为大题目来给以位置,绝不是末节细故之事。因为,鼓之中心正击,就好比文之正笔死写,毫无活气生趣,令人生昏昏欲睡之思了。只用“一个劲儿”(力度)总是敲那正中心,岂但不成乐音,且会成为噪音,人的“音乐耳”听来是“受不了”的。文章也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文有正笔、侧笔之妙用,取“中”取“边”之微旨。
书法艺术中也有“正锋(中锋)”、“侧锋(偏锋)”之别〔1〕。也与文事相通,但文中所谓“侧笔”,含义似乎还要广泛一些,它指的是如何从“边”处着手用功,而目的却正是以此来表出那个“中心”——他不敲鼓心而鼓心“更响更亮”!雪芹写人写事,极善此法,他虽不是专用侧笔,而侧多于正则是晓然易见的。
雪芹在整部书中写了几百个人物(低统计言三四百,高统计台六七百),在这多人中,他用笔最多最重的显然是熙凤、宝玉以及钗、黛、湘、晴、袭、鸳、平等一二十人。哪位专家如能把写这些人的正笔、侧笔、正侧交用笔的实例作出系统研析,那将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中锋”、“正笔”,在书法上是写篆字唯一用笔法;“侧锋”“偏峰”,则是隶、楷书的基本用笔法:两者区分至为清楚(俗说不明此理,却误以为写隶楷也要“中锋”,其实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如以鼓、书相喻,则击鼓又有双层“侧笔”法,即如击鼓心而不正敲,只是偏拂成音,是一层侧;如再只击鼓边而又不正击而也用拂,则成为双重侧法。因此,用这种譬喻来看雪芹写人的艺木,便知其手法的丰富,不但有正侧笔之分,还有单侧双侧之别。在这方面,恐怕例子仍旧是写嚷凤的最好最多,用批点家的话说:“真真好看煞!”
也许可以说,雪芹的笔在熙凤身上用功夫最多,甚至连写宝玉的部分都相形而有逊色、姑且粗说一二:冷子兴、贾雨村在维扬郊外酒肆中,演说荣国府,所介绍的主角实只宝玉、熙凤二人。“介绍”的结束是谁?就以熙风为宝玉之外的另一主题,但闻子兴之言曰:“(贾琏)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雨村聆此,马上就评议说这样人物都是“正邪两赋”而来之人。这是一笔点睛。但这种笔法,说正而实侧,似侧而又正,从旁人品论、远近口碑中轻轻一点淡墨落纸,旋即收住,——实是侧中之侧。
这是第二回。然后到了第六回,刘姥姥求见周瑞家的,周嫂子向她说了一段话——“……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琏二奶奶管家了。……(姥姥惊异,凤姑娘现今大也不过二十岁,就有这等本事?)……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是人(任何人之义,作”世人“者非。)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
这又是一点比先重了些的纸上着墨——是正?是侧?是侧中正?正中侧?又是旁人品论,上下口碑中“显现”了熙风这个异样出色的人物。
而且,这是黛玉入府时一加“勾勒”之后,重加“染色”,前面用子兴一染,这儿用周嫂一染,——下面还有“三染”以至多少染……。这也就是“积墨”法,古来艺理是何等的精确而非玄谈臆说。
说雪芹善用侧笔,不等于说他只用侧笔。正如周亮工所引尺牍中说的,虽多敲鼓边,鼓心也少不得击上几下。雪芹写熙凤的“鼓心点子”在哪儿?第一次是放在秦可卿之治丧上。
有人说,秦氏之亡,原稿属于十二钗结局的最末一个,现行本反而在全书中靠最前了结她的故事,乃是雪芹的大改动,云云。拙见未敢妄言如何。只是觉得如果那样,给熙凤一大段正笔的文章则不知落在何处?若落在第十七回修建省亲别墅、准备接驾上,那太晚也太不对景了,因为那件大事涉及皇家的典礼,里里外外的百般职务,绝非一位深闺中二十岁少妇的掌管范围和“活动阵地”。这只要看看第十七、十八两回,就明白无误了。所以我说写秦氏丧殡,正为给熙凤一个巨大的“正笔”传写,不会太靠后才安排这一场面。
说写可卿之丧是为了写熙凤展才,是不错的;但又不止是一味写她之才。要看雪芹运用的“衣纹”是如何的“稠叠”,着色傅彩是如何的深厚,则在这一大场面中可见其一斑。且看——
一,秦氏病重,熙凤几次去探望,开解抚慰,深情密语。及病者亡,她尽全力治理丧事(这在当时是关系家庭声誉、社会舆论的极重要之一项礼仪)。每日凌晨即过宁府,到了灵前,致其敬悼,只听一棒锣声,熙凤坐于正中椅上,放声大哭!这是由衷的哀痛,具见熙凤本是一个感情至重的女子。
二,秦氏临终,对熙凤说了些什么最为关切的话?雪芹用“托梦”之笔,叙她二人并无一字及于“私情”鄙琐之言,全是预虑预筹,大祸不日来临,家亡人散,如不早计,则子孙流落连个存身之地也将无有!熙风听了,“心胸大快”!——俗常粗心读者,不明雪芹语意,以为熙凤闻听此等不吉之言不应“大快”而应“大忧大惧”(果然,程、高本妄改为“心胸不快,十分敬畏”了),而不悟雪芹是写荣府男子竟无一人可与言此,无一人具此卓识,只知安富尊荣、醉生梦死,而独秦氏知之,并识自己为“脂粉队里的英雄”,如此知己切怀,故云“大快”。此正写熙凤的品格极不凡处。
三,熙凤理丧,总结出宁府上下五项大弊端,借机革除,具有极高的“管理才能”。她因此对轻忽职守的家下人绝不宽恕,重责四十板,众人见她“眉立”,知其真怒了,不敢违怠。此写熙风之威严——正与上文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以及周瑞家的对姥姥的介绍相为呼应衬补(而她驭下之严也积怨甚深,又为她日后的命运预设伏脉)。
四,在理丧中,因井井有序,成绩昭然,她又眼中无复一人,恃才自大,骄贵凌人,短处已显。
五,在送殡之时,还又出了善才庵老尼施计、熙凤入套、受贿害人的事件,此又写她不学而短识,只贪小利而忘了罪恶(也为后文一大伏线)。这一面,是写她致命的最大缺点。盖雪芹极慕而深惜其罕见之才,然亦不讳其失误罪愆。此即脂砚斋所谓既具“菩萨之心”,亦施“刀斧之笔”之理也。
著书立说之人绝不可以低估读者的灵智,他们不需“详尽”罗列,只须举一反三,自能参悟。我这儿只能草草简说,慧心的人已然看出:雪芹在那张“鼓面”上,是怎样选取“中心”与“鼓边”,怎样正敲与侧拂,怎样“单点儿”还是“连珠”或“迸豆”……,已可窥彩豹之寸斑,尝芳鼎之一味。古人赞才士之文采,谓之“梦笔生花”,其说至美至妙;但我谓雪芹那支奇笔,所生的岂止是花——那太娇弱单暂了,芹笔之所生,千汇万状,不只动人耳目,抑且撼人心魂。其“鼓音”之渊渊然,中有金石之声,钟磐之韵,铿锵鞺鞳,如闻天乐,“人间能得几回闻”?年纪小、阅历浅、文化低、灵性差的人,看《红楼》总只见那“繁华”“旖旎”,铺陈之盛,“情爱”之淫(浸淫泛渍之义),而不知一诵杜甫的两句诗——
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
这就会将真意味放过而只看见“热闹”了。
顺便还需一说:秦氏丧殡这一大段,实际上是两面“鼓”音交鸣互响:一面鼓是凤姐之才干过人,一面鼓是丧仪之声势超众。两面鼓又各有其“心”、“边”、“击”、“拂”之奇致,如混为一面,就又失之毫厘了。写丧事,也觉用笔是侧多于正。例如写立鼓乐、设幡旌、请僧道、求诰封、叙路祭……,皆似正而实侧,击边以衬心。以我看来,真正的鼓心正击,却在以下几笔——
一,未入宁府,先闻府内哭声“摇山振岳”;
二,四十九日一条荣宁街,是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
三,出丧之日,只见那大殡(仪仗全列)“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
所以,要识雪芹的鼓音之妙,方能从《红楼》艺术中汲取有益的灵智营养,使自己的鉴赏水平不致为俗常的旧套陈词所拘所囿,那就会如禅家大师提示警戒所说的“失却一只眼”,而辜负了雪芹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宝库。
〔1〕请参看拙著《书法艺术答问》,专论此事。顺便提及一点《红楼梦》涉及书法也有二例,一次是众姊妹代宝玉写字搪塞贾政的盘查,写的是“钟王小楷”,钟繇是“章楷”的代表书家,王羲之是今楷的代表书家,二人正是魏晋时期书法由八分侧笔法过渡到楷书侧笔法的重要关键,彻底改变了篆书的中锋法。雪芹未必即有深意,而我们此刻寻味联系,却也饶有蕴涵在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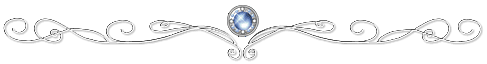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