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 由此说起
|
我们有句老话:"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注:按此语来源当出《史记·孔子世家·赞》:"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同书《屈原贾生列传·赞》亦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至《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乃为另一义。)这话也有时被误解误用为"读其书,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样吧,反正可见"书""人"总是那等紧密相关。《红楼梦》的读者,大都因为想见其作者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们真能够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话,就一定会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部"隻立千古"(注:"隻立千古",借用梁启超评《红楼梦》语。梁氏学术、文学观点如何,非本书评论范围,但他给《红楼梦》下此四字评语,实觉最为简切。)的长篇小说名著。
《红楼梦》,这"书"具在,流览研读,尚称方便(注:说"方便",是相对地、比较地而言之;若认真论及《红楼梦》的版本文字,那问题也很复杂,因为这部书很早就遭到严重篡改,须辨真伪。);而曹雪芹,这"人",却还是一位我们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们所知于他的,仍旧是异常地有限,或者说,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简直是可怜得很。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个人有九个是提起曹雪芹来都谈论兴趣十分浓厚--其实就是求知愿望十分迫切。这情形,我们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来,在我们悠久的文学历史上讲,曹雪芹不过是比较最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却远不能像介绍比他早了一两千年的许多作家那样地顺利和翔实。这真是遗憾之至的事。--困难究竟何在呢?
这困难,是多方面的。
在客观上,截至目前为止,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或者应该说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和便于运用的)正面文献资料稀罕得很。从主观方面讲,研究者的努力也还不能说很够。研究过程中的空白点、模糊点、纷歧点又出奇地多。--这些空白点、模糊点、纷歧点往往就成为了解曹雪芹的关键性的阻阂。再说,这主题所牵涉到的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也又广泛又专门,通晓这么多方面和清楚这么些关系,对一个尝试研究的人来说,真是难度极其巨大的事情。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十分要紧的一点,像曹雪芹,作为一个清朝乾隆时代的内务府满洲旗下人、既有着特殊家世历史、又有着特殊本身经历的"过来人"--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各种情况、各种特点、各种"规律",究竟何似?这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中,也还简直可说是基本空白,探讨起来,了无凭藉,令人时时感到茫然莫知所由之"苦"。
这样说,不是一味来强调困难,"无可奈何"。相反,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来试行了解曹雪芹这位令人无限倾倒、无限神往、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大师,艺术巨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实在应当抱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努力朝我们的研究目标前进。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才敢来尝试这个工作:对曹雪芹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作一下介绍。
然而,困难是客观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能立刻都获得解决。不向读者说明是不对的。
不待说,空白点,我们不能凭空"制造"一些什么去填补它;纷歧点,我们不能主观武断,都作出"结论";不太懂的事物,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遇到这类困难,似乎只应采取以下的办法:空白的或模糊的,如果可能,不妨就某些迹象、线索暂时加以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假定;纷歧的,可以把问题本身加以简要介绍而附带提供个人的评议和正面看法,藉资参考;不太懂的,可以暂付阙如,或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
由此可见,介绍曹雪芹时,除了那些较为确切的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尽免于--不能不容许着若干的探索性的、假定性的部分。这些,原该随处酌加说明,但最好先向读者一总交代一下。
在此以外,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如果只就他本人所生活的那区区四十年的过程来看,就会有许多事情不易明了,大部分的问题难于解说剖析。因此,先要了解他的家世历史,--而这和了解任何作家都必须知道一些他的家世情况的那个"一般命题"又并不完全相同。原因是,不仅曹雪芹的家世非常特殊,而且他本人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境遇上的变化,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历史政治事件所牵连产生的后果,种因甚远,牵绪颇繁,不由历史寻其来龙去脉,就无法说明曹雪芹那些遭遇的意义,也就无法窥见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面貌。
但是,要交代这些,包括百十年间的许多事件(连带着清朝的很多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势必成为辞费,读者就可能感到讲曹雪芹而讲家世和讲历史的部分太多了,不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很不容易恰当解决。
关于这点,我想只好这样:一方面,介绍家世和讲历史时尽量地简要;另方面,也要求读者谅解,我们并非是为了讲这些陈言往事而讲它们,是为了要说明曹雪芹的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而讲它们,目的只在便于更深入而全面地直接了解曹雪芹本人并间接有助于了解他的小说《红楼梦》。在本书中,我并把一些在叙述上可以较为"独立"的章节特别分出去,降为"附录",放在卷尾,这样,既可以"尽早地"直接介绍曹雪芹本人,也可以让读者补充理解那些前面叙说过于简略的各种问题和关系,主次比较分明些。--不过,我还是要说老实话:如果你以为,除了"曹雪芹"三个字,一谈别的,都是"节外生枝",因而表示"不感兴趣",那么你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最好能适当地改变改变才好,因为,想了解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家,特别需要把他放到历史背景中去看问题,除了曹雪芹本身,"以外"的事情都看成是"庞杂"的闲文赘语,恐怕就不好讲了。
和上述之点紧密关联的另一点就是在行文时,有些地方感到单用抽象概念的话来陈述那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陌生事物,既觉空泛,又不易明白,因此有时引事例、借话头,从旁来比喻衬托,希望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这也只是帮助读者理解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特别喜欢"毛举细务"、故为枝蔓的意思。这点也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合作"。其实,干瘪枯燥的文字不一定最"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很多译者把原著中的有意味的部分都当"枝叶"删净了,结果这朵"花"(即使是很美的花)也就不再成其为花了,--先生那还是指自然科学的论述而言,何况是涉及文史艺术的文字?
还有如何对待关于曹雪芹的传说资料的问题。研究曹雪芹这样的人,他"名不见经传",所以也不会有碑铭志乘可据,完全画限于书面文献,排斥故老传闻,那可能是不正确的。比如清代人也有几位笔记著作家记下了一些曹雪芹的遗闻轶事,那其实也得自传说,不过是偶然遇上好事者,存之于笔墨,或付诸刊刻罢了。但口传各说法中也会因年久辗转而走样子或夹入附会。至于到了今天,相距雪芹时代已然二百几十年了,仍然出现一些传说,往往支离可笑,恐怕是一二辈编造者的无稽之谈,我们对这些"资料""文物"应当特别慎重,以免为妄人所乘,制造混乱。
介绍曹雪芹的种种困难,略如上述;归根结蒂,还应该提到一点上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水平的问题。记得曹子建说过:必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才可以论姿容,必须有宝剑龙泉之利,才能够议断割--如若按照这个标准来办,那有资格来讲说曹雪芹的人就太少了。不过,刘勰有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个道理却是不错的。赏文如此,识人又何莫不然。太史公司马迁的伟大,绝不是在于他仅仅能够"网罗放失旧闻",遍历名山大川亲作采访,等等别人也可以努力作到的事情,而是在于他具有异常杰出的良史之才之识。否则,《史记》一书中所传写的那些人物,是不会如彼其栩栩如生,须眉毕现,如彼其富有魅力,如彼其既具有高度的历史学价值,又具有光芒映射的文学性价值的。我们中国"良史"这个宝贵的传统,可以说明传记学的许多问题。可惜的是后世渐渐无人发扬光大了。光是"档案室主任",是写不出一部好历史好传记来的。曹雪芹是一位极其高超的文学艺术家,而我们却是普通人;他的风华襟抱,学识才情,和一般的人相形对比起来,是天壤之别。那么不难想见:就是掌握了全部的翔实史料,克服了各种技术性困难,也还并不等于我们笔下就出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呼之欲出的活生生的曹雪芹。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是太有限了。
我在落笔时,只抱着一点奢望:尽可能地提着自己,不要歪曲了曹雪芹这个光辉的形象,切莫拿琐儒陋士的世俗的眼光、心光去测量曹雪芹,把他庸俗化了,猥琐化了。
好了,那就让我们这样来尝试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文曲巨星,空前伟大的小说家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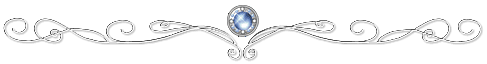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