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十 满汉
|
曹雪芹最后结束他的"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公子生活时,大约年已十六七岁。 上面说过,他家世代是内务府包衣旗籍,是"富贵"而又"下贱"的一种特别的家世。可是自从这时为始,他家和"富贵"二字是断绝关系了,曹雪芹从青年时期起,就转到了另一个队伍里面去,就是,转到了闲散无位的、不得意的、贫困的满洲旗人的行列里面去了。
由于这一"转队",曹雪芹的人生观、世界观,便在起着日益激烈的变化。 为了了解曹雪芹,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时期的满洲和八旗旗人的概况。 雍正朝的大肆压迫、残害宗室,防闲他们的争夺和反抗,可谓无微不至;特务活动的严密,迫害手段的毒辣,都是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这种皇室内部矛盾的丑剧,到乾隆初期犹有馀波,前文亦已约略讲过,乾隆表面虽似稍为宽厚,实则其对待宗室王公的手段和精神与雍正初无二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满洲统治集团上层急剧分化,而影响所被,阶级压迫下的中下层也在发生着分化变动。同时,这种分化又和满人汉化的倾向趋势结合起来,使得统治者十分忧虑,--他表面竭力显示其对待满、汉毫无区别轸域,强调"满汉一体"的大公态度,而实际则歧视汉人,深恶满人沾染汉人风习,极力打击满汉汇流的一切人、事的关系。到后来连早已归旗的"汉军"旗人也逐渐加深歧视,在各种行政制度上制造满汉分域,也就是对汉族血统的人一概不敢信任。这结果自然促进了汉军旗人的日益从八旗集团内向外分化,可是满洲旗人内部也并不是在这种政策下日益团结巩固了,相反,却同样加速了分化和汉化。总之,八旗人的思想,越来越纷歧复杂化起来。
乾隆刚一嗣位,就非常重视旗务,采取种种整顿措施;甚至想到下令修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由郡王降为贝子的弘春,曾因办理旗务不善而"革去贝子,不许出门"(这虽然还不是"在家圈禁",可是不准行动,也是一种软禁的替管形式),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布延图因为"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而受到严饬。乾隆二、三年间,一方面准许包衣佐领、管领与八旗联姻,一方面定出八旗家奴开户(即准许脱离旗主而独自立户)的条例;三年七月,设置稽查内务府御史,十一月命八旗包衣归汉军考试(注:清《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八"选举考"二,"乾隆三年议准,包衣人员,有投充庄头子弟隶内务府管辖、编入上三旗者,又有旧汉人在内管领下,及五旗王公所属包衣旗鼓佐领内者:此等原系汉人,因由满洲都统咨送,每有在满额内中式者,悉行改正,并饬严行禁止!"又卷六十四"学校考"二,"(乾隆四年)清厘满洲、汉军籍贯:嗣后内府、王公府属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及八旗满洲都统务严饬该管官逐一稽察,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下与下五旗王公府属旗鼓佐领内之旧汉人(按即指入关以前入旗者),均别册送部,归入汉军额内考试。有将应归汉军考试之人造入满洲册内咨送者,将该管都统、佐领照蒙溷造册例治罪!"可见乾隆初期开始的满、汉甄别政策是如何严厉,而内务府包衣人自此为始乃完全作为"汉军"一例看待。这是清代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一点,而研究者每不能认识此事之真正意义,而只从包衣人是否应称"满洲"或"汉军"之表面现象立论。参看下条注。),到乾隆六年十月,又命令汉军御史归汉缺--就是划归汉族官员名额之内、制度之内。这已然显示出,乾隆是越来越把八旗内部的所有汉族血统的成员都要当作一般汉人来看待了。果然,事情发展到七年四月,便发出了一道全面而彻底地处置汉军人员的"上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有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无庸另议更张。其馀各项人等,……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
在这里,特别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这次的措施,虽然表面上是为了"联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的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目的,但是联系上举其他迹象而看,内中实际还是包括着政治、民族等政策方面的用意。其二,"上谕"虽然说明"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并且特别表示"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可是结合八年四月"谕汉军同知、守备以上毋庸改归民籍"的命令而看,这一场文官同知、武职守备以下的逐旗为民,实在是规模非常巨大的一次旗员分化,那意义是,官方不但承认了这种日益分化的趋势,而且明令规定以实现之、促进之。其三,乾隆列举了那许多种汉人归旗的旗人,虽然特别把"从龙人员子孙,旧有功勋,历年久远"的这一类分出来另论(这就是包括内务府包衣人而言),以示与一般汉军不同,但是,他称呼内务府包衣为"汉军",这不仅是认识上、名词上的淆乱(注:以内务府旗汉姓人为"汉军",乾隆以前罕有此种讹误。从乾隆以后,逐渐混淆不清,连旗人自己也沿用这种误称了。但"内务府旗汉姓人"和"汉军"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身份殊异,在研究旗人时最应注意分辨。参看杨钟羲《来室家乘》叙其先世本为内务府旗,因召见时不善满语,奉旨贬入汉军旗的事例。(在历史上,仅康熙时三藩期间曾有把个别汉军安插于内务府当差的事例,雍正时编整汉军时曾以内务府包衣人拨补其上三旗的不足数额。)关于这一点,有两种情况应该说明:一种是根本不清楚这种区分的,误认曹家为隶于"汉军旗";一种是以为内务府的汉姓既可称"汉军",又可称"满洲","实质上完全一样",而且说,这样使用名词,"丝毫不发生混淆"。但这后一主张是想拿较晚的误称事例来说明问题的,殊不知这正是混淆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应当以误证误。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认历史上有混称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们的异同则是又一回事,而这后者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说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这些老早合入满洲、世代隶属满洲旗下、满化既深且久的奴仆们再当"自家人"看待,而要归到"汉军"范围以内去计算了。这一点,无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这同时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乾隆上来就整顿旗务,修辑满洲《通谱》,然后就开始定出满洲郎中保道员,满洲进士准许选任知县,奉天州县选用旗员,宗室准取进士等规例;屡次谆嘱宗室、八旗人等"亲亲睦族",提倡满洲旧俗遗风,并"御制"《盛京赋》以发满洲的"祖宗之心"……。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乾隆自己确是在极力制造满、汉和旗、民之间的轸域。用满洲为府县亲民之官的新办法,使给事中杨二酉十分忧虑,上疏谏议;接着,便发生了杭世骏的事件--他因为考选御史,在时务对策中表示了"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的意见,乾隆乃斥杭世骏为"怀挟私心,敢于轻视(满洲)若此!"交部严议,结果竟然因此革职。这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注:参看龚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状》:"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乙酉岁纯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湖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其文极冷隽深刻之致。杭世骏所以为乾隆所恶,也因为他曾反对屡次南巡。)。 但是事件并不像封建统治者所设想的、设计的那样单纯,他的种种处心积虑、设阈防闲,都不能阻止满、汉两大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汇合的趋势,对满人的优待、偏袒的措施也并不能消除他们对当前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不满和憎厌,--这后者也就是满洲、汉族汇合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一。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胡中藻,广西人,是故相满人鄂尔泰的门生,累官内阁学士,时为湖南学政,所著《坚磨生诗钞》,被乾隆细加挦撦,从书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认为皆含讥刺怨怅,对国号、对时政,都肆为诽谤,连他所出的考题《乾三爻不象龙说》也解释为是对"乾隆"谐音廋义式的低毁(等于说弘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曾官居广西巡抚,不但对广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是为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以"负恩党逆"勒令自裁(当时的说法,是"赐自尽")。在此案内被挂累的还有宗室诗人塞尔赫的《晓亭诗钞》。因此传谕八旗:"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矆;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结,又下了一道命令,说道: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著通行晓谕部院八旗知之。
从此,八旗满洲连作诗学文也要犯罪,和汉人文字往来、朋友交契、论弟称兄,都是"国法"所不容了!
请看,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地摧残文学活动、挑拨离间满、汉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满洲人舒坤在批注《随园诗话》时就说过:"时帆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尝以京察引见,高宗(乾隆)恶其沾染汉人习气,不记名。"时帆,即内务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实,要讲"沾染汉人习气",那乾隆本人应该是毫无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无时无地不在题诗作字,笔墨遍处濡染,古人字画卷轴上,名园湖石山坳里,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笔宸翰。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
上述的这类事实,过去的历史家能够注意的,大都也只作为片面强调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旗人压制汉人的迹象和事例来看待,而往往忽视了这些迹象的内在真实意义,不能从八旗满洲集团内部分化以及满汉汇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来理解历史,因而也就难以解释在乾隆死后的十多年上、嘉庆正在申禁宗室、觉罗人等与汉人结婚的时候,就发生了"林清犯阙"的大事变(注:在前此(嘉庆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厨子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的"异事"发生了。陈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领林清,联合了滑县的教首李文成,获得了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的策应,并有宫内太监刘得才、刘金、张太、阎进喜等多人和御书房的苏拉(白身闲散满洲人供役者)作为内应,仅数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内。这事件,虽然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统治宝座几乎一旦倾覆,震动远近;以致嘉庆(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来了)下"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说出"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卒,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非朕之涼德,何以致此?"的实话。--这绝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这是统治集团严重分化最有力的说明。
介绍曹雪芹而讲到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离题太远"了呢?这则牵涉到对"远""近"怎样看法的问题。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八)说过这样一段话: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hào)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gǔ)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緜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遂死,杭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注:"练亭之子"说盖为袁枚《随园诗话》所误。"楝"误作"练",亦由袁枚始。按"楝亭"为雪芹祖父曹寅别署。)。练亭在官有贤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注: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也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陈六舟《谈异录》亦载:"(雪芹)子孙陷入王伦逆案,伏法,无后。")。
这就是把林清事变和曹雪芹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这所说的曹勋,即是曹纶。曾有历史家考证曹纶隶属汉军正黄旗,其伯祖名瑛,历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讹混,实际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无关系。从纯考据和简单的是非正误的角度来说,历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从研究当时社会心理和八旗集团内部汉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况来看,则笔记家所记下的人们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红楼梦》这两件事联在一起的现象,仍然是有其社会意义而值得注意的(注:不妨参看这一事例:镇压天理教的那彦成,碰巧正是最恨《红楼梦》的人。)。我们只要看一下,曹纶、曹福昌父子事发后,前后该管的都统、副都统禄康、裕瑞(即《枣窗闲笔》的著者,此书曾论及《红楼梦》与曹雪芹之为人)等,皆革去宗室顶戴,即日发往东北,永不叙用,福庆、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职、或罚俸,其馀参领、副参领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屯居汉军旗人听州县管辖,同民人编入保甲"--这就是干脆划出旗外,不再当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时,豫亲王裕丰,因其属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闲散陈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党恶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丰因此罚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贝勒、贝子、公等,嗣后各将所属包衣佐领人等留心稽查,……断不可姑容隐匿!"(裕丰后来又因其包衣祝海庆与教犯祝现为同族,隐匿不报,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闲房居住,不准出门"。裕丰就是曾作《枣窗闲笔》传写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孙)。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当时一部分八旗包衣,汉军兵丁,宫内太监,苏拉人等,这些统治集团下层人员或奴仆阶层(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参加了秘密起义组织,用行动来推翻清室的统治(注:至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也不无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亲王裕丰,即是显例;还有《啸亭杂录》详记"犯阙"经过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对搜捕"教匪"所表现的令著者昭槤十分惊异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为"其心实叵测"。稍后又有觉罗常鼐,与满人尼莽阿,归附邪教一案。)。诚如嘉庆的罪己诏所说:"变起一时,祸积有日",上述的这些和人民较为接近的下层旗人,对黑暗统治压迫的不满和怨愤,竟至使他们终于决心参加起义反抗,这在封建时代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足见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么积久而日趋激烈了!
我们在这里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他们入关后的初期,还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问题虽然也还包括着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经是阶级矛盾了。八旗集团本身就是由上层旗主、旗兵来压迫、剥削下层的。下层旗兵和并不"披甲"当差、只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旗民(称为"余丁"),受到残酷的专制统治和盘剥,因此用种种方式进行反抗,如逃亡,谋求出旗,抗租,乃至个人行刺统治主,最后参加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只有从阶级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满汉汇流的原因和意义。
这里并不是要说曹雪芹"就是"曹纶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纶一模一样的"天理教徒思想",而只是来说明,要想探讨曹雪芹这样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产生那种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了解当时八旗人的分化情况是有其参考意义的: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处于激剧变化中的下层旗人中间,才有可能产生像曹雪芹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从他的《春柳堂诗稿》里所流露的若干迹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个汉军或内务府包衣旗人。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注:另一满洲小说家和邦额的事例,可供研究参证。蒋瑞藻《花朝生笔记》说:"乾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著《夜谈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然记陆生柟(按可参看本书第三节引者)之狱,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啸亭杂录》云,'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又云,'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按此当指和邦额以"狐"隐"胡","若辈"即指满洲"胡人"之意)。"礼亲王著书,安得不云尔?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远也!"(见《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和邦额实亦内务府籍,永忠的诗稿中有他的题句。)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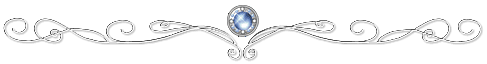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