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十三 被钥空房
|
曹雪芹虽然后来落拓人间,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很自然地还是从家庭方面而开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堤防"相遭遇。只要他不愿向这一道堤防低头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斗争,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家长正面交锋陷阵。 看来,青年的曹雪芹是这样做了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曹雪芹那样的人物和作家。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推论,也还不无记载线索可寻,足供参证。 本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一则既不是为当时封建士大夫所喜欢的,二则他本人又不是什么名流显宦,自然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则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过家的,当时也很少愿意甘冒忌讳而提及他们这种人物和事情的,所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其有关传闻,即在当世也不会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献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因)。虽然如此,那时候还是有些人知道"曹雪芹"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的一些影子--尽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胧模糊。乾、嘉时期的文人,还是颇出我们意外地有几位居然记载下了点滴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 像名诗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并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后人,--不过他误认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辈数,又说"相隔已百年矣!",而其实他正是雪芹的同时人,他说那话时是"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后,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几年而已:这就是我所谓"朦胧模糊"的例子。然而稍后的梁恭辰、毛庆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老贡生""汉军举人",无有后嗣,身后萧条,等等情况。这大致还是和事实符合的。由此可见那时还是有一些有关他的"口碑"在辗转传述。 长洲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是乾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经学家,由他这里也传出一件颇为重要的"口碑"来。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注:《能静居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按此笔记,徐珂所著《雪窗闲笔》还曾见及,引作赵惠夫《能静居随笔》。赵烈文,字惠甫(旧时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荫华,有《双清阁诗》。) 这个传说乍一听来好像是有些离奇附会似的。可是它实在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献,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待它、阐释它。 宋翔凤是怎样一位人物呢?龚自珍非常爱重他,说他"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说他"朴学奇材张(zhàng)一军";他虽是经学文儒,但又吟咏风流,时有奇气;"少跳荡,不乐举子业,嗜读古书;不得,则窃衣物以易。祖父夏楚(笞打)之,不能禁也。"其性格正和曹雪芹有相近之处。这种人的话,是颇堪注意的(注:宋翔凤这一传说的来历,当和庄存与或张惠言、恽敬二人有关。庄存与和孙灏(字虚川,前曾作右翼宗学稽查官,是敦诚的师辈。曹雪芹和敦诚为至友,曾同在宗学,所以也该认识他)曾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子,可能间接知道或认识曹雪芹,张,恽二人在雪芹死后和敦诚有交游痕迹,见《四松堂集》。庄存与之侄为庄述祖,宋翔凤即是述祖的外甥。张惠言、恽敬也和庄、宋交情密切,非师即友。而且,张惠言做过景山官学的教习,恽敬则做过咸安宫官学的教习,这两个官学都是专门教育内府包衣旗家子弟的学校,其间当然有知道曹家事情的,甚至有曹家的亲友。所以宋翔凤的话必由庄、张、恽等处而来,应当可靠。 又上举诸人,皆常州派经师文家中的重要人物,常州派是清代思想界中的重要潮流,而他们都如此重视《红楼梦》与其作者(参看第二十七节恽敬以四色笔细批《红楼梦》事),亦可注意研究。此点尚未有抉出者,附记于此。)。至于他把雪芹说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误说完全一样,可不必深论;《红楼梦》大概后来真个到过乾隆的眼里,这事还可能和这小说的迷失八十回以后的重要部分很有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须留待下文再讲。此刻值得注意讨论的,却是这个传说的后半。 所谓"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诗稿》中说雪芹是"其人素性放达",完全证实了宋翔凤的传述十分正确,因为张说"放达"、宋说"放浪",正是同义语,只不过口气在婉蓄和径直、赞赏和评论之间,微有差异罢了。所谓"至衣食不给",其为可信更不待言,因为关于这一点的参证就更多了,我们此处无须一一列举。 由此足见宋翔凤的话颇有其真实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点尚不在此。 宋翔凤的话,对我们说明了两点更值得注意的要义。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给",生活贫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变的后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规规矩矩",投靠统治集团,老实地为他们服务,衣食之给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于"不给",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第二,因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给,这终究还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继续"放浪"下去,那就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长遂站出来干涉了。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两点可以略加解释:第一,钥空室中的这种办法,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惊讶了,但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欢"生事"的本家宗室,就爱使用这种恶毒的惩罚,严重的"高墙圈禁"(特种监狱),轻一些的在家单室圈禁,再其次的还有所谓"不许出门":都是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同时是隔离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极为残酷。满洲式的家庭对"不肖"子弟也使用这一作法,是毫不足异的事情。第二,这一作法当然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常便饭"式地轻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须使出这一"绝着"的境地,那就说明别的办法都已想尽了,也就说明那种矛盾冲突已然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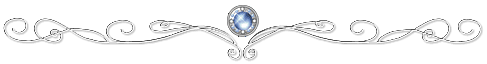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