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十六 当 差
|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注: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注: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乾清门侍卫"的音讹。乾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未知确否,疑不足信。)。 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我个人认为,此一可能,值得探讨(注:此说根据系由敦诚赠雪芹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等语推得。按"虎门"一词何指,向不为人注意;我曾在《红楼梦新证》三版本640页"补遗"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虎门"条及《周礼·地官·师氏》推测敦氏所谓虎门有两解,可能指国学国子监或指侍卫值班的宫门处所,而以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按当云八旗官学属国子监,而宗学属宗人府,固与国学非一),因此倾向侍卫一解。吴恩裕先生始进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门"指宗学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学,向来之疑遂解。吴说见其《有关曹雪芹八种》38-44页。当然,仅据敦诚诗,实不能断言雪芹必为宗学人员,盖"数晨夕"出陶诗,本移居喜得佳邻,日夕过从,交游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当时居住西城,离右翼宗学很近,故而能和敦诚在学中晤谈。这些,还无法即作结论。)。 宗学的情况,还可以粗知梗概。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清显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孙皇族)所设的官学。清初时期,本来在顺治九年就设立过宗学,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即等于将宗学撤销。雍正二年,复行设立。这时的制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分设宗学,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子弟十八岁以下的入学读书(十九岁以上的亦接受),有愿在家读书的,听之。每学以王公一人总其事,下设正教长(后名总管)二人、副教长(后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担任;清书教习二人,以罢闲满官及进士、举、贡、生员之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二人,以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之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无定额,每学生十人设教习一人,由举、贡考补(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里,就写到优贡考教习的事)。每月考试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试,又每五年大考试一次。仅教长有官俸,教习只给银米衣服,学生月给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因为这对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间接关系。 第一点,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只是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内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制这些子弟,要他们"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内部矛盾争斗的复杂与剧烈是出乎一般情况之外的,顺治时期的宗学最首要的一条规矩就是:"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放松了这一点,不但令各就本府读书,而且还特别鼓励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这到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康熙的诸位皇子,为了"夺嫡",分朋树党,各在本府延揽名士材人,造成势力集团,争斗极其激烈,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雍正本人是当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这种事态的严重意义,所以他"初登大宝"不久,一面穷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后起之秀"--这就是他复立宗学的更实际的目的。 在宗学里,教长、教习等人便负上了沉重的责任。雍正向这些教师们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若非立学设教,安能使之改过迁善?……今特立义学,拣选尔等教习宗室,……导以礼义。或有不遵,小则尔等自行惩戒,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这和顺治早年的话简直完全一样)。……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职,以副腾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这就是说:"尔等"要帮我来管理控制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为此效劳,--否则可要小心!(注:有意思的是到后来八旗官学的教习中也出现了不循"礼义"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栋《吟斋笔存》卷一所载:"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脱不羁,充镶黄旗教习在京,忽月余不赴馆,长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樱桃斜街勾栏中,往侦之,见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怜曲》,群妓环绕,奉为师,酣嬉于粉香花影,不复更知有人世也。"这事极有参考意义。) 和宗学关系切近而很有参证价值的,还有雍正七年的设立觉罗官学(觉罗其实也是宗室,不过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后裔,"觉罗"特指旁支后裔;俗称以"黄带子""红带子"来分别)。觉罗学的制度规例大体俱如宗学,只是那"上谕"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蕴藉了:"所派出之管辖人员,不时训诲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该旗衙门居住学习,禁止出门!"--不但觉罗的子弟学生,连学生的家长觉罗等本人也在这里入了"学规"(这真是奇闻!)--:"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准外出。"不用说,这种"精神"绝不限于觉罗学,对宗学同样起约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当上了差事。
第二点,正像前一节里讲过的那样,在宗学这一方面也是无法解决"汉化"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顺治朝初设宗学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说:"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他认为,学生们只要通过翻译文字,就可以来看"各项汉书"。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在学的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但是当时规定却形成清书教习一共只设二人、汉书教习每十名学生即设一人的悬殊比例。这种规定(当然是由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本身就反映了问题和矛盾。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两翼,"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这当然也是汉文的事情。乾隆三年,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二人。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说:"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顺治)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许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九人,改为翻译教习,并每翼各增骑射教习一人。二十七年裁觉罗学里每旗汉教习一人,改为满教习。一乾隆朝大致的政策趋势,是很明显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见宗室公(爵)宁升额,宁升额竟不能说满语,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这就暴露了以前满语教学完全是敷衍应酬的事实真相,也说明了满洲族人的汉化简直是封建统治者主观意志所无能为力的历史进展。 扼要地叙明了这些事势,是因为要想理解曹雪芹这一阶段的生活,必须向这方面参考研究,寻求消息。上述两点,对曹雪芹在宗学里的地位、遭遇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曹雪芹究竟在宗学里所任何职?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答复。 据传说,曹雪芹作的是宗学教习(注:张永海说。)。如果事实确是这样,那么结合上述种种,就可以看出更多的意义来。 不过这个传说也有一点不好解释。
传说中的"教习"的原语是"瑟夫"(注:据黄波拉、吴恩裕两位的调查记录。黄文发表于《羊城晚报》1963年4月27日-5月1日。),传说者解为教师之义。这个解说倒是对头的,因为清代官书也写作"塞傅",是满人称呼教习的用语。但是雪芹的好友之一、宗学学生敦诚,在诗句里提到他和雪芹在宗学时的交谊的时候,说出了"接■倒著容君傲"(注:此用李白《襄阳歌》典故。(向来解"倒著接■"为倒戴帽子,实则接■乃古代鹭羽编制之簑,即鹤氅类。我另有考,此不备及。))的话。这语式语气,绝不像是学生对老师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从学生敦诚是皇室贵族而老师曹雪芹是包衣奴隶的身份来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乾隆时代,还像以前的各姓封建朝代一样,对作老师的,不管是私家延聘还是公家指派的,礼数都特别尊重,受到特殊的厚遇(例如官中教职,品位极卑,却只长揖以见公卿,不行跪拜;到晚清总督大员当书院开学典礼时,还要亲率诸生,先向教师行跪拜礼;皇帝皇子对师傅也要施以殊礼,绝不能和一般臣僚同样对待(注:如《晚睛簃诗汇》卷二对乾隆帝诗的案语所说:"感旧之什,盖于诸旧臣中择其尤者始著于篇;师傅称先生,字而不名,尤致敬礼。"乾隆诗云:"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最是佳证。《天咫偶闻》卷一:"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卷十叙旗家家法子弟礼节最严,而"其敬师也亦然"。)),师生的关系和感情,是极鲜明的东西,它虽不能完全"解除"其他身份差别,但满可以部分"抵消"或具体"压倒"之。康、雍时代的权相太傅马齐(注:此人是傅恒伯父,明义、明琳等人的伯 祖;是康、雍两朝与皇室内部矛盾和内务府人员关系都很密切的人物。马齐与弟马武,威权倾一时,有"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不甚识字,因为所请的馆师常常不按时守职,他竟然和门下诸人说:"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也。"当时传为笑谈。敦诚却不是这样"保持"着"旧俗醇风"的满洲人,他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著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子。试拿这些和"接■倒著容君傲"的口吻来比较,那差别就极分明了;我们很难想象他对一位老师可以说出"容君傲"的话来。 看来,在宗学里的曹雪芹不会是一位塞傅老师;而可能是一种较为高一等的杂役人员,比如抄写、助理文墨等事的"下手"。我们可能想到,如果他是举、贡一流的身份,岂不正合作教习的资格,宗学里何至于把他用为杂役之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曹雪芹家是获罪抄没并且又经过其他巨变的,这种家族的子弟因为被罪惩斥而沦为杂项人员,在学校里当当冷差,勉维生活,倒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在宗学任职,起讫年月,都不可考。往上推,似乎可以早到乾隆九年(1744)左右,即敦诚初入宗学的年代,但也许比这要晚一些;往下看,恐怕不会迟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因为这时他已经移居到西郊山村去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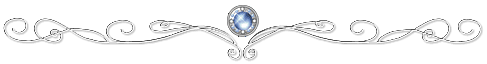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