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秦可卿之死(4)
|
瑞珠在楼下自己的居处,就着油灯,细细地端详了那支有黄莺叼蝉造型的八宝银簪一番,心中很是纳闷。
后来,瑞珠隔窗望了望对面厢房,漆黑无光,只有秋风在天井里旋磨。她便吹熄了油灯,躺下歇息,很快,她便发出了平稳的鼾声。
4
尽管伸手不见五指,贾珍还是极熟练地进入了天香楼里通向秦可卿楼上居室的暗道。这条暗道所有的仆妇都不知道,就是尤氏和贾蓉,也都不清楚,那是可卿十二岁,为她盖这天香楼时,贾珍亲让营造者设计修制的。
走到那扇直通可卿卧室的暗门前,贾珍用指弯轻轻扣出了一贯的暗号,奇怪!每次他一扣,可卿总是马上在那边扳动机括,暗门也就立即翻开,这回他敲过两遍,却还没有动静,他心中不禁咯噔一下——难道这女子竟不等那消息进一步座实,便寻了短见么?气性也忒大了!她难道想不到我一得便,必来她这里么?别人糊涂,她能糊涂么?我贾珍对她,难道不是一腔子真情么?什么叫“爬灰”?那糟老头子占儿媳妇便宜,你能叫他“爬灰”,现我和可卿站到一块儿,让那不知我俩是怎么一层关系的外人看看,能说不般配吗?我才三十多岁,可卿二十出头了,我的雄武,她的成熟,好比那蜜腊石木瓜镇着飞燕的金盘,实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只可惜为掩人耳目,只好把她配给贾蓉,那蓉儿跟她站作一处,你问不知底细的人,准说是长姊稚弟……我“爬灰”?论起来,可卿还是我破的瓜,倒是那蓉儿,占了我的便宜!说来也怪,是哪世结下的孽情,我贾珍过手的女人多了,偏这可卿让我动了真心!她对我,那也是不掺假的……这擅风情、秉月貌的女子,就是真为她败了这个家,我也心甘情愿啊!……就算大难临头了,她也不该连我也不再见一面,就撒手归天呀!
暗门这边,贾珍满心狐疑,情血涌动。
暗门那边,秦可卿从贾珍叩响了第一声,便从坐凳上站了起来,走到暗门边,手握机括搬手,但她却咬着牙,身子抖得如秋风中的白柳,心乱如麻,下不了决心……
其实,秦可卿一直在想,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那贾珍他还会不会来?她先是判定他不会来了,而且,为贾珍自己计,他也实不该来;但如果真的就此撂下她“好自为之”,那她付给他的一片真情,不就太不值了吗?……无数往事,在她心中一个叠一个地掠过,开始,她还小的时候,她只觉得贾珍是个堂皇慈蔼的父辈,过了十岁,她觉得贾珍仿佛是个健壮活泼的大哥哥,而到她初悟风月时,找不到什么道理,她的心目中,贾珍就是那她最愿意委身的男子……后来父亲派来联络的人,跟她直接见面通话,她也从渐知深浅,到深知利害,她后来当然懂得,这一段情缘,是绝对的宿孽。她也曾竭力地抑制、克服、摆脱,甚至于故意更加放荡,想把自己的情欲,转移到许多的方面,比如她就故意去点化过还是童贞的贾宝玉,也沾惹过贾蔷,可是没有办法,没办法,到头来她还是只能从贾珍那里,得到真正的快乐……她真想叩问苍天:宿孽总因情么?分离聚合皆前定么?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暗门那边,贾珍情急中开始低声呼叫她“可儿,可儿”。
暗门这边,秦可卿抖颤更剧,她欲开又止,欲止又不舍,她实该独自演完自己的这出苦戏,万不要再连累堂堂宁国府的威烈将军……可这孽海情天,谁能超脱?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情既相逢,一道暗门又怎阻拦得住!
秦可卿终于搬动了那暗门机括,暗门一转,贾珍狂风般卷了进来,可卿还没反应过来,贾珍已一把将她揽于怀中,紧紧搂住,叫了一声“可儿!”便狂吻不住……
秦可卿先是一束白柳般抖颤于贾珍怀抱中,任他狂风过隙;待贾珍风力稍减,她便从贾珍怀中挣脱了出来,倒退了几步,贾珍追上,逼近她问:“可儿,你这是怎么……”
秦可卿理着鬓发,开始冷静下来,仰望着贾珍眼睛,说:“你来了,我这心里,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去了……”
贾珍抓住秦可卿的手,说:“现在还只是一个谎信儿……”
可卿感觉贾珍的手温,正徐徐传递到自己手上,她便引他坐了下来,坐下后,他俩的手还联在一起。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交谈过。
“你的心,我知道……可冯紫英家的消息,向来没谎过……”
“就算你父亲真的没了,看来也还不是事情大露,是他自己没福,二十几年,都奋斗到宝座边上了,偏一病仙逝,功亏一篑……你要想开,这也是冥冥中自有天定呵!”
“他既去了,母亲一定已殉了,我耽误到这时辰,已属不孝……”
“孝不孝,不在命,全在心;比如我爹天天在城外道观里跟一帮道士们胡羼,炼丹烧汞的,指不定哪天就一命归西,难道我非也去吞丹殉他么?再比如我一时丧命,难道定要那蓉儿他也服毒自刎不成?”
“你们比不得我,我更比不得你们,你忘了去秋张友士留下的那个‘益气养荣和肝汤’的方子,那头五位药的十个字两句话,不是说得明明白白!那是父母的严命,我能不遵?”
那张友士开出的“益气养荣和肝汤”的头五味药是: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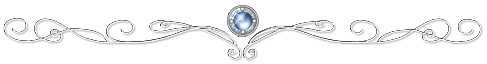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