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平民红学”背后的个人学术情结
|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当代中国文化发生的深刻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时代。刘心武先生正是在这个文化时代的不间断的对话中,写出了他的长篇名作《风过耳》和《四牌楼》,以创作的实践昭示了昔日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终结。在他这种文化思想的烛照下,投入了《红楼梦》探佚的研究,而且一发不可收,也许是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信条:
真正的品位是超脱于他人的眼光和褒贬,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找到自己钟情的精神空间。
显然,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周老先生在几近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境况下,不仅关注刘心武先生每一个具体的细小的探佚成果,而且还不断提笔写信、赋诗,作为他的学术后盾。仅《红楼望月》一书就选登了6则周汝昌先生的书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远离“权威”。不仅没有远离,而且以“红楼梦讲座”的形式将周汝昌晚年学术错误倾向在更广泛的空间传播出去了。回头看刘心武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平民红学”“出了闷气”,又怎么理解呢?红学界有一个很不正常的风气,凡观点不同,就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冷暖。即使周汝昌先生这样如此奖掖后进的老学者,也不免沾染其习,刘梦溪先生曾批评周汝昌先生说:
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畴,置考证派红学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加之他也热衷探佚学的研究,且著作频频问世。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情色彩过重的话语。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气:“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此话差矣,翻开国内外几部红学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证派集大成者,岂止是“民间”?
郭豫适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专章介绍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成果,长达两万五千多字;韩进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白盾先生主编的在1997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刘梦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设专节介绍“考证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几乎国内外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达成共识:考证派集大成者。
至于周先生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那只是个人意气的宣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名单赫然写着周汝昌;《红楼梦学刊》编委也赫然写着周汝昌,难道这还不算红学界的?以上这些都是学术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纠葛,不必多说。但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沿着周汝昌考证与索隐合一的道路发展,成为新索隐派的带头人。学术界对新索隐派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试想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在红学界就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必然处于尴尬的局面。然而刘心武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此路不通,相反却引发了受压的情绪,以“平民红学”作为对阵,又差矣!
综上所述,我们对刘心武现象作了概括而简要的剖析,既从宏观上,即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指出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又点到了他个人的学术情结。但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红学发展史、曹家历史本事,以及学术思维方式等各个视角去探析,才能发现在浮动的、琐碎的、狂热的现象的掩饰下,文化现象与社会趋动潜在的关联,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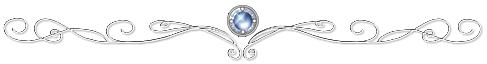
|
|
|
|
|
|
|